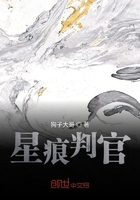黎升东被耿禾秋邀请讲话。他说话的神气,仍然带着“革命小将”敢冲敢杀的火药味,比起他的战友和学长刘森林毫不逊色。他声色俱厉地说:
“我们要继续学习上海革命造反派战友抓阶级斗争的经验,‘组织队伍,打击敌人,巩固政权’。把古城医学院建成让阶级敌人和一切牛鬼蛇神颤抖的钢铁堡垒。我们的头一件措施就是派学生红卫兵,进驻行政楼和教学楼,与革命教职工一起‘斗批改’。******思想是最高、最活、最科学、最现实的马列主义,我们要用******思想这个照妖镜,寻找阶级敌人,重新揭开某些单位阶级斗争的盖子,深挖隐藏得更深的反革命分子、敌特分子。要揪出一个,往牛棚里送一个,不规规矩矩的,就坚决镇压!”
革委会成立后,全院各单位重新掀起了“斗批改”高潮。几天功夫,牛棚里就增加了三十多个人,而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古城医学院的代理人魏旗、胡宗传等几个大走资派,重新被押回学生大饭堂接受“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学生批斗。在他们被推搡着进大饭堂的时候,周伊波在路边看见几个人的脸都肿着,胡宗传的一条腿跛了,而魏旗还是从病床上拉出来的,听说颜飞已经瘫痪了,黎升东在大会上提到他时,说他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
虽然,院革委会委员间思想分歧严重,实际上是貌合神离的两张皮,经常发出两种声音。但是军代表耿禾秋和工宣队几个队长,对于两派学生委员过分出格的言行,尚能发挥一定制约作用。他们不太在意两派都指责军代表、工宣队偏袒对方的杂音,基本控制了“内战”局面。
院革委会要求各年级成立相应的分委员会。63级的学生百分之八十以上都属于“红战团”,参加“八.一八”的人数很少,“八.一八”的人把郝一民推出去参加分委会,郝一民几经推辞,最终还是接受了。除郝一民外,63级分委会基本上还是“红战团”的原班人马,换汤不换药:主任是左国强,副主任裴鸣、朱勇实、郝一民。
63级学生除过参加院革委会组织的大批判以外,多数时间是坐在宿舍里背“老三篇”,读社论,在早晨和晚间的体育活动时间,要先到司令台前跳一趟“忠”字舞。一天下午,一班几个人一起从操场走到饭堂,两派人只是在这个把饭碗放到同一张饭桌上的时候,才有意无意地站在一起,说上几句话。苌安全经过去西宝二院的一段见习,对自己的业务能力愈加心虚,对“红与专”的关系有了新的见解。他带着不满情绪对唐韶说:
“当医生得有点真本事,咱们在西宝的见习计划还不过半,就被叫回来。这样下去,毕业后总不能脖子上挂着‘老三篇’去给人看病吧?”
郝一民站在唐韶旁边,立即对唐韶严肃地说:“你俩在说什么?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不是?”
周伊波知道郝一民进了年级分委员会后,和左国强,裴鸣、朱勇实几个人相处得还不错,他总想借机会报复唐韶和苌安全。郝一民两句问话,把唐韶和苌安全镇住了。周伊波也觉得很解气,不过他并不觉得苌安全说错了,只是说过了,他替苌安全解围道:“你说咱们得有点本事,这话不错,要红也要专。但说脖子上挂着‘老三篇’,用词欠妥!”
“你不要在这儿搞折中调和、当******!”郝一民对周伊波怒斥道。
周伊波见郝一民当真生气了,身旁的牟成天、韦保名似乎也站在郝一民一边,觉得很无聊,即转身洗碗去了。待回来放碗时,他听见韦保名用娘娘腔重复着一段校园里的老生常谈,“****同志说过,毛主席的话,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你活学活用了,就能无往不胜,排除万难,逢凶化吉。******思想学好了,有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医学知识不愁学不好。”
牟成天冷笑着,咳嗽一声后接着韦保名对苌安全骂骂咧咧道:“咱这是个饭桌上的批判会,在你灵魂深处刺刀见红。现在挽救了你,你以后就少痞疳!”
“对,对,算我痞疳。不过没有那么严重,说句玩笑话。走,走!你们也快去把自己的臭嘴漱漱!”苌安全沉默了一阵后,突然咧开大嘴笑着,故作镇静地拍了一下唐韶的肩膀去洗碗了。
郝一民仍然站在桌边,严肃地对唐韶说:“你把刚才发生的事和大家说的话写出来,送到年级办。”
第三天,在左国强主持下,63级同学在解剖楼南大教室,召开“批判反动学生大会”。与会的还有院工宣队副队长、兼年级分队长华石头和分驻各班的队员。三个挨批判的反动学生,都站在讲台边,挂着“反动学生”的大牌子低着头,样子和在大饭堂里挨批的黑帮分子没有差别。苌安全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三班的铁杆保皇派于文凯。他放在宿舍里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读书笔记”被人发现,其中有恶毒攻击毛主席的言论“尽管毛主席把心都操碎了,但是过去有些事还得一分为二来看,比如大炼钢铁和全民吃食堂。”第三个是左国强班上刚和农村媳妇离了婚的革大联。他前妻来学院告他是陈世美,只把女人当生孩子机器;还揭发他,曾经在上床前,说过一段反对中央一位女领导的话。女领导认为,在传宗接代方面,男人只提供了一个精子,而女人提供的是全身,甚至不要男人也不是不可能的。可是,革大联竟然说,“从医学的角度来讲,这句话不正确,他认为,生儿育女就和种地一样,种子和土地都重要,甚至种子更重要,不要土地,也不是不可能的。
唐韶是站在台上的主要发言人之一,他慷慨激昂地批判苌安全这位曾和他一起回家乡造反的战友,和批判桂小芹时一样,他的眼睛瞪得很圆,手臂挥动有力。周伊波看到在前排就座,不时起身回头引领着大家呼口号的工宣队分队长的确是自己小学的同桌华石头。他不仅神态和十年前酷似,而且连讲话时的皖北口音都没变。
周伊波走了神,他想起了曾给山芸讲过的那段华石头送给他一只脖项上长着两个肉赘赘儿的公羊羔的事。真可惜,那时爸爸硬是不让养。他还想起了,在接到中学录取通知单的回家路上,华石头浑身膻气、伤感地对他说:“周伊波,你以后闲了到我家玩,我给你挤羊奶喝。我爸爸不让我再上学了。”
批判发言一结束,苌安全等人就从大教室前门走出,被直接押送去了牛棚。
左国强在作大会总结时说:“在工宣队和革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咱们年级出现了‘一个太太,两个腾腾!’那就是,‘革命形势好的太太;大批判,杀气腾腾,学习毛选,热气腾腾。’”
大会一结束,周伊波就走下台阶,到前排和华石头见面。华石头一见到周伊波就眉开眼笑,亲热地把周伊波的手抓住不放,爽朗地说道:
“从我一进你们学校,就打听你,还没有问清楚,今天就见着你了。”
“欢迎来对我们进行再教育!”伊波在周围好奇的目光下,说着套话。
“面对你们这些优秀人才,我们惭愧,不敢这样说,互相学习!”华石头看看周伊波,又看看左国强谦虚而又庄重地说。
左国强和裴鸣、朱勇实几个人毕恭毕敬地向华石头点头:“我们先走了,你们聊!”
大教室里的人走空了,华石头转而直率地说:“伊波,俺这双手,小时候拿羊鞭,挤奶,也拿过几天笔杆子。长大了拿尺子、剪刀。给恁说实话,在俺工宣队里,大部分人都是俺这水平。现在干革命要靠‘二杆子’——笔杆子、枪杆子。这笔杆子俺拿不稳,枪杆子更拿不稳,就是有点‘二杆子’脾气。你说俺凭啥来领导知识分子?再说,俺来的人,本身就是两派,内部都不统一,咋向恁宣传?听说恁这儿复杂,很难弄。以后,请你多帮助了。”
“哪敢呀!”周伊波见华石头还是那样一见如故,对他不加设防,也毫无顾及地问:“我知道,现在你们的副队长里还有蓝发,他以前在俺们铁路南巷住过,上小学比咱们高一级,很赖皮。现在人咋样?”
“还是那样,虽说俺两家住得很近,却一直不来往。在厂里他参加工指派,俺属工总。”华石头想说、想问的话都很多;周伊波问他的话,他尽量清楚地作答。在说话中,他忽然又想到什么事,问道:
“伊波,你是哪个班的?”
“一班!”伊波答。
“嗷!去你们班的工宣队员叫王西生吧?”
“好象是姓王!”
“他人不坏,可是常冒傻气,还喜欢拍蓝发的马屁,蓝发说啥他都听。以后,班上有啥事,咱们也可以聊聊。”华石头推心置腹地说。
“那我想对今天的批判会,先说点意见,不知行不行?”周伊波问罢,看华石头很愿意听,就把自己对苌安全的看法和他被揪出来的过程,给华石头反映了,最后说:
“他可能和你说的那个王西生差不多,也是一个常冒傻气的人,嘴上把不住门。已经把他批判过了,让他受到教育就行了,不要再把他定成反动学生关进牛棚。”
华石头回去后,叫上左国强、裴鸣、朱勇实、郝一民、王西生,又一次传唤了苌安全,经过再次询问他犯错误的过程,对他进行了一番严厉批评后,华石头对苌安全说:“我们看你认错态度还算好,就不再按反动学生对待了。以后要加强毛主席著作学习,努力改造思想,嘴上要有把门站岗的。”
回班后,苌安全变蔫了,嘴巴上了锁;床头放了《毛选》,而且用铁夹子把它一直翻开着。
宋锺先生平时在街巷里谦善乐施、睿智热忱,在邻里纠葛的复杂事件中,既能分清是非、区别钉铆,也能把人们心里的死结解开,把不必要看得太清楚的事抹得界限模糊。上年纪人说他练达,年轻人说他圆滑。练达也罢,圆滑也罢,毕竟是解放前在反动派的铁路管理局电务段里当过段长的人,加上他东北老家的成份不好,妹妹是****分子,就有小辫子可抓。老章家找人写了材料向办事处革命造反派揭发他,不但说他有个人历史问题、社会关系问题,还说他常和邻居周三铸聚在一起发政府的牢骚。这样,他就不能不被揪出来审查。在街道办事处关押时,办事处掌权的工指派里一个年纪较大的副主任把宋锺认了出来。这人姓雷,是周三铸的老乡,在周家见过宋锺,知道他是烈属。而且,老雷还能记起来,在车站广场迎接从朝鲜战场光荣回国的志愿军伤病员和烈士骨灰那天,见到宋锺的情景:那天,广场上飘动着彩旗,城墙头悬挂着巨幅标语,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用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牢不可破”、“向英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军乐队在站台上奏着雄壮的“志愿军军歌”,居民们站在车站广场敲打着锣鼓,中、小学生带红领巾、挥舞花束。志愿军伤病员躺在担架上,身盖草绿色军被,手持花束频频向群众挥动。在车站站台上迎接凭吊烈士骨灰的亲属中,住在解放门地区的人只有宋锺一家,他们都佩带着黑袖章等在那里。那时,老雷就站在他们旁边,当几个军人搀扶着悲痛欲绝的宋锺及老年家属返回时,他也簇拥着放声哭泣的几个孩子,一起从站台下来。老雷觉得,对宋锺应当和对其他被关押的人有根本区别。在他的坚持下,宋锺在隔离审查期间得到了适当照顾,不久就被释放回家。
宋锺被释放后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神态自若,身体健康。一个星期天,他看周三铸在家休息,就又过来串门,主动述说自己被关起来隔离审查的经历,也寒暄些家务事。他说,老雷看过他以后,不但没有再挨打,而且还批准家里人去探望和送衣物。他还对三铸说,小女儿婵婵和她的男朋友齐子长,经常去给他送吃喝。他不住夸齐子长勤快、善良、不倔,听使唤。起先,他不太同意婵婵交这个男朋友,可是,患难见真情,经过这段时间,他转变了看法。现在学校对学生领证、结婚的政策放开了。学生中连怀孩子、抱孩子的都不少见。他告诉三铸,婵婵和齐子长打算尽快把事情办了,有了结婚证,在毕业分配时才能得到照顾,才不会把俩人分开。他问三铸,对伊波和山芸的事有啥想法。
周三铸对宋锺被关押期间没有受罪,不觉得稀罕,而对宋锺告诉他大学里有关毕业生分配的政策,却觉得很新鲜。可是,儿子回到家里为什么不吱声?他没有把心里的不悦说出来,只是表现出对婵婵打算结婚感到惊喜:
“俺可是要给小婵婵贺喜的!喜事儿啥时候办,可得打招呼!”
“咱们不用费心,领证以后,就在齐子长家简单举行个仪式。你这边娶媳妇和我家丫头出嫁不同,伊波办事的时候,你老周还不得摆几桌?到时候,如果没有地方摆,就放到我家院子里。要是没有地方住,我可把房子腾一间出来。”宋锺被隔离审查几个月后,似乎对老邻居的情份更重了,也许他预感到了什么,提醒三铸和柳枝对下一代该尽的义务,早一点尽完。
“替伊波,谢他宋伯啦!可是婵婵结了婚,还不得给她们布置间新房,让他们在家住段时间?”柳枝感谢宋锺,却仍想着婵婵结婚的事。
“你们都知道,我那个家,是个‘联合政府’,我这房太太,对我不错,也是好人,就是心眼小,自进了我这家门,她这个当继母的,就不待见婵婵。家里的空房,我可以借给别人,就是不能让女儿和姑爷回来住。”
周伊波和黄山芸回到家的时候,宋锺刚离开。三铸和柳枝把宋锺的话对他俩学了。伊波听罢,沉思了一会儿,想说些什么,似乎又有点难以启齿,和平时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完全不同。在父母又问“你俩啥想法?”“啥意见?”的时候,他吞吞吐吐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