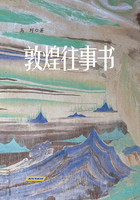一周过去,63级新生走在校道上与老生已经浑然一体。星期一上午,当同学们第二次来到理学大教室的时候,李紫丰领着两个同学已经在黑板偏上方写好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向旧社会问罪走社会主义道路”两横排大字。他也把黑板正中部位“忆苦思甜动员大会”几个大字的虚框勾画出来,准备再用彩色粉笔涂实。当他们注意到教室里的同学越来越多,估计田主任快到了,就匆忙结束了最后的修饰。
动员报告开始后,田雨书记态度严肃、声调高亢地告诫大家:“阶级教育是大学生的一门长期主修课。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谁胜谁负的斗争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特别是在大学和研究机关,这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很严重,有些人还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的立场,一定要站在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一边,只有根本上转变自己的思想感情,才能有革命的坚定性。”
田雨书记还把前一天晚上,在学生干部会上已经安排和布置的工作,又一次给大家简要传达:一、邀请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工人、贫农代表做两次报告;二、组织讲雷锋家史、唱雷锋的歌,根据雷锋的光辉事迹,自编自演学雷锋的节目;三、到校外参观反映四川大地主、大军阀刘文彩凶恶残暴、贫苦农民悲惨可怜的地主庄园泥塑――“收租院”;四、分班讨论“阶级教育”报告,交流参观展览的感想,忆家史,深入检查剖析本人的思想变化。
田雨书记讲话后,“忆苦思甜报告”正式开始。年级团总支和学生会请来做忆苦思甜报告的老工人和农民,都是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人民代表”。近一年多来,他们已经在各个高等院校和中小学作过许多次报告。周伊波感觉,尽管他们的理论水平不如田老师,但无论是表达能力,还是对过去发生事件的记忆能力,都不比田老师差。报告会很快进入高潮,大教室里除过做报告人嘶哑的嗓音外,啜泣声一片,偶尔在某个座位上还传出呜呜的哭声。周伊波虽然不太爱哭,眼眶还是有点湿润。
第二天上午,6301班同学又按照统一安排的时间,去博物馆参观泥塑“收租院”。在展室里,配合着展出的水牢、抢粮、鞭笞等泥塑场景和讲解,播放着如泣如诉的歌曲:
“鬼门关前破锣响,阎王道上尘土扬,新谷登场未进屋,豺狼出动把粮抢……”
和听忆苦思甜报告时一样,周伊波眼眶里又一次湿润了。他朝旁边挪动了几步,在暗淡的光线中,看见黄山芸和桂小芹走在队伍的最后,拿着手绢在擦泪。
回到学校,一班下午的讨论会仍由苏莘莘主持。起初大家都表情严肃、低头沉思,又似乎都想发言,却都不愿打头。周伊波觉得自己的家境和作忆苦思甜的老工人、老贫农比,不算太苦。更何况自己知道的家史,都是听父母讲的,自己对地主阶级怎么剥削压迫劳动人民,具体细节并不了解。正在犹豫要不要发言的时候,苏莘莘向他示意,“你带个头吧!”
周伊波沉默片刻,即把头抬起来带着深沉的感情,娓娓地讲述河南人的故事:“我母亲生在河南农村,她小时候姥姥家里穷,兄弟姊妹多,姥爷去世后,家里生活无法维持,她十二三岁时,姥姥就送她就到财主家里干活,为家里挣钱。每天鸡叫头遍就得起来做饭,因为个儿小,得站到凳子上才能够着锅台,经常手上、脸上烫起燎泡。一年到头累死累活,肚子还吃不饱。干了三四年,实在熬不下去,她就偷跑出去,摸到城里找到她老姨家。老姨帮她在煤窑上找到事儿干。我父亲因逃避封建包办婚姻,离开家乡,先是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来跟日本人打仗腿打断了,被老百姓救下来放到煤窑养伤。在那里他遇到我母亲。俩人结婚后,他们又扒难民火车,搭坐汽车、马车,回到父亲的老家嵩汝镇。老家不但旱、涝、蝗灾不断,而且还闹土匪。我父母刚回到家乡就招惹来土匪抢劫。听我父亲说,一天半夜,跑来了七八个人,脸上抹得黢黑,手里拿着家伙,把他吊起来拷打要钱。说他在外边发了财。土匪找不到钱,临走还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敲打了。我爷爷本来就饥寒交迫,身体有病,受到惊吓后病情急剧恶化。我出生后不久,爷爷就病故了。一家人在老家实在无法生活,我父母这才带着我,一担两筐,走了近千里路逃难来到古城落户。起初,经老乡介绍,租赁到了房子,那时屋里没有床铺,睡在苞谷杆和蒲席上。门外边也只有锅灶和风箱。父亲先是在火车站扛包,后来因为腿脚受过伤,干不下来了,又去拉架子车搞运输。我小时候,母亲经常领着我到火车站去卖稀饭、茶鸡蛋,帮助父亲维持生活。到了过年的时候,我父母不愿邻里和朋友来拜年,也不到别人家拜年,更怕我串到院子里或哪个小朋友家里。过年那几天,天不亮母亲就熬好了稀饭,一家人匆匆喝过,带上干粮离开家门去转大街。到了天黑,才回到家里歇息。以前我母亲经常唱旧社会穷人过年的小曲儿,我只记得曲调悠长低沉,也能记得小曲儿的词:
二十三日是祭灶,再有六七天新年就来到。虽说家家都过年,富人穷人两条道。富家张灯又结彩,杀猪宰羊真热闹。穷家过年发熬煎,缺油少盐没柴烧。集上买斤母猪肉,再把一块羊血挑。闺女要花儿要炮,磕头烧香祭祖庙。神灵保佑没病灾,老少平安就算好。
解放后,我家的日子才一天天好起来,1958年父母亲都参加了服务行业的工作。我现在也成了家里第一代第一个大学生,我父母总是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
周伊波的发言,似乎有些平淡,没有引起任何人人哭泣,也没有人叹息。然而却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他刚一说完,何法娃、袁凤梧、郝一民几个人都争相举手、喊叫发言。虽然这几个人的年龄比其他人也年长不了太多,可都像是在旧社会长大的一样,对旧社会的事记忆犹新。他们的父辈,都是在周扒皮那样的地主老财和阔太太的残酷剥削下,同样是在“半夜鸡叫”时就开始下地干活,每天连稀汤都喝不上,月月缺油少盐,糠菜半年粮,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们每一个人讲起来,大家都是热泪盈眶。有几个女生还痛哭流涕,不住擦眼泪,和周伊波讲述的效果明显不同。后来顾衣锦、唐韶、苌安全、于景一个接一个相继发言,气氛相当热烈。
于景刚说完,苏莘莘即以舒缓的语调感慨道:“我们这些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同学,都是旧社会的苦孩子,新社会的幸运儿。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我们决不能忘记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翻身得解放,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生活,一定要为祖国、为人民好好读书,将来做一个又红又专的好医生。”
苏莘莘的话还没有说完,孙雅就佝偻着腰前倾着身子,打断她的话说:“让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学也发发言吧!”
张信平坐在孙雅的对面,注意到孙雅正在盯他。他眨了眨失神的眼睛,心想,组织委员一定是知道每个同学的家庭成份,于是,吞吞吐吐地说,“虽然我父亲是医生,但出身富农家庭。以前在农村,不时听到老辈子人说,我们家原先也很穷,后来我爷爷领着我大和我二爸拼命干,置地买牛,节衣缩食,也顾了几个长工,还做点生意,才发了点小财。后来我大离家学医去了城里。解放后,土地改革时,家里定成富农成份,全家人思想上都想不通。现在,学了政治理论,明白了。解放前,我爷爷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剥削。解放后,他们连做梦都想着恢复失去的天堂。我以前根本不了解劳苦大众,没有站在雇农、贫下中农的立场上去想问题,只是偏听偏信家里老人的鬼话。所以,对我来说,今后思想改造的任务还很艰巨,革命的道路还很漫长。”
孙雅又把眼睛盯到了马夫。马夫讨好地把苏莘莘看看,团支书给他了个刹那间的微笑,向他点头示意,鼓励他发言。马夫忙起身站起来,向大家鞠了一躬,然后坐下捏捏金色眼镜框,低着头用浓重的方言含糊不清地说道,“我家住在本省和内蒙交界的地方,是老区,土改进行得早。我爷爷是地主分子,在当地闹红潮时就罪有应得地死了。可是他的反动思想影响和余毒还远远没有肃清。以前我父亲说过,高原上的地主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连关中的中农都不如。来我家放羊的穷人,都是自动找上门,赖着不走,有的人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甚至还贩过大烟土。他们没有饭吃的时候,就到我家来,情愿当长工。现在我才认识到,我父亲那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说话,为反动阶级评功摆好,美化剥削阶级,抹杀阶级界限。这说明一切反动阶级和他们的思想,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更不会被埋进坟墓。我虽然出身于这样的家庭,但决不做他们的孝子贤孙,一定要做革命人,做剥削阶级的叛逆者,当他们的掘墓人。”
未等苏莘莘和孙雅点名,黄山芸就把手绢装起来,抬头看看苏莘莘,问道:“我可以说几句吗?”
苏莘莘微笑着向她点点头:“当然可以!”
黄山芸带着一份深情和感动,说道:“我虽然从小长在山东农村,出身下中农,却是第一次知道天下的劳动人民在旧社会都那么苦。第一次真正明白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剥削阶级都是那样残忍地对待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我虽然不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但是我的父亲却是去为剥削阶级服务,为反动派卖力,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我从小学到中学,都受到党和人民的培育,现在党和政府又给了我一次来大学深造的机会。我想借此机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和坚决跟党走的决心。”
周伊波和多数同学都好奇地看着这个出身下中农,却有着复杂社会背景的同学。
孙雅对着苏莘莘的耳朵悄声说:“她怎么一句都没有提和家庭划清界限,肃清反动思想影响,好像和我们一样?”
苏莘莘平静地好像没有听见孙雅说什么,但心里却在想,“你孙雅说自己出身干部家庭,其实你父亲不过是饮食行业的一个小干部,也不是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你能和我们工农子弟一样?”
接下去,苏莘莘让没有发言的人,按座序往下轮。每个人毫无例外地都表了态,只是发言长短不一。
当晚,周伊波靠在床框上回忆了两天来的所闻所见,结合自己的家庭变迁酝酿了一首小诗,抒发自己两天来的感情体验:
活棺材啊漆黑一团,阴森可怖啊毛骨悚然。
血流成河啊路有尸骨,无衣无食啊泪雨涟涟。
金银成山啊酒肉发臭,任意挥霍啊魔手血染。
孩子们的哭叫,少爷小姐的笑谈;
老年人的呻吟,老爷太太的狂欢;
年轻人的怒骂,刽子手们的凶喊;
旧世界的进行曲啊,太凄凉、太悲惨。
多少个祥林嫂啊,多少个白毛女;
多少个伪君子啊,多少个大肚皮;
沿街乞讨啊,子散妻离;
羊羔美酒啊,纸醉金迷;
草菅人命啊,受压受欺;
豺狼当道啊,哪儿有理?
想想过去血泪,苦难莫忘记。
向旧社会问罪,仇恨埋心底。
我们要:
痛恨资产阶级,热爱社会主义;
做革命接班人,直到共产主义。
阶级教育开始后,学生区5号楼楼厅的黑板报上增加了一条标语——“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另有一首以紫锋名义写的短诗,取代了“新生入校第一周简报”:
“田地里下了雨,这是春天的雨,在枝条上的一颗种子,随风落入泥土离开故里,却又闻到了姐姐的清香,母亲的气息。”
“‘紫锋’是谁呀”周伊波站在黑板跟前纳闷,忽然听见彭波对李紫丰说“你写得真好,写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周伊波这才知道“紫锋”原来就是李紫丰。对这首诗,他另有看法,觉得彭波是在讨好李紫丰,姓李的是在拍另一个人的马屁。于是,他以挑剔和不屑的语调问道:“这诗是歌颂党还是歌颂田老师?”
“都是!”李紫丰眯着笑眼,看了看这个对诗歌还有些敏感的瘦小伙,认出他是6301班的班长,略带尴尬地答。
“写党还可以,要是写田老师,就有点拍了!”周伊波对眼前两个年级干部都看着不顺眼,楞楞地撂下一句话就走了。
星期四下午,年级办通知全年级同学课外活动时间在理学大教室召开紧急会议,动员和布置有关助学金评定工作。晚上各班班长、团支部书记在年级学生分会会议室继续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