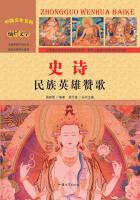狼,对于现代都市人来说,早已是一个虚无飘渺的神话。既然是神话,就不管它曾经于人是如何地凶恶残暴,崇拜者仅取它美丽的表象和勇猛的性情,便视狼为膜拜的一个物种了。它炫耀地伏在假洋服的左胸或颈椎部位,装饰着主人不羁的爱美之心。它在流行歌唱中走过,用毛茸茸的尾巴爱抚着歌者孤独而冷漠的梦想。它也溶解在酒浆饮品里,让你的肠胃及血液翻江倒海而遁入醉乡。某种意义上的偶像的狼,只是狂妄于同样虚拟的荧屏上,悲烈地嚎叫着,以示它的存在。
而真实的狼,正蜷曲或徘徊于都市.角的囚室里,期待人工饲养。它以潦倒的状态,接见孩童们的认证,完全有损于它的种群的形象。它成了人的奴役、玩物和欣赏品,丧失了野性即天性,沦落为十足的活标本。它是教科书里的害虫,生性凶恶,也是受保护的动物,濒临灭绝。人满为患的都市是它的异乡与坟墓,那一片温馨的故乡被它丢失在遥远的山野。儿也一样被人类所挤兑,它们与许多同类的命运一起,坚守着最后的栖息地。
狼也有思乡病么?人非狼,人只能按照自己的立场和思维方式揣摸狼,狼也无法来校正。狼的天敌是人,狼吃人,但总归被人所降服。回到卜个世纪初,随便翻翻地方志,就可以读到狼患对人的致命威胁。甚至到五六十年代,狼还是一些并不偏僻的山村农人家畜家禽之敌。狼带给人的首先是恐惧,那种毛骨悚然的感受大多来自狼。个别老辈人的脖颈上至今依然戴着狼的纪念章,它们却是最后的狼咬。于是,狼变种了,狼改恶从善了,狼美丽了,狼可怜了,狼成了人的宠物了。
于是,狼在失去它真实存在的时候,狼性似乎化灵,或者说是仙气。在造就生态科研成果的同时,潜入了现代都市人的精神空间。其实,狼早已进入了文化,东郭先生一直生活在人们中间,狼来了的故事源远流长,狼和羊的传说经久不衰,与狼共舞的风景精彩依然。慢慢地,慢慢地,狼的恶名被一些孤愤的人们所自诩或者说是白虐,在人头攒动灯红酒绿的世界里发出了狼的嚎叫,野性而充满诱惑。似乎有人不如狼,有人的低迷与颓败,脆弱与浮躁,虚伪与无耻,该从狼那儿拿来点什么,用以阐述和丰富这个花花世界。
人们想起了狼这个物种,用亲昵的口吻充满人情关爱的姿态,向栖居于遥远山野的狼的残部问一声:你现在还好吗?而最先听到这个声音的,是都市一角人工饲养的狼的活标本,那辱没狼的本色的圈养动物。问候不是猎人的枪声。人与人之问,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狼之间,多义而饶有趣味的关联,是一个多么费神的命题。时下,许多汉语词汇的应用,早已不是本来的概念了,对狼的崇拜也就不会让人们惊讶了。
《三秦都市报》2000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