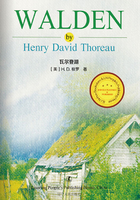20年前的某年夏天,军委总部的一位中将来青藏线视察,到了唐古拉山下的长江源头兵站。将军破例地在这个一般人都不过夜的地方住了一天一夜,找了不少于50名官兵和过往人员谈心。他了解到经常有人在这座“站在山顶双手能抓天”的地方望而却步,有严重的高山反应,有的甚至把命丢在了这里。将军还特地走看了那片戈壁坟地,他的眉头皱成了一团,他问:“医院呢?”回答:“报告首长,这里没有医院,有了小病忍着,得了大病要跑800里路到格尔木去找医生。”将军的皱眉仍然没有松开,他骂人了:“什么手掌(首长),我还没有你们的脚掌高呢!不是吗?你们的脚下就是5000多米呀!我说这些搞编制的人真******浑蛋,最需要医生的地方偏不建医院,白吃饭!我做主了,这儿必须有救战士命的医生。当然我没权批准你们建医院,但是设个只有十人八人的医疗站总可以吧!”
江河源医疗站便应运而生。
按照将军的指示,从全军抽调了一批优秀医务人员到医疗站。将军的侄女叶萍就是在这时候,从北京军医学院来到唐古拉山下。
遥远的白房子
医疗站是清一色的平房,在空中悬着。
悬空房?
原来房屋下面是一片空洞,没有地基。整个房屋是用一根根水泥柱子托着,空洞的深度有三四米。
悬空盖房与高寒区的永冻层有关。
可可西里虽然地处青藏高原永冻层区域内,但它不像唐古拉山巅的永冻层那样,终年都冻得硬邦邦永不开化。它是季节性永冻层,到了夏季最热的日子里,永冻层就会出现一定厚度的冰消雪融层,使地面变得软绵绵,承重能力下降。又由于早晨、中午、下午太阳光的强度不同,季节性永冻层融化程度也就呈现出深浅不一样的状况。这样在修建房屋时如果将地基打在地面上(冻土层之上),房子就会随着不平坦的融化层而倾斜,甚至坍陷。防止这种现象的唯一办法,是掘地三四米,穿过永冻层打地基,之后再筑铸起一根根水泥桩基。这些桩基支撑着整座平房或楼房。
悬空房便由此而来。
江河源医疗站的两排悬空房,是最早出现于可可西里的建筑群。白亮白亮的墙壁使它在这片荒原上格外惹眼,几里路外就能瞅得见。“医疗站快到了,加把劲快走,那是咱们的家啊!”汽车兵们一瞅见白房子总会这样兴高采熟地说,踩着油门的脚底狠劲一踏,车速快了许多。
汽车兵们渴盼快一点赶到白房子,自然是因为有头痛脑热的不舒服之感想求医求药,但是还有一点埋在心底的秘密(其实在他们中间是公开的秘密),这就是急于要见到医疗站的女医生女护士。在青藏线跑车的汽车兵们好像在与世隔绝的另一个世界颠簸,在这儿野生动物举目可见,那些善跑耐寒的野驴、黄羊常常和汽车赛跑。但是想见个人,尤其想见个女人,那是很难的。要不怎么称无人区呢?传说,有一个兵在唐古拉山兵站服役3年,穿行唐古拉山4078余次,只见过两个女人,还都是老太太。一个是他母亲,老人家想到独生儿子去了那么远的地方当兵,很是牵挂,在老头的陪同下千里迢迢上山看望了一次儿子。另一个是一位藏族老阿妈,她得了急性阑尾炎,从深山出来求医,因为候车在兵站住了一夜。兵们的生活之单调心头,之寂寞便可想而知了。世界本来就是由男男女女合理组成的,缺了任何一方都是亏损,从而失去心态的平衡。
遥远的可可西里。
汽车兵们从瞅见白房子那一刻起,心就热乎起来了。不过,他们并不急于进医疗站,而是先在距医疗站5公里处的通天河里把车冲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再把头埋进水里,扑噜扑噜地痛痛快快洗个脸。总之,人和车不带征程上半丝的烟尘和油腻。因为医疗站上有穿戴整齐的白衣天使,她们那压在眉梢的白帽就足以让人推想,如果世间的女子都像她们这样洁净,人心肯定会变得没有一丝污垢。
兵们进了医疗站后,首先要一个个接受护士们测量血压、注射疫苗、发放预防感冒药物等必要的程序。然后才是有病者对号入座地找有关医生问病,开处方。毫无疑问还在他们并不熟悉该找哪位医生对症看自己的疾病时,又是护士们来充当向导。
遥远的白房子此刻都装在了兵的心里。
这些平日开玩笑开得不可收拾的兵们,这时候一个个变得老实极了,没有一个人出声,连走路的脚步都是轻抬慢放。因为他们把在医疗站的这段有限的时间看成难得的一种享受,而任何享受都应该是悄无声息的。
的确是很有限的。医疗站最初只有两个女护士,其中就有中将的侄女叶萍,另一个叫阿袁——她的本名袁明芳。不过,大家都叫她阿袁,本名仿佛被人忘记了。
平平常常也快乐
其实,悬空而建的白房子里的医生护士们,生活得很寂寞很单调。生活中的每个人,各人为各人活着,各人有各人的苦楚。这是外人很难体会到的。
医疗站的节奏紧张吗?确实紧张。抢救起病人来巴不得一个人顶两个人忙,太阳拽着月亮,可可西里没有了昼夜之分。
医疗站的节奏松缓吗?确实松缓。有时候,门前的青藏公路上断了来往的汽车,没有人踏进医疗站的门槛,死寂沉重地笼罩着白衣战士的心。特别是夜晚,整个可可西里蜷缩在夜色里打盹。白房子已经在此时消失了自己的颜色……
熬死人的无人区的昼夜啊!
慢慢地,这些医务人员终于费尽脑汁地琢磨出了找乐的办法:自己做饭吃。
把吃饭作为找乐的事这恐怕只有在可可西里能见到。人在平庸的日子里,做出任何一件在局外人看来很无聊的事都是合情在理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无聊不是生活中没有女性。因为这是发生在一男二女间的事。那么该倒过来说了,缺少男性。
开初,医疗站一间简陋的小食堂包揽了全站所有男男女女的吃饭问题。上顿下顿毫不例外都是一成不变的老三样:白菜、萝卜、土豆丝。能有不吃腻的一天吗?胡明、叶萍、阿袁是第一个向这种淡而无味的伙食宣战先行者。二女一男,自由结社,组成一个单独的伙食单位,另起炉灶,自己做饭,他们把这叫单身汉里的“临时家庭”。胡明是家庭主男。主妇呢?暂时空缺。
第一个“临时家庭”一亮相,接着,相继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在此自然只陈述第一个了。
不用说,明明是厨房的大师傅丁,负责炒菜,做主食。叶萍专管淘米、洗菜。剩下的那位女士,什么活儿也不会干,专门负责吃——她从小就很少干家务活,来到可可西里高山反应比别人都严重,也无心“补课”了。胡明很大度,用能包容一切的口吻说:“阿袁,你也别不好意思,任何事情都是两个方面,红与白,闲和忙。合理合法。就拿我们这个家庭来说吧,总得有人剥削别人,也得有人被人剥削,我和叶萍就心甘情愿地受你剥削一次吧。你就放开肚皮吃,吃多少我们都保障供应。”阿袁受之有愧,说:“胡哥,你这是损你的傻妹子吧!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我要让你对我刮目相看。阿袁也有两只手,绝不坐着吃闲饭!”这是****中的语言,她也学会了。
胡明高人一筹的地方如果仅仅在于把菜炒得香喷喷,让两个小妹吃得满嘴流油,那他这个家庭主男不能算完全称职,早该引咎辞职了。他的突出长处是会幽默,逗你玩。也怪,只要一掌勺,他满脑子都是笑话,随便崩出一个都会让你捧腹大笑。你看,这会儿他要卖弄他的炒菜绝活了。他把锅端起,抖了一下,菜便从锅底腾起在空中翻了个跟斗,又浇到锅里,一丁点儿也不外撒。他说:
“别看这一手,你们要掌握它,且学着呢!我是拜了3个师傅,磕了三七二十一个响头,又练了七七四十九天,才算马马虎虎地能让菜在锅里翻身了。对啦,这叫翻身,不叫翻跟斗,孙悟空才叫翻跟斗。”
叶萍哪里信他这一套瞎掰,便打破沙锅问到底:“姓胡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从师的是哪3个师傅?”
他十分严肃地回答:“我妈算一个,我奶奶也算一个,外加我们隔壁的二大爷,这不是3个师傅吗?”
阿袁听了像被针尖戳了一下尖叫起来:“我的妈呀,这都是些什么角色,大老娘们,老少爷们!这样的厨师用火车皮都拉不完。”
叶萍哭笑不得,她从胡明手里夺过炒菜铲:“就你这两下,谁还不会?”她说着便端起锅就撂菜,第一下没成功,又撂第二下。没想,连锅带菜一起扣在了炉子卜,“扑哧”一下,满屋都像着了火,喷散着油烟味。
胡明着急了,赶紧收拾残局。叶萍吓得双手抱着头直啷啷。阿袁在一夯抱怨:肚子早饿得咕咕叫,这一来又得拖延开饭时间了。这阵子她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勇气加智慧,索性动手做起了饭菜。
完全可以想象得出,阿袁做成的饭菜是什么样!菜是半生不熟,又成又辣。米饭是不稀不稠一锅糊糊……也完全能想象得出,这一顿饭3个人吃得很开心,很充实,有滋有味。毕竟是第一次掌勺做饭,阿袁得意地还喝了几杯,叶萍跟着乐,与阿袁对饮。两人都醉了。
胡明始终很清醒。
当他分别把两个醉女抱到各自的床上时,觉得好沉好沉。女人原来这么沉。是不是醉女更沉?
他很幸福。
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而不是为了吃饭。
“临时家庭”好快乐!正是从那一次起,阿袁有了变化,她不再专门负责吃了,而是接过了叶萍手中的活儿:淘米洗菜,做主食。她对叶萍说:“萍姐,让我干活吧,你歇着,胡明心疼你呢!”嘴里虽然这么说,她的眼睛却一直望着胡明。她希望能换来胡明几句话,胡明却没哼声,光是笑。
后来,外面有一种说法:“临时家庭”有主妇了,她就是叶萍。
叶萍听了没表态,连胡明也像没事似的不说话,只是那么淡淡地笑着。
平平常常的日子继续平平常常着……
流氓狐狸的闹剧
“临时家庭”的男男女女随着日出月落的自然轮回,有苦也有甜地打发着在可可西里单调而漫长的时光。人生在世毕竟不是为吃饭活着,吃饭带来的乐趣总会有限的。
白房子的主人们继续自得其乐地制造幸福。
如何制造?沙梁的赤狐知道。
悬空房的窗户——其实不能算严格意义的窗户,它没有窗棂,只是砌墙时留下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圆洞,里外各有一块堵板。当它洞开时,极像碉堡的枪眼。掀起窗板,浩瀚的戈壁滩就呈现在眼前。在你未走进戈壁对其缺乏了解时,总是把它跟荒凉、单调连在一起。然而,荒凉是客观存在,单调就未必了。
出现在悬空房窗户洞主人眼里的戈壁实实在在是多姿多彩的。
那道并不算高的沙梁,顶多不过百米远,站在窗洞里面连上面被风吹皱的一道道水波纹似的沙折,都看得十分清楚,整齐得好像工艺人用刀刻出来的。沙梁上稀稀落落地生长着一簇簇骆驼草,草棵在风中东摇西恍地滚动着,仿佛随时都会滚跑,但却总是不离原地地滚动。你不能不佩服赤狐用精明的智能选择了这样一个能掩护自己的戏闹场所,它们在骆驼草中间追逐、打滚、撕咬,粗心人很难分清真伪,误把它们当成了草簇。
“临时家庭”的成员几乎每天都要倚窗看赤狐闹沙梁的景致。赤狐出穴嬉闹的时间多是在中午,口头当顶,气温暖暖,玩得才舒畅!
赤狐为什么临人不惧地把嬉闹的场所选在了医疗站窗前的沙梁上?自然是“临时家庭”成员对它们行动的赏心悦目的欣赏,纵容了它们不惧怕人的胆量。
“狼行山脊,狐行山谷”。这句民谚在这里不适了。本来狐狸怕被人发现才走山谷地的,现在既然白房子里的主人情愿参观它们闹腾,滑头狐狸便投其所好,就走上了沙梁。
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隔窗观赏赤狐戏闹的极好机会。起码在阿袁看来是这样。周日,叶萍在病房值班。午后,阿袁敲开胡明的门,轻脚慢步地走了进来。她一把夺过胡明手中的关于治疗高原常见病100例的薄册子,说:“胡哥,你就不知道放松一下,书能把人看呆的!”胡明说:“好我的阿袁小姐,我几乎从早到晚都在病人身边泡着,难得有个看书的时间,怎么会变呆呢?”阿袁不容胡明再说什么,就把他推到窗前,说是沙梁上有好景致看。
只见几簇骆驼草在风中摇晃。
胡明失望地摇摇头,又拿起了书。阿袁却表现得很有耐心:“胡哥,别急,还有好戏没出台呢。”
胡明这才似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说:“阿袁,你真有这样的闲心……”
原来这季节是赤狐发情的时候,每天它们成群结伙地在沙梁上放纵,或者在别的地方干完好事后来这儿“休闲”。亏得阿袁对赤狐的行动观察得如此仔细。
流氓孤狸。
不一会儿一只肥胖胖的赤狐从沙梁那边走了上来。它站定,四下里观望了一下,便用一只前爪洗了洗脸,才慢慢地在沙梁七走着,很是一副酒足饭饱的悠闲样子。
“是只母的!你瞧那眼圈红红的,连屁股也是肿乎乎的,肯定刚做完美事。”阿袁到底是阿袁,别人难以出唇的话,她能说得津津有味。
这时,又一只赤狐爬上了沙梁,它的个头显然小多了,一上来就冲着那只肥胖赤狐跑去。肥胖赤狐躲闪着,跑了,小个头赤狐紧迫不放。
肥胖赤狐跑出好长一段路了,小个头见追上无望了,折回身走了,一直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走出了好远。
肥胖赤狐这时索性不走了,站在沙梁上冲着那只远去的小个头嘿嘿直笑——它也能笑得那么灿烂。
阿袁来劲了,说:“胡哥,上,捉住那家伙,玩它一回。”
“玩?咋玩?”胡明显然也有了兴趣,他放下了手中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