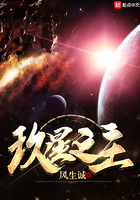夏天,当我再次踏进可可西里草原时,流向远方的楚玛尔河给我送来两幅截然相悖的画面:这边是公安人员正在焚毁数千张缴获的藏羚羊皮;那边是一位年轻靓丽的女歌手怀抱藏羚羊,正动情地唱着一支凄凉的歌。善良与残暴并存的现实,使可可西里这块藏羚羊的家园喜忧参半。
也许因为爱得深沉,也许因为恨得无奈,我的心情是难以言传的复杂。楚玛尔河呀,从你平缓的波纹中我看不到宁静,从你汹涌的浪涛里我听到的是最后的呼唤。
其实,在南、北极之外的世界第三大无人区的可可西里,难得碰见个女性。所以,一位诗人在他的诗里把可可西里诠释为“美丽的藏羚羊”。可可西里在我脑海里最初留下抹不去的印迹,也是缘于藏羚羊。我真的很留恋20世纪50年代末我初进可可西里时看到的情景,那会儿因了藏羚羊满山遍野地奔跑,整个可可西里都显得生机勃勃。我们这些不安分守己的汽车兵,想着招儿和散布在公路两旁的藏羚羊嬉戏。最初它们老远一瞅见汽车就甩开蹄子跑掉,后来见兵们并不伤害它们,就不惊慌了。先是躲在远处仰头张望着兵们,再后来就站在较近的地方望兵,面部的表情也由恐慌换成友好。渐渐的,彼此混熟了,兵们便逗着它们玩。我们开着汽车和藏羚羊赛跑,车快它快,车慢它也慢。每次车过可可西里,如果哪个汽车兵不和藏羚羊逗逗乐,生活仿佛就变得很寡淡。人和野生动物成了朋友,和睦相处,大自然显出了无比的纯美。
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得了,反正是从“**********”后期的某一年某一天开始,寂寞了千百年的可可西里被一阵又一阵古老的杈子枪声激得狼烟四起,随着枪响,不断地有藏羚羊倒下。时间的秒针指到90年代以后,疯狂的偷猎者对藏羚羊的猎杀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此时贪婪者在藏羚羊身上找到了新的生财之道:风靡欧美上流社会的女式披肩“沙图什”是用藏羚羊的羊绒加工编织的。一条“沙图什”披肩重约三白克,需用三百到四百克羊绒,而一只藏羚羊产绒仅一百克左右,因此编织一条披肩就得杀三到四只藏羚羊,而在欧美市场,一条“沙图什”披肩价格高达四万美元,由此可以想象藏羚羊羊绒及其羊皮的价格。为此贪财的偷猎者变得肆无忌惮,罪恶的子弹穿透着可可西里。唐古拉山在高原的寒冷中颤抖。
保护藏羚羊的“西部工委”就是在这时候成立的;三十八岁的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也就是在这时候与偷猎者的搏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接替他职务的妹夫扎巴多杰,不久也倒在偷猎者的枪口下。偷猎者疯了!可可西里荒芜了!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才嘎,忧心忡忡地向我披露了以下几个数字:六七十年代可可西里的藏羚羊约有十万只,到了1999年锐减到七万五千只以下。最新的统计已不足五万只。国际上有这样的共识,如果不抓紧采取有力措施,在中国仅有的世界珍稀野生动物藏羚羊将在五年内灭绝。
2000年夏天,我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索南达杰烈士的纪念碑下,写出了散文《藏羚羊跪拜》,文中写了一只怀胎的藏羚羊向猎人下跪求饶的事。在当年上海的《新民晚报》9月25日的“夜光杯”栏目发表后,引起了较大反响。海内外的四十多家报刊及选本转载了这篇散文。好几个省市还把它列为中学生课外阅读文章,有个省还在他们的高考模拟考试时,选择了从这篇散文中析出问题让考生解答。素不相识的青年歌手艾萌萌就是在朋友的介绍下读了《藏羚羊跪拜》,找到了我。她诚恳地要求我为她写一首关于藏羚羊的歌词,她要唱这首歌。我从这位刚满二十岁的歌手的目光里,感受到了她对可可西里的忧虑,对当前藏羚羊遭戮杀的无比愤慨。我也从她的目光里获得了创作的动力。当夜,我不顾盛夏的暑热,写出了《抱藏羚羊的女孩子》:
有个藏族女孩,
抱着一只藏羚羊,
那是一只死去的小羊。
胸部淌着血,
它失去了妈妈,
女孩怀抱就是它的家。
我听见,
草原响起枪声,
枪声穿透了楚玛尔河,
小羚羊倒在了血泊里。
我看见,
小羊还睁着双眼,
眼角挂着长长泪迹,
女孩抱着小羊默默地走向远方。
很快,作曲家为这首歌词谱了曲。令人十分感动的是,艾萌萌在拍摄《抱藏羚羊的女孩》的MTV时,是冒着高山反应的袭击在可可西里完成的。有人劝她在京城制作一个类似的现场拍摄地,她说:“不,我要抱着真正的藏羚羊唱歌。”当时,我正好在可可西里深入生活。高原的风雪把这位汉族姑娘白净的脸镀成紫赯色。她抱的小藏羚羊是可可西里一户牧民收养的被遗弃的藏羚羊。萌萌穿着藏袍、藏靴、戴着漂亮的藏帽,好神气!
我在歌词里塑造了一位抱着藏羚羊的藏族姑娘,而现实生活中又有了一个抱藏羚羊的汉族姑娘。两个姑娘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她们要唤醒人们的良知:珍爱藏羚羊,保护大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