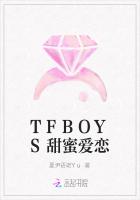几十年间,我先后相识的唐古拉山兵站的站长、指导员、教导员总该有10多位吧!我只在这里记录下4个人的“足迹”,是因为我知道4人也好,10人也罢,都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历史必将继续延续下去——不管这儿的兵站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儿,唐古拉山海拔高度对人类的残酷威胁不会消失。这4位同志所展示的即使点点滴滴的事实,已足以说明我们的指战员在这种常人不堪忍受的环境里是如何地寻求生存的,他们不仅自己生存下来了,还为过往人员在“无人区”里营造了—个比较温暖的家。比如,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些火、水、灯的故事,今天的年轻人会像听“天方夜谭”一样不可理解。有什么办法呢,你不理解它仍然存在着,而且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就是现实。天国里有“天堂”,但那是虚无,是幻影。从唐古拉山走过来的申金仓,虽然在北京已经生活了30多年,可他对往昔那段不算长的唐古拉山兵站的生活已经牢牢地烙印于肌肤里了。他对我说:我不怕别人说我守旧,我经常对自己的孩子重述那段受苦的岁月。因为那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块奠基石,我也希望它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起一定的作用。
申金仓大校是解放军302医院政治部主任。他1969年2月入伍后主动要求到了唐古拉山兵站,被分配到炊事班烧火。离开唐古拉山调到北京时仍然是个士兵,后来才提干。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从风雪唐古拉山走出来的大校,从士兵到大校,在唐古拉山他是第一人。申金仓十分坦率地告诉我,没错,他是主动要求上山的,但是没有想到山上是那样艰苦。领导又让他到炊事班烧火,这更是他没有想到的。也许他有点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了,便连着写了两首诗以表心境:唐古拉山高又高/一年四季冰不消/空气稀薄天气冷/时风时雪真难熬;第二首:唐古拉山高又高/我在山上把火烧/又脏又累真辛苦/脸上黑黑真难瞧。他是高中生,是唐古拉山兵站最高的学历,也只有他才能用这种高级的形式发泄牢骚。
申金仓的这两首诗被领导发现了,他理所当然地要得到同志们的帮助,而且领导会毫不例外地带领他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老三篇”。
32年后申金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十分客观地说:领导帮助我时讲的那些大道理以及毛主席的著作,都对我思想的转变有作用,但是使我安心在炊事班工作的原因是他看到了那些在高原奋战了十多年仍不减斗志的一批又一批老兵;是他看到了那些驾驶着汽车不分昼夜在四千里青藏线上奔驰却从不叫苦的汽车兵;是他看到了一位年近50岁的同样在兵站当炊事员却不顾一身疾病折磨的老职工……都是人,都是父母养的,也都是在同样的地域工作,而且自己吃的苦受的罪并没有人家多,为什么就不能像人家那样无怨无悔地去工作?申金仓的心动了,是受了谴责之后的动心,是得到了在唐古拉山干下去的力量之后的动心。他是个苦孩子,旧社会全家由河南逃难到山西,为糊口先后卖掉了4个姐姐。不说别的,为了报答党对自己一家人的这份救命之恩,他也要干好组织分配的工作。申金仓变了,不但把火烧得旺旺的,而且想方设法节约煤。他受到了表扬和嘉奖。他又写诗了:唐古拉山高又高/我为革命把火烧/艰苦环境炼意志/红心向阳不动摇。
申金仓这三首诗,作为反映他在唐古拉山兵站当兵时思想变化的过程,刊登在1969年9月20日《人民日报》上。
新千年的开春,我在京城见到申金仓时,他特地拿出一张照片让我看。这张照片是和他同年入伍的同乡战友、又一回主动要求上唐古拉山兵站工作的李吉昌同志的留影。照片上的李吉昌正在给过往的同志端饭送菜。可是,申金仓再也见不到这位同在唐古拉山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了,他因脑溢血永远把遗骸留在了高原上……
第六节从五道梁滋生出来的精神财富
写下陈二位这个名字,我心里一阵酸楚。我相信在我写这章的过程中,这种酸楚会一直浸蚀着我的心。
陈二位的这个名字有点奇特,很容易记住,可以说是过耳不忘。再加上这些年来他的工作总是在唐古拉山和昆仑山之间的几个兵站来回调动,我常常在兵站上能听到陈二位的名字或见到他本人,所以我们早就认识了。应该说我们的认识还有一个原因,都是“陕西乡党”。
陈二位是1980年11月从陕西兴平入伍,他是汽车驾驶员出身,后来当了汽车连连长,曾143次去西藏执勤。1996年7月调到格尔木大站,他以为这一回该结束“开着汽车游牧生活”,在格尔木找个稳定单位住下来了。没想到大站田敏社政委对他说:“小乡党,你还得是山去工作呀!”陈二位忙问:“上到哪里?”田政委说:
“到沱沱河兵站当副站长。”陈二位不得不摆了一下“老资格”:“我已经到西藏去过143次了!”田政委说:“我像你这么年轻时还正欢欢实实在线上的兵站干工作呢!”陈二位无话可说了。就这样他背起行李到了长江源头的沱沱河兵站。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久他又平调到五道梁兵站当了副站长。脚跟还没站稳,又调回到沱沱河兵站当站长,算是提拔了一级。一年后,他再次回到五道梁兵站当站长。
陈二位感慨地说:我这是怎么啦,来来回回地总是在可可西里这块地方折腾。当然我明白,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何况最后两次的调动都是让我当主管,自然是对我寄予希望的。
正因为来回不断地呆了好些地方,再加上他在汽车连队时又跑了不少兵站,这样一比较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青藏线上最数五道梁高山反应厉害。
如果就这个结论,那没有什么可说的,许多“青藏线人”都有同感,五道梁这个地方自然条件确实非常恶劣。要不一代一代的高原人怎么会留下了这样的话:“不冻泵得了命,五道梁要了命”、“到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问题是陈二位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体会:我跑遍了青藏线上的兵站,只有在唐古拉山兵站感到最舒服,能吃能睡,有时还可以运动运动。陈二位的这一点认识恐怕没几个人敢苟同。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但这并不影响他对五道梁所下的那个结论。
我问二位:你能不能给我具体地讲讲五道梁这地方对人的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这样我才信服你说的这儿的高山反应最厉害这句话。
二位答:我如果笼统地给你说些情况,比如说来到这里你会头疼呀,呕吐呀,睡不着觉呀,脱落头发呀,性功能减退呀,等等,仍然是个很抽象的概念。现在我就给你讲五道梁兵站两个战士的事情,你会明白五道梁到底是怎么摧残人的身体和精神的。
陈二位就这样给我讲起来了……
他叫朱扬志,当兵11年了,绝对的老兵。他的正式职务是勤杂班班长,具体工作是在发电房管理发电机。自从青藏公路沿线的兵站结束了点蜡烛和用煤油灯照明的日子以后,各个兵站都建起了发电房,它是全兵站光明和动力的源泉,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朱扬志能在五道梁兵站当11年兵,就足以说明领导对发电房有多看重了。培养一个这方面的技术人才不是那么容易的,让他多超期服役几年本是情理之中的事。问题是在五道梁生活的时间长了,这个特殊环境就把他塑造成了另外一个人。朱扬志原本就是个很内向的兵,自从他一个人成天钻在发电房孤守着一台喧闹不止的发电机以后,性格就变得更怪癖了。他除了吃饭来到食堂、睡觉回到宿舍外,所有的时间全在发电房里泡着。同志们最先发现他性格上的变化是你给他讲事情时,他总是爱理不爱理的样子,讲完了,他也很少表态。时间久了,大家才看出点门道了,一是他确实不大喜欢与别人交谈,二是他的耳朵好像出了点毛病,耳背,听不大清楚别人的话。这两点相加,就使人感到他这个人很冷淡。
冷淡就是迟钝,反应慢。平时的每天里他总是静坐在发电房的小凳上,呆呆的,从不主动找人搭话。但是,在另一些别人认为并不成问题的事上,他又斤斤计较,表现得十分敏感。一次,他吃饭时剩了些饭菜,倒掉了。这件事让陈二位看见了。这种情况并非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陈二位觉得有必要讲一讲,以引起大家注意。
当晚点名时,二位就提出了要大家重视节约粮食。说每粒粮食都来得不易,他当场给大家背诵了“锄禾日当午”那首古诗。陈二位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字,他是作为一种倾向性问题提出来,也是尽他当站长的职责。朱扬志却受不了啦,躺下伸腿不上班了,还要卫生员给他送安眠药,流露出不想活下去了的意思。陈二位不明其因,便找到朱扬志问他是否病了,朱说没病。陈二位以为他是累着了,就说,小朱,你歇歇就快去上班吧!
谁知,朱扬志第一天没上班,第二天也没上班,第三天还是没有上班。别人给陈二位传话,朱扬志躺倒不上班与那天点名时的批评有关。二位一听这问题严重了,赶紧找到小朱说明情况,也带有几分道歉的意思。他说,小朱,是不是我批评的太重了?朱扬志不说话。陈二位又说,小朱,我批评的也不是你一个人,要大家都注意节约粮食。小朱还是不吭声。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问二位:站长,你念的那首诗是什么意思?二位说:那是一首古诗,是要人们知道我们吃的每粒粮食都是劳动人民用汗水换来的,所以要特别爱惜。小朱说:那诗不是专门责备地主的?二位说:哪里呀,爱惜粮食是每个人应有的美德。小朱放心了,说:那就行了,站长我会爱惜粮食的。那天倒掉剩饭剩菜是我的不对。
陈二位讲到这里,一声长叹,对我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五道梁这地方呆久了把好人也熬成这么个半傻半呆的样儿了。你问这儿是什么样水土?也许这应该是专家们回答的问题,我只能说出个大概,这里是青藏高原八百里永冻层的一部分,地处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边缘。此地的水不能食用,因为水里寄生着一种像小米粒的1/3那么小的红虫,开水也煮不死,甚至越煮它越生存得活跃。说是不能食用,我们既然住在这里还得吃这里的水。一年四季屋里都得生着火。还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人在这里住上二三年后,掉头发。你看,”二位说着伸手在自己的头上抓了一把,果然手心落下不少头发束。“你到我们站上走一圈看看去吧,不少老兵都成了秃顶了!朱扬志的头发都快掉光了!”
朱扬志岂止是掉头发呢?那大概是他来到五道梁的第8个年头吧,他的右脚突然疼了起来,脚心和腿肚抽搐着,一着地就疼。
站上的医生检查了几次都没有查出原因,他又到格尔木找了几个医生也没说出个名堂。他们只给了些药,说:注意保暖,多活动活动,不碍大事。也确实没要了命,是不是这就是不碍大事?后来疼痛倒是消失了,但是却给小朱落下了个后遗症,走起路来总是一颠一跛的,那只右腿总像是少了一截。为什么好端端的腿会变成这个样?谁也说不清楚。
朱扬志探亲回到老家,家里人问他,扬志,你这腿是怎么啦?
他说,不知道。家人又问,看过医生没有。他说,看过。家人继续问,医生没说这是什么病?他说,医生也不知道。家人总想弄个明白,再问,你还愿意在五道梁那个地方干下去吗?这回小朱再也不说不知道了,他流出了眼泪,说了下面一席话:
“老爹老妈,你怎么不早这么问儿子呢?我确实是连一天也不想在那个地方再干下去了,可是换的一茬又一茬的领导总是说,发电机房是兵站的心脏,离不开儿呀!我教了几个徒弟,他们都没有出师。再有,家里生活困难,儿在那儿一个月可以拿到近2000元的工资,帮家里解决点困难。如果我退伍回了家,谁给你们挣这么一笔钱……”
老爹老妈一话也不啃了。
朱扬志继续在五道梁兵站的发电房干着。2000年是他服役的第12个年头了!
朱扬志的故事还没有完,只要他在五道梁呆一天,他就会创造自己的故事。
我说,二位,不是还有一个战士吗,你再讲讲他的故事。
他说,另一个战士叫莫伯军,汽车驾驶员,也是个老兵了,1991年从湘西凤凰县入伍,土家族,作家沈从文的老乡。这个兵性情暴躁,特别讲哥们义气……
莫伯军与别的老兵不同之处,他是“带着家属”上五道梁的。
当然他这个带家属是没办法的办法,所以应该用引号引着,按规定志愿兵是不能带家属的,可是小莫却是非带不可,所以便破了例。他的爱人是河南人,不习惯湘两土家族的生活,只有跟着他长年住在五道梁兵站。他们的女儿莎莎就是在五道梁出生的,已经5岁了,是地地道道的五道梁人。莎莎像棵缺乏营养的苗儿,瘦瘦弱弱,个头很低,根本不像5岁的娃儿。她整天在兵站的院子里跑来跑去,倒也给这寂寞荒凉的地方增添了几分难得的生机。
小莫一直不愿意在五道梁兵站干下去,道理很简单,他嫌这儿太苫,说,长期呆下去,要折寿。有战友劝他:小莫,你小子不要光想到折寿,还应该看到你在这儿服役人民一月给你2000元的津贴,这不也是很馋人的事吗?他的回答很干脆:只要领导批准我退伍,我还是会心甘情愿地舍弃这2000元。土家人有一句俗话,只要活着,一切都会从无到有。
然而,领导就是不批准小莫退伍。原因也很简单单:莫是个开车技术很棒的司机。在这样一个偏僻的、交通工具匮乏的兵站上,没有他这样一个单独放出去开车能完成任务的司机,领导怎么会放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