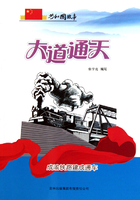见稿纸上写下此题,丈夫站在身后窃笑,说以我那臭棋作此棋(奇)文果真是奇之又奇了,刊登出去难免不遭长安文人雅士耻笑。我说不怕,正因不会下棋,写此棋文才更有人看,成了内行再写,那只有刊在棋类杂志上,让方家们去评论了。他说此言虽不无道理,但不知下文如何作法。我说秦岭大梁上那盘棋是必写的,因那是我弈道精神之所在,跟日本武士道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又笑,说如此说来却也该写。
去年夏天,我去秦岭搜集素材,适值暑假,丈夫便与我一同前往。一日晚饭后,二人在山上下棋(无樵夫观赏),没走几步,我的老将就被将死,情急之时,我指着落下的夕阳和纷乱的群山说:棋有善阵者不战,善败者不乱一说,始以正合,终以奇胜,将军虽去,大树未必飘零,壮士不还,寒风也未必萧瑟。而今老将虽死,尚有卒众英勇奋战,力夺对垒之帅,困兽犹斗,何况万马千军。丈夫一拱手说,领教了,便继续与无将之军作战。那一局杀得十分惨烈,最终只落得士绝象死,车马无声,偌大秦岭梁上唯两只小卒在棋盘上纵横驰骋。他起身赞曰:“精神可嘉,精神可嘉,此棋配以此时此景更显悲壮,堪人《中国名局棋谱》矣。我尤不服,说敢与我作黑白战么?他言不敢,又言好男不与女斗,好人不与狗斗……”
我爱围棋,水平与前述象棋相差无几,且懒懒散散不背定式,大大咧咧不计输赢,随手而下,不思而应,全无别人惴惴小心,如临渊谷的谨慎与思虑。文友中会围棋者不少,我敢与之交手的却不多,但爱看别人下,且有瘾。去年省作协在大厦开四届代表会,常见有人逃会,躲在房内布阵运子,任凭会场上谈论什么“大气魄大作品大作家”而全然不顾。那日,见几位“大作家”着了背心蹲在地上开战,便也凑上去看。只见双方犬牙交错,短兵相接,攻守交替,触目惊心。战者面色铁青,咬牙切齿;观者大汗淋漓,不敢言传。遂思量,观者战者皆省内乃至国内名士,能把棋下到这种赤膊上阵的份儿上也堪称陕西文坛一绝了。想那历代文人,取梅竹掩。映之处,处高山流水之旁,宽服展袖,淡泊清心,以黑白相搏,何等儒雅,何等飘逸,而轮到我辈文人,不知为何却变作这等模样。
北京的白描曾与我在北郊共同执笔一电视剧。他自言善弈,问为几段,答曰五段,我遂吓得再不敢提棋之半字。据我所知,丹舟君围棋下得不错,才是准初段,我已不敢与之交战,眼前这位是五段,当然更得退避三舍了。现在想来,白描君之言未必都属实,其中难免没有先声夺人之势。写至此处,立即打电话问丹舟,以解疑惑。恰巧丹舟与贾平凹正在家中对弈。平凹闻言,大呼言过其实,说白描君不过师从五段,只数日便不再学,那五段乃是师傅而非白描。我遂明白白描系诚心唬我女流之辈是了。
在国内似乎什么都伯,主要是因了这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走出国门,一切顾虑全都打消,呈勇猛无畏状。客居扶桑时,留学生们常在一处摇头晃脑地谈棋,我亦在其中猛吹神侃。
出访福岛时,曾遇酿酒界资本家高田宗彦,视其为大款,必不懂棋,便有意将他一军,大谈围棋之道,贵乎严谨,虽黑白数子却备天地之理,内中精髓与宇宙、社会相通……高田笑而不语,将身边小桌盖布取了,此桌竟是一精美棋盘!其随手又拈一黑子放在左上角星位之上,稍候我出子布局。我没料到高田会来这一手,暗自叫苦,时已无路可退,只有硬着头皮与鬼子相搏了。遂相对跪坐蒲团之上,取一白子,在棋盘上飞舞数圈,最终落正中天元之处。高田一愣,思索良久,问是什么战法,我言此乃名局之一招,效吴某某是也,虽有金边银角草肚皮一说,然君不知高者在腹,下者在边,中者在角之理么?高田无言,在白子边又置一子,于是双方舍弃四周,专在方阵中心部鏖战。知鬼子高田从未与中国人对过弈,我更放宽心肠,凡于我有利者一概冠以“中国规则,无可更改”。这样一来,在我信马由缰的下法前,高田变得稀里糊涂,不知所措,甚至连我的疏漏也被他认作“弃小而不救,有图大之心”。然对方毕竟是老手,很快看破我之根底,遂戏掌中之物般拿我开涮。我意引征,反为其补棋足厚,我两生欲连,则为其拦腰斩断,几手下来便阵脚大乱,击左而不能顾右,攻后而不能瞻前,招招失误,步步不利,眼见黑势在迅速扩大,白棋已无力回天,任何“中国规则”皆无济于事,不过苟延残喘,空耗时间而已。虽是冬月,我竟热汗淋淋,耳赤面红,自知把中国人的脸面丢尽,把中国围棋的名声也丢尽了。唉,亏得前头有聂卫平、马晓春们扛着,否则人家会视中国棋界无人矣。
及至惨兮兮下完那盘棋,我才发现墙上挂着日本棋院为高田颁发的段位证书,不禁埋怨自己一时鬼迷心窍,瞎了眼睛。更恼的是这位高田君的做法竟与白描君相反,不显山露水却变着法儿地让你上当受骗,一步步往圈里钻。看来,为人处世还得多长几个心眼儿,免得再出乖露丑,真应了清代吴瑞征先生之言:盖人世之险阻,世态之翻复,物情之变幻,可以一弈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