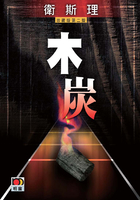“理都对着哩,可不是没粮食嘛。”甲长们说。
“没粮食的拿钱来抵。总不能说一句‘没粮食’就没粮食了吧,那要你们这些人弄啥哩?”警务员也很不高兴。上头的任务顶在身上,谁心里也不舒坦,咱说一百二十圈,不都是为了自己的饭碗吗?
章守信回到家来,心里老不痛快。他管着的十几户人家,可能有一多半交不出粮食,没有粮食的人家,自然也都是没钱的。
抗了几天,他想出一个法,东邻居章四海是村上富户,家里五六十亩地,还开着豆腐房,每天都能磨五六块豆腐,放家里卖两块,由他大孩游乡卖几块,见天他都能见豆子见钱。他想叫他先给拿不出的人家借些粮食。他来到东邻,叫声“四海叔”。
四海叔没有立时答应他,说:“今年地里都没收,可家里使的人都干了一年了,得先紧着给他们不是?我向来不亏人家,这几天他们也都说了,眼看家里就揭不开锅了,有的都拿走一些粮食了。我得先顾住自己的事,才能给旁人借呀。”
他说的都在理上,章守信不能再说啥。他知道这是章四海耍手腕,他家存粮多的是。
章守信第二天又来到院子里,章四海迎出南屋说:“不中了,不中了,给了使的人以后,留的就不多了,你爷一听说再要从囤里挖粮食,气得日撅我一黑,他说家里没有存粮,不胜叫他死了算了。”他说着,用手指了指堂屋,他的老父亲近两年来,有些半身不遂,不轻易出门,总是在堂屋躺着。
章守信又说些商量的话,都被他好言好语地给堵回去了。章四海心里自有主意,他想等这事再拖一拖看,他听游乡卖豆腐的大孩说,今年粮食越来越主贵了,北乡繁阳镇上,有一户粮食多的人家,用五六十斤麦就换一亩地,就这还是有人拿着地契来给他换。肚子不等人啊。
章四海叹口气:“我的侄呀,我知你是好心,为着大家好,为着完成上边的任务,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瞅瞅我这一院子的人,东屋西屋,堂屋南屋,还有西院里的牲口,都是人,都是嘴,我问问你,恁家有没有给人家交的呀?”
“俺家里嘛,自己不吃也得交上去,就算有吧。”
“那就妥了。侄呀,只要你说是恁爹恁娘恁孩没啥吃的,你拿上斗往俺粮食囤里挖了,剩得再少,也有你的,别的,我顾不了那么多。”
过了些时日,警务员又来了。章守信的这十几户交了一半子。那一半子又没粮食又没钱。警务员叹口气,临走前对章守信说:“再想办法吧,反正我得天天来,完不成任务,咱俩日子都不好过。”
那一半子人家这挤那磨地攒着。章四海稳坐家中,他知道那些人没法的时候,会来找他。
死活交不上粮食来,章守信急得没法,闪动着嘴上的燎泡给警务员说:“你看咋处置吧,我不管了。”
“你说不管就不管了?你是大家选出来的甲长。交不上粮食,上面拿我是问,我也轻饶不了你。”警务员用手点他的鼻子,章守信一拳上去,那人倒在地上,血从鼻子里流出来,扑上来要与他撕扯,可哪里是章守信的对手,他只一推,那人又一骨碌倒在地上。众人忙上来劝的劝,哄的哄。
“你还反了你,完不成任务,还打人,你就等着吧。”警务员爬起来,自己拍拍身上的土,抹一把泪走了。
“你这二杆子,你可把事惹了。”长生大爷心疼地说他。
其实,那一拳一出去,他就后悔了。当时他只想着,谁敢这样指着我的鼻子说话呢,见那人鼻子流血,他又觉得是自己不对。
“咱完不成粮,还打人,这就够着定罪了。”长生大爷说。
“定定去,有本事把我绳了去,我还省心了,还有地方管饭了。”他嘴上强硬,心里也不是味。
章槐已经跑回家学了这事。章守信回到家的时候,季瓷正在生他的气,少不了跟娘一起将他数落一番,他闷闷地骨堆到灶火门口不吭气。晌午饭后,季瓷手巾里兜了几个鸡蛋到北边双周村。这里一个保长的女人娘家是小季湾的,与季瓷一辈,在娘家时两人相好。季瓷想那保长姐夫跟上边能说上话,叫好言劝劝那挨打的人,莫要追究了,章守信终究是个病人,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过了两天,那警务员肿着一张脸又来了。
“哼,你可记着,你打了我,我公务在身,不与你一般见识,可你有本事这辈子别从俺庄街里过。这一宗不与你说,粮食还得交,交不上来,我就把你交到上面去,到那时,你有本事再去打吧。”
转一百二十圈,还得交粮食。长生大爷家人多,每个儿子都又生了好多孩子,他跟着大孩聚财过,聚财的女人连生十几个,成了八个,绳闺女就是其中一个。他家里的粮食是最难收的,东凑西借还是不够。章守信从自己家里把粮食底挖了挖,一下拿给了聚财。他总觉得,是绳这闺女救了他的命。“拿走吧,拿走了,我就不信,我章守信一家能饿死。”背过人,他给季瓷说,“天无绝人之路,有我在,就不叫你们挨饿。”
果然,同村有人来到章四海家里,愿意用地换他的粮食。
你谁都能哄,你哄不了自己的肚子。肚子像不听话的小孩,黑天白里地闹人,天天鸣叫着,整个村子白天黑夜都是肚子鸣叫的声音。
天又下起了连阴雨,地泡在雨水里,苞谷种不进去。一连下了二十多天,颍河水再次漫溢出来。小季湾、河西尹的街里又变成一条河。等到水慢慢退去,已经过了种苞谷的时候,强着点了进去,苗芽也长得不好,细细瘦瘦的。
这是老天爷要收人了。老天爷过几十年就得收一回人,因为人总是要不停地作恶,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可是老天爷呀,你睁睁眼,你为啥总是把可怜人收走,那些赖人还是有吃有喝,活得好好的,饿死的为啥总是我们穷人?
于枝兰托人送来一袋子小麦,一家人如获至宝,却稳稳地放着,一次只磨一小点,也不箩了,连同麸皮一起,配着点红薯干、干红薯秧磨碎了吃。那红薯秧本是喂牲口的,牲口卖了,买成粮食,猪卖了,买成粮食,能卖的东西全卖掉,换成粮食,粮食成了世上最主贵的东西。那两头猪从圈里往外赶的时候,章守信的娘说,我真想趴到猪屁股上咬一口。
章柿已经在村小学上到二年级了。学校里给学生发过两回吃的,第一回是一小包饼干,第二回是一罐奶酪,上面都写着洋文。老师要不说这是奶酪,就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老师还说这是美国人给的,美国人帮助中国人打日本人,还救济中国的小学生。章柿把那罐奶酪交给爹,叫给弄开,一家六口人,六个脑袋凑到一堆,章守信拿把切菜刀好容易撬开了那个铁皮家伙,一种奇异的气味扑出来。章槐奔到灶火拿来个调羹勺,挖了一点,放到嘴里,一股子酸怪味,可是现在顾不得了,只要是吃的就中。
庙门口,常有孩子围着外号叫烧包的,听他读《西游记》,讲《水浒传》。
烧包其实年龄不大,可他留起了胡子,执着地穿着补了好多补丁的长衫,表明他的出身或者见识与一般庄稼人不同。据他自己说,他祖上都是识字人,有留下来的一套《西游记》和一本没皮的《水浒传》为证。烧包算是读了几年书,不知读得怎样,总之是肩也不能挑了手也不能提了,家里的地一代代经管不好也都变成人家的了,他常年在学校门口卖点小东西,挣小孩子的钱。大人都没钱花,何况小孩子,手里能有几个小钱?等到咬咬牙送到他手里,那利润就少得可怜,基本上常年顾不住一家人的生活。可人家长衫不脱气派不倒,时间长了人送外号“烧包”,像章柿这样大的孩子压根就不知他的真名,认为他生下来就叫烧包。当面叫到了他,他也不恼,他说,不是谁想烧就能烧的,那得祖上有家业,那得能掀开《西游记》不打绊地念下去,那得合上《水浒传》也能说出里面谁跟谁是咋回事。
现在,大家爱围住烧包,听他念仅有的一本《水浒传》,听武松打虎前叫酒保上肉的场面。瞅瞅,人家武二郎那叫一个气派,吃肉都是论斤来。孩子们越想听,越难受,越难受,还越想听。
章柿放学回到家里,刚想问娘要吃的,娘叫他:“柿,过来,我给你说个事。”
他走过去,季瓷抚摸着他的头,眼睛红红的:“以后,再也见不到你绳姐了。”
“为啥?”
“卖了。”
“卖到哪儿了?”
“卖到西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