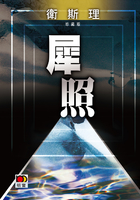七六四团团长沈嘎岳荃带着从嘉善县长手里取来那串金色钥匙后,穿梭于一片密密麻麻的地堡群中,按牌号次第打开了那些紧锁的铁门。在部队进入工事后,发现工事之间联通的交通沟窄而浅,出入容易暴露目标,于是一面命令部分兄弟警戎敌人,一面又令其余的弟兄赶修交通沟工事。下午三点,日军水上飞机的一个大队向嘉善飞来,在前沿阵地和县城投下了数百枚炸弹,六百多间房屋被炸毁,平坦的田野瞬间千疮百孔。随后而来的,便是敌人整齐的步兵,他们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阵地发起了集团进攻。
布阵于七六四团前方的东北军一0九师葛团纷纷向后方溃退了,他们的团长默声不语,在路过沈嘎岳荃团长的身边时也只点了一下头。
“您好。”
“您好。”
一0九师六五四团刚刚退出沈团防线,追击之敌就气势汹汹地席卷而来了。他们约有八百余人排成方队,沿公路和铁路两旁行进。但在离沈嘎岳荃团约二三十米远的一个营地,几近遭到了灭顶之灾。据守这里的正好是白神兵的那个神兵队,他们像鬼一样满脸涂血地从地下冒出来,从天上掉下来,“打不死!打不死!”他们咦咦哇哇横刀就砍,人头落地身首分离就像风吹蒲公英那样简单。日军被这种架势振懵了脑袋,也哇哇啦啦地乱叫起来,但他们的大刀在神兵队的身上并没有发挥刀的效应,他们模仿的声音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打必死,打必死!”
“呀噜巴给——”一个日军联队长在丢掉了一只眼睛后疯狂地嚎叫起来,但并没有向前冲而是向后退去。
“妈个巴子——”白神兵以着同样的口吻回应他们,还朝他们的背影吐了一些口水。
午后四点左右,日军又派出了他们的制空优势飞机,对白神兵的阵地进行了狂轰滥炸,一小时内有三百余枚炸弹在不到一华里的土地上开花,土地被翻犁一次,白神兵和他的士兵成了埋于地下以火药当肥料的种子。但白神兵仍从身腰摸出一块令牌,“先天大神,至善至灵,呼风化火,唤雨行云,丑丁助我,六甲护身,五雷五虎,紫薇降临。天兵天将,千呼千应,万叫万应,不叫自应,阴兵神将,大显威灵,大刀向前指,万物化灰尘……”白神兵气息奄奄,已经没有了指天化地的气力。
有士兵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沈嘎岳荃:“完了,白神兵这次神不起来了,但愿菩萨保佑,他不是在地底下长蛆而是再发一次芽。”那个士兵流着眼泪说,又走到一边去,伤心得哭过没完。
但不久,沈嘎岳荃在擦拭他的枪时,耳边清晰地听到了“打不死,打不死!”的声音。“是白神兵!”他突然跳了起来,奔到战士们跟前急于把这消息告诉大家:“我不知道这是怎样的奇迹,但他确实还活着,我们很快会找到他的。”他把这个感觉完全当成了事实,还派出了七六三团吴嘎光烈营向白神兵的阵地靠近。吴嘎光烈率队进入阵地时,果然看到白神兵的弟兄们在和日军扭着一团。他当机立断地命令大家上好刺刀。他们凭着的旺盛精力和英勇善战的气势最后迫使敌人一次又一次罢战收兵,向后溃退。在横尸遍野中,吴嘎光烈清点了一下人马,白神兵的队伍仅剩二十余人,连长白云胜、藤传道和全营所有排长全部阵亡。他也来不及悲伤,吩咐把那些残腿断臂还在流血的士兵抬出阵地抢救治疗。这时沈团长也带来了一排人赶来救护,他从一滩污泥中拉出的一个人戏剧性证实了他的预感。
白神兵还活着,但却成了一个血人,叫花子一样衣服被弄得得条不成条,片不成片,赤着双脚,虽然不省人事,被砍得断得只剩皮的一只手还不在意似地握着那把大刀。
沈团长弯下腰时发现他还在呼吸,他喊来卫生员一起擦掉血迹包扎伤口,在翻动中白神兵醒了过来,他喉咙里发出轻微的嗫嚅声:“打不死,打不死!”
“算了吧,你已经死过一次了。”沈团长说,脱下自己身上的一件干净衣服盖到了白神兵的身上。
由于七六四团的顽强抵抗,日军一直不能打开西进的通道,他们当然不明白这支筸军从戎的信念历史和不给家乡人丢脸的单纯初衷,更不愿意把原因归咎于钢铁铸成一样的筸军意志,而是归咎于多层次立体防御体系的坚固的钢筋水泥地堡。并觉得如果继续沿公路铁路两旁大道进击,恐怕付出再大代价也难于得手或是得不偿失。他们在经过几小时的商量论证后,决定避实就虚,攻其不备。他们为此列出了首先拿下不远处一座南星桥,然后包抄铁道、公路国防工事后侧的计划。他们对这一计划实施后将取得的胜利深信不疑,甚至连如何留出一部兵力对两条大道阵地进行佯攻,造成他们用兵重点并没有改变的假象都设计好了。
“等着吧,那些支那狗屎!”痛还没有消散的独眼联队长愤愤地说。
第二天清晨五点钟,日军的一个少将放出一匹东洋大马,亲自率一千多人马向南星桥直奔而来。他似乎决心要在此地与中国军队决一雌雄。南星桥是一座横跨河流之上的石砌圆拱桥,长二十多米,是除铁路和公路以外连接南星港的重要通道,桥头偏西和偏北各有地堡一座,当初是设计人员为护卫石桥而设置的。驻扎这里的是三八二旅的一个营,他们仅有一挺轻机枪和数支步枪,桥上尚不能构筑简易工事掩体。日军在以飞机轮番轰炸后,又在机枪的掩护下,蜂拥而上了。尽管谭旅长非常果断而灵敏地调来兵力火速增援,赴汤蹈火,但也渐渐不支。他给匡嘎惹巴打了电话。
“我恐怕难以支撑两小时了,”他报告说。
“屁话,如果支撑不到两小时,丢失阵地,提你的脑袋来见我!”匡嘎惹巴吼道。他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怀表,那时离守护嘉善阻击日军四天的任务正好还差两小时。
事实上,到了第七天,匡嘎惹巴也没有接到撤离的通知。战斗进入到白热化的程度,战士们也报定了一颗死了卵朝天的决心,匡嘎惹巴也亲自上了战场并上好了刺刀。他无法知道以后的结局,但一想起离开家乡镇筸时原师长匡嘎一琼“不要拿镇筸的子弟当炮灰”的话,心里不由得火烧火燎似的难受。那时,匡嘎惹巴甚至带去了匡嘎一琼最保留的黑旗大队,那些被称为黑杀队的士兵打着黑旗,一律着了黑便服、黑头帕、黑腰带、黑帮腿,连看人的眼神都是黑的。
黑旗大队平时所练就的跨越深沟过独木桥攀岩飞越及过硬的武功本领在这里依然发挥了作用,有一个姓侯名汉清的战士居然飞身而上撩倒了那个少将的东洋大马,跌倒的少将在咆哮与怒骂中脸无血色,让人搀扶着避退到了三舍。“真是丢脸,”少将怨气不消地说:“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自嘉善战斗打响,我们对中方在此投入多少兵力,如何部署,部队番号,指挥官是谁,属哪派哪系都知之不详,难怪行动艰难,处处碰壁!”
少将因此派出了敌工情报人员,并让他们务必在很短的时间内搞清底细。很快,那些被派出的人回来了。
“那是一群来自支那南部湘西镇筸的土匪,”敌工人员说,“他们最喜欢的是打家劫舍,最擅长打架斗殴。”
日本少将咬了咬牙,有种恨钢不成铁的感觉。消息传到黑旗队那儿,团长刘嘎耀卿笑得饭都喷到了地上。“老子就是土匪,日你奶奶的!”他说。
南星桥战后,匡嘎惹巴的一二八师又击退了日军不断地往左翼西塘和南北方向的无数次进攻,敌人更为恼羞成怒,甚至派出了强大兵力进攻了城北一二八师的师部。敌强我弱的状况下,七六三团、七六四团的士兵损失过半,七六八团也有一定损失。包括沈团长在内的三位团长受伤,团副两人死亡。受伤及死亡的营、连、排长则是更多了。士兵的尸体就像地堡沟壕边一堆一堆的子弹壳,收尸的人将他们集合起来,堆得和南星桥一样高,血流成河……
在经过六天六夜的苦战后,十五日上午,匡嘎惹巴终于接到了上级下达的撤退命令。
“第一二八师匡嘎惹巴,现命你部于十五日午后六时开移,沿杭善公路往临平转进。”第十集团军的司令官在电话中说。
这真是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当匡嘎惹巴把这一消息告诉给大家时,战士们有了从未有过的轻松,甚至欢闹起来。他们愉快地开始捡拾行装,但在他们以筷勺敲击碗和水壶获得暂时性快乐的鼓乐声中,匡嘎惹巴走了过来。他把自己的军官军用背包往旁边一扔,抖动了披风,严肃地说:“从现在起,我希望我们的筸军弟兄,不要再丢失一兵一卒了!”
事情就是这样,越是担心的事情就越有可能发生,就像怕鬼就会撞着鬼。撤退一直是悄悄有组织有秩序地进行着,先是保证伤病员先行,各旅、团、营、连等务必按规定顺序善后,以保证安全到达预定地点。当行进到六十七号铁桥时,却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
一个当地的做绸布生意的商人先是为日本疯狂入侵和灭绝人性的屠杀吓破了胆,之后又觉得做日本人的生意要比绸布生意划算得多,便开始为五斗米认贼作父,成了汉奸。绸布商装成逃难者从一个通讯兵那儿获取了一二八师动向的情报,然后以数个铜板的价卖给了那位日本少将。
“六十七号铁桥是他们的必经之路,”绸布商又告诉日本佬说,“那是身体的喉咙。”
匡嘎惹巴早也有所防范,他在部队开拔之前即命令留作预备队的七六七团开赴到了六十七号桥的附近,构筑工事,严阵以待。七六七团长期以来一直是他的一枚最珍惜的棋子,除非仗打到生死攸关。团长陈范思想活跃,胆谋兼具,他能深谙每一个士兵的内心,并觉得武器的拙劣与否并不要紧,关键是军心一致才能发挥最强的战斗力,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他所带的六百多名壮士曾在很多次的战役中给这支筸军争足了面子。
“请你们一定记住,我们身上的这颗脑袋不是我们自己的,它是父母的,是妻子儿女的,”陈范在战前的动员会上说,“所以,我们什么都可以不要,但一定要带回去这颗脑袋!”
他在铁桥一带驻兵的房子里堆满了子弹和手榴弹,集中兵力在西桥头和铁路两侧的村子阵地修筑了可以遥相呼应的工事,匡嘎惹巴还派了特务连、辎重连及军官队在桥头布防。一切看起来是那么万无一失。午后七点钟左右,工兵连的一位连长带着全连兄弟在桥头用木板铺设桥面,因为那座桥曾在日军无数次地轰炸中早已面目全非了,桥面裸露的只是几根桥梁的钢筋。这时,敌人出现了。他们从北面的七星桥、干窑镇等地气势汹汹地直奔桥头而来。东面也有一线日军开了猛烈的炮火,以牵制三八二旅和七六八团,企图对一二八师进行夹击。这一晚的宁静被打破了,六十七号桥上更是乱哄哄的一片,成群结队的日本兵挤满了桥面,与筸军们展开了木板的争夺战。日本佬其实也在拿自己的脑袋冒险,仗打到第二天拂晓,用做铺陈桥梁的木板,全换成了他们的尸体,满地的狼藉,这些人中有的被捅了刀子,但更多的被木板砸碎了头。
“你们看看,这完全是他们自己找来的麻烦,”陈范团长当着大家的面这样说,“我们不过是要过一下桥而已,又不是他们家的桥,何必与我们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