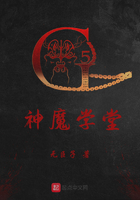消息全无的一年后,在南华山一个背道的山弯里,莫歌象征性为匡嘎云飞做了一个小小的坟茔。坟茔里,摆放着匡嘎云飞的所有用品和玩具。莫歌记住了这个山弯,记住了坟的旁边,长着一棵山茶树。但第三天早上,莫歌在反复哀叹失眠的辗转中,却发现刻着匡嘎云飞生辰八字的那块青铜镜项饰没有放到坟茔里而是落在她的枕头下,之前她一直以为和其他遗物一起埋葬掉了。
对于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匡嘎恩其一无所知。没有一个人告诉他。他写过很多信,一如泥牛如海。他并不明白,是夫人莫歌一点都不愿意身处战争中的丈夫来承受这种有如飞来横祸的苦难,更是因为惭愧无法面对他的一种苦楚。一开始莫歌还读丈夫的信,后来连信也懒得读了。有一次,丈夫又写来了信,他说要亲手送给她一件不同寻常的礼物。
“请猜猜吧,这件宝贝世上绝无仅有。”匡嘎恩其炫耀着说。
她自然猜不出是什么,也不想去猜,她觉得对于自己,什么都不需要了。
“你不用在我身上费心思了,”她想着丈夫,难过地说。
同治七年,匡嘎恩其回任古州镇总兵。八年,奉命署贵州提督。十年,肃清黔匪,自己向皇帝报告,仍然担任总兵职务,但希望能给一些时日回乡休假。
“我已经好几年没回家了,”他在报告中说,“家里的老母妻小孤单过日,幼儿应不识我,我乃忠孝不能两全,望能垂怜。”
皇帝赏了他一块大大的贴金匾额。对于休假之事,只字不提。之后,朝廷将他调往四川建昌镇。赴任。
其实,匡嘎恩其早就感觉到了家里有了一些变化,出了些状况,他心情压抑,经常无故惴惴不安,有一次他从上至下拐弯抹角地寻找到了一个回家的老乡,便问有没有听到匡家的什么情况,老乡说没有,他几次路过那里都想进去看看,但大门一直紧闭,缝隙不露。
“他们把院墙加高了几米,”老乡说。这就是唯一的消息。
在匡嘎恩其赴任的一段时间,他越发忧郁,并明显感到以前自己钢铁般的意志在消蚀,内心倦怠松弛。不过,他没有把这归咎于自己身体上的原因,也没有归罪于多年的积劳成疾,尽管此时全身数十处创伤创病齐发,疼痛难忍。而是归结于一种他自己也说不清、只是隐约感到的东西,即对于家人的如饥似渴的想念和担忧。他渴望拥抱儿子的心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终于,上级准了他的假,并说只要他忙完这一段时间的公务,随时可以动身。
“老子很快可以见到他们啦!”他高兴地有些忘乎所以。
那些日常要做的公务像蛇一样一件件从他手中滑过,他做得疏而不漏,有始有终。家乡有一句话说债不可欠儿可养,他想儿子一定长高了许多,样子也变了。只是这一次不知能否分出大小来。这几年,家里一定发生了不少事,想想老母和夫人,为培养他们费了多少心血吃了多少苦,而自己,却知道无休止地打仗,打了多少年仗啊,从来没有为孩子们操过心,或看看他们病了渴了是否需要熬一副汤药端一杯水。
在即将离开部队回家的前一天晚上,匡嘎恩其从一个珍藏的盒子里拿出了一件物品,他一直想作为不同寻常的礼物送给妻子莫歌,他已保存了许久。可能有些激动,他突然感到两眼发黑,他想可能是这段时间的辛苦劳累而导致暂时性的视力衰退,便躺倒在床上休息。可是不久,他感到头晕脑胀,不可思议的是眼睛却雪一样地亮堂起来,天体通透。他很奇怪有了从未有过的对于儿子面目如此清晰的记忆概念,仿佛就站在他面前,仰着匡嘎家族的脸谱,方脸浓眉,鼻如悬胆,嘴唇执拗。他默默的强辨着他们之间的不同、他们存在的距离以及他们各自的气味。这时,他意想不到地发现了他们身上各异的特质,那就是气味。首先,他感觉到的是匡嘎一琼身上朱砂的气味,那是一种甜甜的血腥的粉质味道,说实话,他不是很喜欢;其次,他闻到了匡嘎云飞身上灰色尘土的气味,这种气味他很熟悉,是一种沙质味道,粗粝而不明是非,盲目而固执强横;他最后闻到的是从匡嘎惹巴身上散发出的菊花的气味,这是一种流质味道,那般温软而令人沉迷。这也是他们兄弟中唯一继承了母亲的血统基因,遗传她固有特质的孩子。
现在,他对他们知道得那样一清二楚了,他想等见到他们,即使闭着眼睛也能知道他们谁是谁了。原来他们是那样的容易分辨。
第二天一早,勤务兵在将一切回家的行装都准备好之后,来敲门喊他起床,但敲了许久都没有回应。勤务兵闯了进去,发现匡嘎恩其的身体横陈着一动不动,嘴闭得很紧,眼睛却睁着,明亮如雪,却停止了呼吸。起初,勤务兵还以为他躺着在思考什么问题,用手拼命在他眼前晃动都没有感应后,确信他已经死了。
“你怎么是这样一个死了也让人觉得还活着的人啊!”勤务兵说,流着眼泪帮他合上了眼睛。
匡嘎恩其的突然瘁死令朝廷有栋梁已倾之感,许多官兵为之伤心悲泪。皇上也有如痛失良驹,在默哀一阵后,下旨沿途由官府接送,棺廓运回镇筸城安葬。
这一年的秋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早,农历十月初九,匡嘎恩其的棺廓在吹吹打打的哀乐声中步出了建昌镇。在未到达家之前,人们没有看到他作为一个死人的任何反应,而对匡嘎恩其来说,这一天同他以前的任何一天都一样,前面是队伍的士兵,后面是士兵的队伍,他仍有如坐阵其间,指挥千军万马。只是因为季节的缘故场景有点凄凉,风声鹤唳。到了第三天,下起了连绵细雨,淅淅沥沥的雨声仿佛上天的哭泣。人们在棺盖上裹上了一层保暖的毛毯,他的勤务兵干脆又加上了那张虎皮宝座的虎皮座垫,那是攻打南京府时劫来的,另一长给了祖母,这一张自从匡嘎恩其得到它后就一直不离屁股。不仅仅是舒服保暖,神奇的是能减轻身体的病痛,这几年匡嘎恩其一直依靠它来治疗因连年征战身体创伤复发的疼痛。“他以后再也不需要了,”勤务兵暗地里说,又用手梳理了一下虎毛。虎皮坐垫随着棺廓起起落落,那些抬棺的人突然觉得轻便起来。那时,离回到家只有半天的路程了。
队伍越过陌生的地界,跨进有如自家门槛的一个名叫张排寨的地方,大家放下来休息,做一些洗脸小便之类的洁身准备,并接受当地官府的接亡迎往。等他们一切就绪再上路时,令人费解的是那口棺廓怎么也抬不起来。雨已经停了,天气不怎么潮湿寒冷,只是围绕在四周到了中午也化不开的大雾使人觉得气闷。抬棺的八个人换了一拨又一拨,就是不见起色,棺廓岿然不动。“他不肯回家啊!”有人猜测,但似乎也找不出理由。这倒惊醒了一路都在悲伤的勤务兵,他突然想起,他是要等他至亲的人来接他了。“去喊他的家人吧!”他说。
匡嘎恩其离开人世并将由官府一路接送回家安葬的消息早几天前就传遍了镇筸城。自从得知这一消息,祖母菊在便不再说话,目光痴呆,脸部肌肉僵硬,家人以为她是暂时性的为悲伤击倒,因为这样的状况曾经在匡家痛失匡嘎云飞后也出现过一次,但不日又恢复过来。莫歌在匡嘎云飞丢失后很长一段时间浸泡在差点淹死在自己的泪水里,之后明白哭并不能换回什么,也不能挽回任何结局时就把眼泪藏进了肚里。这次得知丈夫的死讯,她没有痛哭淋涕,只是全神贯注地为丈夫赶制一件衣服,为一丁点不如意的地方缝了又拆,不厌其烦。她什么也没想,也没发觉落了几天的雨停了,而中午的雾有些大。直到有人到匡府来通报了情况,并说是否由她出面到张排寨接亡时她才如梦初醒。
“我知道了。”她说。
她缝完了丈夫衣服的最后一针,用牙齿咬断了线。管家问他要不要准备一点纸钱酒肉,她说完全用不上这些。她重新梳理了一下头发,换了件还是结婚时的干净衣服就出门了。回头又摸了一下一直看着她的匡嘎惹巴的脸,告诉他说马上就可以见到父亲了。匡嘎惹巴懂事地点了点头,像早就做好了承受这种事实的准备。
“爸爸还好吗?”他说。这时他看到母亲的一张苍白冷漠的脸,上面没有一颗泪水和一点表情。
“当然。”莫歌说。
在莫歌还未到达之前,大家仍为启动棺廓而不懈努力。他们入乡随俗地在当地请了一个巫师,烧香祭酒,于当坊土地神前,大呼亡者名字三声,欲引回家。但这次巫师不明白为什么不灵验了。
莫歌的到来使沉闷的空气天开雾散,那时太阳喷薄而出,强烈的光照竟使棺廓要动起来一样吱嘎作响。因为那么多的人等着,她不可能想着自己的哀伤,只好把思绪转到了其他零散的往事。对于那些往事,她只是不加鉴别的去想,免得那些无法避免的回忆刺痛自己的心。但即使这样,她仍然不由自主地踏进了怀念的陷阱。那些对于丈夫的向往把她的心快撑炸了。她像呼吸一样哼出忧伤的歌——
我夜以继日地想你
我想你比这还多一点点
我无法解释
我内心的一些东西已被瓦解
我不停地想你
不停地想……。
她步态优雅,一如她内心的歌。
“吙咳,起来啊!”人们吼了起来。
奇迹出现了。棺起。一行队伍跟着她轻松上路了。在长满野菊花的山坡上,黄的紫的菊花开得正浓,这让莫歌想起匡嘎恩其第一次带她回家的情景,这种从心中闪过的转瞬即逝的情景对她来说仍是一种享受。“现在,我带着你回家了,”她说。接着,队伍开进了一个到处是不化的雾水空气清新的地带,然后又开到了清浅明澈自然泛着水草的沱江河边。大约五年之前,匡嘎恩其带儿子们曾在这里钓鱼。
下午四点钟,队伍终于进了镇筸城的北门城楼,在官府隆重的迎接仪式举行过后,莫歌拒绝了将由官方举办的丧葬大典,直接将棺木引进了自己的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