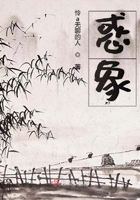徐炎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白色的小收纳袋。
那是他从生下来到现在有过的最大的秘密。
至少,在知道二姐和孙竹喧已经发觉以前,他一直认为,收纳袋里的黑色棋子所意味的东西只是他一个人的秘密。
那枚棋子,由石头做成,黑色,圆润,只比商铺里卖的一般的棋子贵些。
那枚棋子,是徐炎来书院之前在那个人的棋盒里面偷摸出来的。
当年定了去书院后,大姐在他要离开家时,特意喊他去袁府吃顿饭。大姐从小身体不好,但性格柔顺,对于身体上的种种病痛只是一个人忍着,从来没有听她抱怨过。记得那人说过,徐师伯家的大姑娘是个很不错的女子。
长姐如母。徐炎小时候喜欢搬来小板凳坐在大姐床边,听大姐用柔和的嗓音讲故事,或者低低的嘱咐一些话。
前年,大姐嫁到袁家。今年,她的肚皮已经高高隆起,徐、袁两家的长辈欢天喜地。大姐自己也满心欢喜,说,没想到今生能够生下孩子。
吃饭的时候,大姐不停的往他碗里夹菜,不断的嘱咐去了书院要照顾好自己。袁斯良也在,他穿着由最好料子做成的锦衣坐在妻子身边,光彩照人,每个举动中都透着优雅和大气。他对着徐炎,只是微笑着附和妻子,说要什么就写信回来,性子收着些…完全是个可亲的大哥与姐夫。
大姐身子重,需要多休息,吃过饭,袁斯良将她抱回卧室。徐炎一动不动的看着姐夫抱着姐姐进房,目光停留在姐姐微微羞涩但幸福的笑脸上,停留在袁斯良成熟且富有魅力的表情上。
徐炎喜欢看袁斯良扬起的嘴角。
他没有见过第二个人,嘴角向上扬时可以那么好看的。嘴角先拉长,慢慢向上翘,停留,几乎是挨着嘴角边斜上方的地方会出现一个浅浅的小涡。每每看到袁斯良笑,徐炎就想凑上前在他嘴角亲一口,正中酒窝。
亲戚、朋友家里的长辈们说,袁家这一辈虽然只有袁斯良一个儿子,但这一个比十个加起来都好。
听这话的晚辈们没有一个能够开口反驳的,最多鼓着腮帮子暗地里“切”两声。
袁斯良的每一个眼神、表情、动作都散发着被掺杂了野性的优雅,这种野性就像外面裹着一层厚厚糖衣的五石散,首先对你的眼球和味蕾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吞下后浑身飘飘然,如同刚刚飞升的神仙。
从十四岁起,徐炎就在这种飘然感觉中难以自拔。
袁斯良从房间里出来,将徐炎叫到书房内,又嘱咐了很多关于书院里人情世故的话。
书房里摆满了书,文房四宝都是京城澜宝斋里最上等的货色,挂着的狼毛笔里有一支磨损得比较厉害,纸张、砚台和常用的书本摆放在一边,不用伸手就能够得着;案上还有很多公文,高高的垒起来;做装饰的古董每件都很昂贵,并且摆在最合时宜的地方。架子、柜子、桌椅上光洁得能够照出人影,上面镶着金银做装饰,出自京城最有名气的工匠之手。
徐炎坐在袁斯良常坐的檀木椅子上,摆弄他放在桌上的印章,见印章上积满了陈泥,就用木簪子一点点往下刮。他笑道:“烦不烦啊,当真是要当爹的人了,有那么多话留着给你儿子说去。”
袁斯良的食指和拇指习惯性的伸向徐炎的脸,却在抬起后一秒钟之内放下。笑道:“我现在正学着怎么教训儿子。”
徐炎将刮下来的陈泥往袁斯良精致平整的衣裳上扔,道:“你能大我多少!”
发暗的红色陈泥被袁斯良轻轻弹去,落在看不见的地方。扬着嘴角继续他的“教训”实践。
徐炎一手撑在扶椅上,看着对面的人侃侃而谈,猜袁斯良一天要批改多少公文、晚上什么时候才能合眼。
小时候,徐炎就经常看见袁斯良坐在书桌前俯首凝神的样子,英气的眉头微微皱着,两只眼睛里有着时而变换的神色,非常认真。
徐炎每次去找袁斯良,只要看见他在看书,便蹑手蹑脚的走进书房,坐在看书人的对面仔细看他的眉眼,往往要几分钟后,袁斯良才会意识到徐炎的存在。
徐炎问过他,干嘛那么努力,还能没你的饭吃?袁斯良伸出拇指和食指往徐炎脸上一拧,笑问:“从私塾偷跑出来的?先生布置的文章写完没?”
捏在脸上的手指用劲很轻,触感温柔,有时候会觉得一点点痒。
发生在过去时光里的事情就像梦一样,飞速在徐炎脑中闪过。当他看到袁斯良深邃的眼中闪烁着异样的情愫时,知道自己已经盯着袁斯良看太久,忙将头偏到一边,笑道:“知道了,知道了,你快赶上我爹那样啰嗦的了。”
袁斯良走到窗前,和徐炎一起看向院中盛开的马缨花。徐炎乘机从他桌上打开的棋盒里摸了一粒黑色棋子。
房内沉静了一会儿,徐炎感到不自在,起身道:“我还要回去看他们把东西收拾好没,姐夫,帮我跟姐说,我先走了。”
“也好。”袁斯良从窗前朝徐炎走了几步,保持一定距离,点头笑道:“回去时小心些,我叫下人赶车送你。”
徐炎深吸了一口气,刚要转头,袁斯良欲言又止,二人看着对方。
片刻后,徐炎咧着嘴笑道:“我知道,要懂事些。”再拿眼睛将他从头到脚看了一遍。袁斯良只是点头。
大姐嫁到袁家之前,袁斯良对抱着他的徐炎说:“小炎,你要懂事些。”然后将他推开。说这句话时,袁斯良眼中神色极其的复杂,混合着痛苦和坚决。
看着大姐的花轿出门,徐炎对自己说:“你要懂事些。”
大姐嫁给袁斯良之前,徐炎三天两头往袁府跑。
大姐嫁给袁斯良后,徐炎一年之内最多踏进袁府两三次,还是在推脱不过的情况下。
起先家里人很奇怪,说六炎子你不是最缠你袁大哥的吗?徐炎垂下眼睑,啃着酱猪蹄说人家的官越当越高了,一天到晚多忙啊,找他也没什么玩的。
那时徐炎他二姐那时候还没出阁,点着他的额头笑道:“看看人家再看看自己,什么时候你也去弄个官儿来当当。”
徐炎伸手往自己衣服下摆上擦,二姐手指上的力道加重,骂道:“你成叫花子了吗?这可是白色的,沾上去就洗不干净了…”
“洗不干净就洗不干净!”
“成啊,你就这样穿着满大街的走去。”
徐炎扔掉手中啃了大半的蹄髈,嘴都没擦,梗着脖子道:“我现在就去,您瞧好了!”抬起脚往外走,刚出大门就被回来探望双亲的大哥让管家叫了回来。
娘说:“六炎子发什么火呢?”
大哥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臭小子吃撑了呗…要不要挨两下家法消食?”徐炎嚷着往外走,说这就请家法去。
大姐出嫁一年后,有喜了。
娘在家高兴得不得了,吩咐给全府的下人加菜,这个月的工钱长四成。她抹着眼泪跟两旁的丫鬟、婆子们说,家里大姑娘从小身子就遭罪,想不到还能怀上孩子,菩萨保佑啊…张罗着要去寺庙还愿。
徐炎站咋一边,不温不凉的说:“娘,我想去冀州的书院读书。”
徐夫人的脸立马垮下来。说京城的石鼓书院挺好,干嘛跑那么远的地方去,三年都回不了家。
徐炎说我要去,我一定要去。
徐夫人问你去干嘛?
“读书啊,盛材书院的教学天下第一呢,保不齐三年后,儿子中个状元,您就成状元的娘了,多气派!”
徐炎他爹眼中出现欣慰之色,口中嗤笑道:“凭你小子还想当状元呢,薛院长可是很严格的,你别被人家提着扫把赶出来丢我们的脸就行了。”
“哪儿能啊,”徐炎靠在他娘肩上蹭来蹭去,“儿子长那么大还没出过远门呢,娘,让我去读书嘛…”
徐夫人一直反对,娘儿俩说了半天。最后还是徐炎他爹拍板,说反正家里二女儿嫁到了冀州,六炎子过去有照应,再说,送去薛院长手下管教几年也好。
于是,徐炎成功的离开了袁斯良所在的地方。
书院是年轻人的天下,徐炎很快认识了新的朋友,每天读书、玩耍,日子过得挺愉快,不像在家的时候,经常猛然听见某个人的名字,瞬间就搞得心里十分郁闷。
夜深人静的时候,徐炎常常拿出那枚棋子在手中摩挲,不知道袁斯良有没有发现一盒的黑子里少了一颗?
刚来书院徐炎接到家里来信,说大姐生了一对双胞胎,都是儿子,胖乎乎的很健康,袁家老夫人拉着徐夫人去寺庙还愿,一次就捐了上千两的香油钱。
接着好友孙竹喧家里出事,急急的赶回了家。回书院后,跟他说京城的刑部侍郎来了冀州。
徐炎心中重重一沉,心酸中透着些许期待。
孙竹喧接着说,袁大人两天前已经离开了。
这中间隔了一年,大姐生了孩子,原本羸弱的身体越发艰难,死了。一年后,袁斯良又来冀州,这次还来了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