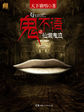子惜坐在就近的雪椅子里,她在雪地里孤身行走大半天,身子偏寒倒也不必费心降温。只见那黑袍男子一只手端起蜡烛底座,另一只手打开黑木箱子,取出里面的药酒和纱布。子惜在他背后瞧得仔细,原来那黑木箱子不过是个普通的行李箱,大多都是换洗的衣物和少量日常用具。
“你是旅行者?”子惜好奇地问。
“不是。”黑袍男子蹲在子惜面前,拆掉她胡乱包扎在手心上的白布,此刻差不多已是红布了,伤口不大,皮肉翻卷,呈现青紫色,血液一半自行凝固一半冻成血冰。
“艺术家?”
“不是。我现在要给你处理伤口,会有点痛,你忍一忍。”话音一落,他将药酒倒在子惜的伤口上,顿时泛出白色气泡。
子惜倒抽一口凉气,下意识地缩手,却被黑袍男子握在手中,不让她逃避。
她抬眸注视他,他也正看着她,眼底似有悠远的浅淡笑意。
雪屋里安静了一会儿,子惜手心里的白色气泡逐渐消失,疼痛也在慢慢消退。
黑袍男子又倒了一些药酒在她伤口附近,用纱布小心翼翼地擦拭她手心里的血污。
他浑身给人一种冷酷决绝的感觉,可是他眼底似有若无的微笑以及处理伤口时的手法却出奇的温柔。
“我感觉你很熟悉,好像很久以前我们就认识了,可是我的记忆里搜寻不到你的影子。”
子惜看着他薄而软的中长发,她很少看见这个世界的人将头发剪得那么短,一般都是及腰的长发,无论男女。她伸出另外一只完好的手,手指轻柔地撩起他肩上的黑发。
“人改变了,影子自然也变了。”他低着头,专心致志地包扎着她的伤口,不在意她拨弄他的黑发。
“为什么剪短?”她真的在哪里见过他,只是想不起来了,看着那头被剪断的长发,没来由的一阵心疼。
他依旧低着头,静静地说:“逃命的时候,被杀手砍断的,后来就没再长过,也许生命在那时候已经终结,所以不再生长。”
“很痛苦吧?”
“已经不痛了。”
“能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吗?”
他忽然抬起头,幽深的眸子凝视着她的眼睛,一瞬间的犹豫过后,他不轻不重地说道:“花离枝。”
“花若离开枝头,就再也回不去了啊。”子惜双眸噙泪,手臂抱住他的头,自己的脸贴在他的头顶,轻柔地对他说,“我在玉沙打听你的下落,有人告诉我,你已经死了。我就在想,以前如果我可以多为你们着想,不要那么庸庸碌碌,现在也许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你们就不用受那么多苦了。以前总以为散了就散了,又有什么可留恋的,其实是我总是心不在焉,没将感情投入进去。”
花离枝轻轻地搂着她的腰,轻轻地说:“我该高兴还是悲伤呢?你能将投入的感情全部收回去吗?”
“你能回到从前,我就能收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