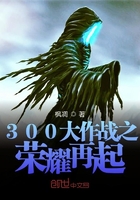我嗯了一声,没再说话。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打量这座城市,那么多庞然大物拔地而起,遍身镶满像钻石一般璀璨的灯火,的确是奇迹。城市从我们站立的地方,水一样向四面八方洇开,无边无际,我们置身其间,就像是蚂蚁爬行在巨大的巢穴中。这是个多么宏大的世界,在那些建筑物当中,有些楼房就是出自于我们手下。我们曾经亲眼目睹着那些楼房,就像竹笋一样,很突兀地从地面冒出来,越长越高,最终耸入云天。要是不来深圳,我也绝对想象不到,这地方会由一个小渔村变成如今的现代化大都市。可是,此奇迹不等同于石岩口中的奇迹,哑巴会唱歌,跟我们建高楼大厦,这两者之间既无联系,也无丝毫可比性。然而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为石岩感到高兴,他要结婚了,这是件喜事。这些年来,我们怀里始终揣着一个关于结婚的梦想,就像是揣着一个神秘的宝箱,而这个宝箱即将被石岩打开。
那时,石岩已经干了七天五夜。他妈的,他往空中吐了一口痰,说,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回工地了。我说,我也是。我真是这么想的,那些由竹架板和钢铁架铺就的进路,我是连一步也不想走了。这是我们在工地上的最后一天,过完这一天,我们就算是解脱了。所以我们咬紧牙关,把这两担灰浆送到了目的地。
我把肩上的担子卸下来,拍拍手上的尘土。我拍得很用力,但手掌心里没有半点感觉,就像是两块粗糙的树皮在互相拍打。我看了看自己的手,皱纹和裂开的伤口纵横交错,让我想起两块干裂的土地。这是一双属于建筑工人的手,我掌心里的皮肤,甚至比树皮还要坚硬。石岩也是。
石岩问我,回家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说,我只想抱个女人睡觉,你呢?
我想像鸟儿那样飞一次,他张开手臂做了个飞翔的姿势,他说,我从来都没有飞过。
我嗯了一声,摸出火机开始抽烟。他想飞,而我只想抱个女人睡觉。这就是我跟石岩的差距。我脑子里想着的,总是与现实生活脱不开联系。这五年,我在工地上赚来的钱,一分不剩地全存起来了。我计划着,等我回到家乡后,用这笔钱开个小店,做点小生意,然后再娶个健壮的姑娘做老婆,让她给我生至少两个孩子,当然,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最好是三个,或者四个,甚至更多。我的这一辈子就这么平淡着过下去。而石岩是个理想主义的男人,在我看来,他的想法总是那么的荒诞和不切实际。比如说,他想飞,还比如说,他想让一个哑女人唱出歌来,等等。在他眼中,他所生活的领域就仿佛是个魔术般的世界。难道他真能听到千里之外的歌声?我实在是很怀疑。
任务完成了,但我们没有马上离开高空回到地面。我们太累了。我站在竹架板上,不停地甩着手脚。石岩一屁股在竹架板上坐下来,双手抱头躺倒,让目光仰望夜空。我脚底下又是一晃,它总在晃,我也把头仰起来,望向夜空。夜色更浓了,星火开始密集起来。我们还看到了月光,从天空往地面水银般倾泻下来,在灯火辉煌的地方,明净的月色被消解得所剩无几。在深圳的这五年里,我还从未见过如此美妙的夜空。真美,我说。我陶醉地盯着月亮旁边云卷云舒。
石岩把照片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我。她也很美,他说,比月亮更美,你看看,她像个哑巴吗?她在唱歌,真的,你不相信?我知道你也不会相信。他敲敲手指,把一团烟灰弹在竹架板上。
我不置可否。心诚则灵,石岩对那女人的歌声过分迷恋,那种迷恋已经像宗教信仰一般执着而又虔诚。有时候,我不得不佩服他。他说,她真的在唱歌。他坐起来,侧过头,把手掌拢起来遮在右边的耳朵上,往夜空里听了一会。然后,他很认真地告诉我:她唱的是《茉莉花》。她唱得太好了,他说。他深吸了一口气,再缓缓吐出,一呼一吸之间,他摇晃着脑袋,和着那种在我耳中根本就不存在的节奏起`了拍子,就仿佛千里之外的歌声变成了某种芬芳的气味,正源源不断地往他面前渗过来。他比比画画,向我描述着那位远方的女人从歌声里传达给他的丰富信息,他说他听到了茉莉花细小的花苞正在缓缓绽开,白色的碎花中有几只蜜蜂在采集蜂蜜,茉莉花树的根须在泥土下安静地扩张,一个女孩光脚踩在泥土上,脚掌切入泥土时发出土面下陷的声音……
石岩越说越玄乎,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跟着他的描述进入了这么一幕场景——在一个艳阳高照的秋日里,一个哑女站在一片开满茉莉花的山坡上,长发迎风飞舞,她翕动嘴唇正在唱歌。她的歌声石岩能听到,我却听不到。所以我再次竖起耳朵,凝神往夜空里倾听。我耳朵里装满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声音,全是关于深圳这座城市。我听到横在我们面前的水泥墙面在夜色中悄然裂开,一些细小的泥沙从墙体上剥落,远处的大海开始退潮,潮汐声在夜色中逐渐变得稀疏,载满货物的轮船鸣着汽笛驶离海港……我耳朵里只有深圳,没有茉莉花,也没有歌声,难道她的歌只为石岩而唱?
哑巴真能治好吗?我问石岩,我说,我估计这件事情也只有你才会相信。
石岩反问我,哑巴为什么不能治好?
我没哼声。但愿吧,我心里暗忖。我把烟头在竹架板上摁熄,又从口袋里摸了支烟,拧燃火机点着了,我抽一口,没说话,又抽一口,还是没说话,我很想跟石岩说点什么,但某种顾虑又让我无话可说。我想说的是,让一个哑巴唱出歌来,对于此事我并不乐观,尽管这个心愿浇灌了石岩五年的心血,声带又不是件衣服,破了可以用针线缝补起来。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像石岩耳中的歌声一样,荒诞得有点不着边际。
石岩说,她对我说过,等她好了,就跟我结婚,她一向都是个信守承诺的女人,现在,她答应跟我结婚了,所以我相信她已经好了。你听,她又在唱了,他说。他闭上眼睛,再一次陶醉于那种在他听起来美如天籁,可是在我耳中并不存在的歌声里。
我摇了摇头,把一些话和烟雾同时吞进肚子里。我把那张照片拿在手里,学着石岩的样子,把手掌拢在耳边凝神细听。不但没有歌声,我耳中反而越来越嘈杂越来越浑浊,许多声音一起涌进耳孔。我听到成群结队的泥头车呼啸着行驶在黑暗的公路上,工地上的打桩机轰鸣着刺向地心,某栋被拆除的建筑在夜色中轰然倒塌……
我是不是该换种方式来倾听?后来我反复端详着照片上的那个女人,她的嘴巴微启,牙齿被嘴唇挤成一条白净的细线。我盯住她时,她仿佛宽慰地笑了一下,然后又笑了一下。有那么几次,我恍若真的听到了,有歌声从照片中传出,若隐若现,当我支起耳朵仔细倾听之时,这歌声又像幽灵一样转瞬即逝。我突然顿悟,我估计石岩也跟我一样,那种在他耳中长久不衰的歌声,也许只不过是来自于某种虚无的幻觉。
我把照片交还给石岩,他顺手接过去,用两个手指掸掸灰尘塞进上衣口袋里。他说明天就能见到她了,这张照片的用处已经不大。那时他怀里揣着的将不再是照片,而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女人。他说女人真是个好东西,这世界上,没有比女人更好的东西。你摸过女人吗?他问我。
我摇摇头,没摸过。
他说,粉嫩粉嫩的,就像从面粉上滑过,摸一下一年都不想洗手。
我点头附和的同时,心里却暗自对石岩的话再一次表示怀疑。其实我是摸过女人的,只是这件事情让我羞于启齿。初中时,我曾经闪电般摸过一位女同学的手,那次触摸给我的感觉,不像面粉,而是像块烙铁。
石岩说,这次回去,你也该找个女人成家了。
我说,我早就这么想了。
我真是这么想的,有女人的好处,我是知道的,就是找头母猪放在被窝里,也比打光棍强。就是在那时候,又吹过来一阵风,风从海边而来,经过我们身边时,把我的头发从脑后吹到额前,然后又像只淘气的手一样,把石岩胸前的照片拽了出来。石岩就像条件反射似的,翻身而起,伸手去抓那张照片,只抓到一把空气。照片摇晃着往空中飘落。他跳起来,伸手又去抓,还是一把空气。这时我感到脚底下的竹架板剧烈地晃了一下,它总在晃。然后我看到石岩翻了个跟斗,像个跳水运动员一般从竹架板上掉落,他的身体在我面前突然矮了下去,嘴巴里发出一声尖叫。我万分惊讶地看到,他真的飞起来了,衣袂翩翩,如同一只黑色蝙蝠,以怪异的姿势滑翔在冰冷的夜空里。
我伸手去抓他,没抓住,只从他手臂上撕下来半截衣袖。我俯身看到他在铁架子上绊了一下,又落到了防护网上。防护网只能挡住砖石,挡不住石岩一百多斤重的身子。但他还是停留了片刻,在他的身体滞留的这段时间里,他仰面看着我,明亮的眼睛里没有半丝恐惧,只有一种强烈的不舍。这让我感到惊讶。我更惊讶的是,那时,他还能从容地开口对我说话。他说,明天,你一定要回我家乡,去听她唱唱歌。
我点点头。防护网突然裂开了。他伸手想去抓住一样东西,没抓住,另一只手也伸出去抓东西,还是没有抓住。他就像颗出膛的子弹,攸地一下射向地面,最终变成一个黑点在我视线里凝住不动。
我扔掉手中的半截衣袖,大喊一声,沿着那条用竹架板铺成的长路,甩开两腿从楼顶往地面奔。在跑向地面的途中,我看到那张照片跟我一起,飘飘摇摇地落向地面。随着照片的不断翻转,照片上的女人在我眼中一闪一没,那神情很焦急,就仿佛是想从照片中走出来似的。那时,我突然听到了从夜色中传来的歌声,的的确确,我听得分明。我分辨出那是个女人的声音,就像一缕缕轻烟随风而至,穿越黑暗抵达我的面前。这时我才终于相信,更准确一点地说,应该是坚信——这声音,一定是来自于千里之外的那个女人,她的歌声清脆婉转,有如天籁之音。
原载《山花》2010年第3期
点评
华美的文字和如真如幻的描写营造出了一种自始至终的悲剧气氛,关于城市的体验充满了孤独,而关于乡村的回想又遥远且不真实。这不只是两个建筑工人的命运或视角,城市飞速的发展让居住在这里的人普遍产生了孤独感,居住在城市里的这些人,谁未曾在深夜独自思考理想人生时,面对繁华却陌生如鬼魅的城市找不到家的感觉,仿佛置身于晃动的脚手架上惴惴不安呢。
天籁之音虽让人向往,但似乎也只属于天籁,不属于生活本身。当石岩,这个据说性格如其名的男人一遍遍絮叨着自己家乡的女人和未来的生活的时候,心里难道就是踏实的么?“回不去的是故乡”,当石岩每重复一次那个美好的关于故乡和他女人的故事时,那个美好的设想便暴露出一次可疑。在这个以两人交流为主的故事里,充满了耐人寻味的象征意义。不能从现实的角度去挑剔它,但却可以从象征的角度来接近它。如果说初读时有些迷惑,那么你只需继续揣摩体味,这是复杂感受的传达,而非简单地讲一个故事。
天籁之音,也许根本不存在,也无关听力,当你相信、确信时,便在,不信、怀疑时,便不在。也许城市人之所以听不见天籁之音,是因为在这个混凝土迷宫里生存的我们,丢失了那个愿意百分百相信一件事的天籁之心。
(崔庆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