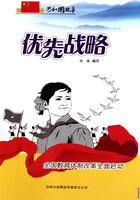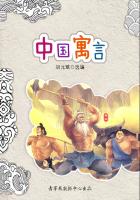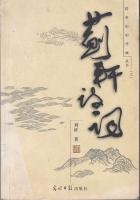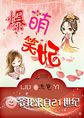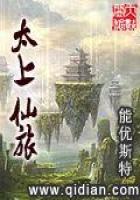我曾经想以“后工业时代的诗与诗学”界定我的诗歌写作。所谓后工业时代,不是对我们栖居的这一个时代的指证,也并非对中国目前混杂现实的指认。实际上,我将之作为个人写作语境的一种设置提出,或指向一种我所理解的当下写作的理想景态。我所说的理想并非完美,仅仅是某些可能性的获得,深层的意念得以坦露的一种形态。
这种设置又不是凭空而生,它源自更广阔辽远的世界背景。针对中国的有限范畴而言,后工业时代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泛本文存在。它迫在眉睫,又似乎被隔绝疏离。它与我们的生存若即若离,时而摩肩接踵,时而影像模糊。但它在我自身写作话语的认知中却日益明晰起来,并确实给予我向一种语式转换或新的体验的可能。
如对时间不确定性的体会与表述,这贯穿了我写作的几个阶段。以及由此关联到的去本质化与存在零散状态的描述,均在绵延的展示中得以确切的呈现。从早期的《水为源》到90年代的《新时间》等,直至近期的《白》与《蓝》,时间提供了一个不断更新的场景,但时间之间并非延续的联系。它只是一种在的展开的可能。
而生存或者内心的孤寂,也绝非来自于对本体的固执或远离。恰恰相反,孤寂是一种弥散的在的形态,是不可解决与无所依据的样式。我写《犀牛走动》、《灰色鲨鱼》和《大鲸》,包括《乌岩村》及《带着问题居住》等,它们是隔离的,是在巨大的空间中散在的。它们之间的呼应,源于弥散时刻的共在。生存因此不是一条线索,而是散漫的隐喻。
我因此不太在意所谓时间的“消逝”。1986年或者1992年或者2009年又有什么关系呢。
雅克·拉康认为人的本我(实在界)主体乃不可能之物,是原初的匮乏。人通过想象界的范畴终于获得符号的呈现,但符号是外在性的,人因此永远生活在他乡。主体的表述亦是他者的话语,然而每个人的认同仍然存在区分。后工业时代或许就是我所认可与期待的言语系统,它为我提供了为我所欣喜与迷恋包括困惑、痛楚、厌倦等的记号及编码的法则。
后工业时代,因此仿佛是我内心的镜像。是书写的命名。
我在一个有阳光的冬天下午开始书写这一篇后记,这一天也是我13岁可爱女儿的生日。这是一些零散片断的重合,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让我有一丝温暖和一点兴奋的感觉。我住的是城市里某个小区楼房的三楼,书房白色落地窗外依然幽绿茂盛的樟树树叶全都安静着,好像就是它们在制造着这一种宁静。还有那一只白头翁小鸟,它在树叶间无声地梳理羽毛。阳光也是无声的,书架上的书,以及书稿中的每一首诗作。
但它们是另外的声音。
本书辑入的诗歌主要是2000年之后和1992年之前的作品,1992年至2000年间的诗作基本上收入诗选集《在时间的前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重新审阅这些诗歌,并没有体会到生存的历史感,每一首诗所指示的时刻,似乎都散布在那里。在的场所是无限的,生存的表达由此是未可穷尽的本文与语式。
一本书的出版,是话语的重现,对于一个人来说,仿佛是一些场景重新密集地开启。某些快乐就在凝视间浮游,如眼前初被搅拌开的这杯牛奶咖啡。
2009年12月22日,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