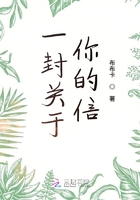至东方既白,太极宫一夜的喧嚣终是落下了帷幕。齐王从宫门口出来时,眉梢间洋溢的喜悦早已抑制不住。没走多远,跟随在他身后的一众党羽,纷纷驻足向他道贺,将他围了个水泄不通:“恭贺殿下多年夙愿达成,今夜扳倒了太子李适,终是扫清了殿下您储君道路上最大的障碍。”
守得云开见月明,齐王自是扬眉吐气,他与一众党羽委婉客套了半天,随即邀请众人过府一叙,“今夜尘埃落定,多亏了众位大人多年来的鼎力支持,王妃已在府里备好了酒宴,还请大家一同移步我府中,共商接下来的大事。”
齐王的一众党羽眼见着自己多年来在政治上的投机,终于要到了收获的时候,自是纷纷应承着,唯恐得罪以后的储君。
齐王环视一周,在最外围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张阁老,只见他恭敬地朝着张阁老行礼道:“岳祖,这些年来多亏有您持危扶颠,方能有今日扭转乾坤的局面,孙婿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这天气太寒冷了,还请您移步府上稍作休息,婉怡已经恭候多时了。”
张阁老十分客气地回敬道,“殿下言重了,殿下是天选之人,一切皆是天命所归,非臣一己之力所为。殿下请放心,接下来那些需要臣做的事,殿下不必支应,臣自当竭尽全力。如今殿下与王妃琴瑟和鸣,臣很是欣慰。臣在朝多年、夙兴夜寐,如今已然是风烛残年,便和那些寻常的老翁一样,只盼望着在家好好睡个踏实觉,儿孙环绕膝下,能够有所出息,不辜负皇恩罢了。”
齐王自是滴水不漏般地回敬到,“岳祖,您请放心,婉怡是我的结发妻子,情份自是旁人所不能及;元朗是我的嫡子,我自是对他寄予了厚望;婉怡的兄弟们自小便承蒙了岳祖您的教诲,自是国之栋梁,我日后必定重用之。”
许是张阁老见惯了朝堂风云,对于齐王许下的这些承诺,不置可否。他捋着花白的胡须,将话题引向了别处:“老臣一辈子在朝为官,大约是战战兢兢惯了。太子自尽、昭叶公主生死未卜,多事之秋,若是让人知道殿下设宴畅饮,恐为陛下所不悦。殿下如今距储君之位仅仅一步之遥,需得万事加倍小心,千万不要输在这一步上啊。”
齐王恭敬地朝着张阁老深鞠一躬,“是啊,岳祖提醒的对,今夜是我昏了头,储君应有容人的雅量,昭叶又向来为父皇所喜。小不忍则乱大谋,若我今日所为被父皇知道,恐是为他所不容。”
他又当即决断道:“来人,告诉王妃取消府里宴饮,再带上些名贵的药材,送到昭叶公主那里去。”
众人见状,也纷纷小声议论着,“昭叶公主今夜晕倒在龙华殿前,据说是气急攻心、命悬一线。刚刚陛下竟然召回了太医院的前任院首——乔太医,为她诊病。”
“是吗?乔院首可是太医院从前的翘楚,如今年近花甲,奉旨恩养在家,看来昭叶公主的情况很是危急,否则陛下不至于请来他啊。”
“都说太子和昭叶公主兄妹情深,今夜总算是见识到了。说来公主也是被为东宫所累,无辜受此牵连。也是难为她了,今夜妄图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保住一座大厦将倾的东宫。”
那些人虽与昭叶身处不同的阵营,却也不自觉地称赞着公主的勇气和忠诚。
只有沈哲一人,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昭叶公主无辜?当真是可笑,只盼望她不要醒来才好。”
沈哲的同僚好意提醒他,示意他不要再在言语上攻击公主,“沈兄,你今夜确是有些失态了。昭叶公主不过是一个女子,你又何苦故意激怒为难她,紧紧抓住她不放。若是她真有何不测,难保陛下日后不会迁怒于沈兄你啊!”
“私自调兵遣将,她又怎么会是无辜?”沈哲气恼地说着:“你不了解,昭叶公主远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她和她的母后一样,惯会蛊惑人心。算了,你不明白,不提也罢……”
事关自家侄儿沈寒清,想着无论如何,家丑也不可外扬,沈哲的话到嘴边,却又生生咽了下去。只是在心中暗暗地愤恨着:若是没有她,他那谢庭兰玉般的侄儿、沈家唯一的希望,怎么会终日里魂不守舍,险些做出背弃家族,离家私奔之举。
沈哲的同僚颇为无奈笑着:“我知道你们沈家与东宫是死敌,只是陛下方才已经说过,今夜东宫的事到此为止,摆明了就是不再追究。若是昭叶公主侥幸醒来,想来陛下根本不会处罚她。你又何苦去触陛下的眉头?”
沈哲怎么肯善罢甘休,只见他走到齐王身旁,低声劝诫道:“殿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善罢甘休,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今夜没有将东宫一网打尽,拿下飞羽军,还放过了那么多的漏网之鱼,始终是隐患啊!”
齐王深以为然,足足握紧了拳头,“我心中了然,只是此事不可操之过急,可徐徐图之。”
张阁老站在原地,目睹着眼前的一切,内心却是唏嘘不已,齐王这般的从谏如流,却是如此伪善和精于表面功夫,对于他张氏一族来说,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啊!
记忆中的濒死感来袭,又渐渐消散退去。昭叶再有意识的时候,已经是在昭华宫的内殿之中了,她努力想睁开双眼,却发现眼皮直打颤,根本无力睁开。她的心口绞着痛,想伸手去捂住心口,却发现四肢僵硬无力,已是动弹不得。恍惚间,隐隐约约听到殿内一阵手忙脚乱的声音,太医们正急得如火如荼,商讨着对症之策。
陈太医是如今太医院的院首,他一向负责照看昭叶的身体,只听到他焦急地疑惑到,“这般严重的心绞痛,是心症之兆。只是殿下一向身体康健,脉案中也从来没有记录和体现,怎会得这种不治之症?”
解答他疑问的是昔年太医院的院首——乔老太医,“殿下的心症是出生时便有的,正因先天不足,陛下才格外宠爱于她。当年,陛下和先皇后为了避免公主殿下有心症一事被人所探知,防止有心人利用此加以伤害,所以从殿下一出生便封锁了消息,抹去了脉案上的痕迹。陛下刚刚还传来口谕,今夜之事照旧要三缄其口,一个字也不许对外提及。”
陈太医惊讶道,“原是如此。听闻先皇后怀着公主殿下时深思俱伤,那么殿下从娘胎来带来心症,并不奇怪。只是这些年来殿下的心症一直被控制着很好,不要说我们这些太医,怕是连殿下自己对病情都是一无所知,想来还是多亏了乔院首您多年前的医治得当。”
乔太医有些惭愧着说出了事情的真相:“殿下一出生,老夫当即施以针灸之法,本以为当时施救得当,以后不会再犯。可惜天不遂人愿,好景不长,殿下四岁那年,发生了一场意外,令这心症被牵引,至此再难被彻底压制。今夜,老夫不知道宫里发生了什么,让殿下心绪这般起伏,这病根被彻底触发,心脉大损,已是无法复原。此后更是极容易被诱发,接二连三,每发作一次,心脉便会受损一半,直到药石无医,心绞痛而死……”
陈太医不无惋惜地说到:“乔院首,您是杏林圣手,若是连您都这么说,便知道已再无回旋之力。心症之人,往往熬不过三次发作,便会殒命,依照殿下如今这心脉受损程度,怕是拼尽太医院的全力,也熬不过再多的两次。以后只能在每次发作时,及时平息压制,尽量减少心脉受损程度。”
乔太医亦感慨着着,“是啊,老夫一生行医,最后却发现医者所能尽之事十分有限,世间万物终究是逃不过那句生死有命。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只盼着殿下今夜过后能彻底远离这权力之争,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若是静心休养生息,也许是另一番清明景象,可保得一生平安无舆。”
“心症,原是如此。”昭叶挣扎地想要开口说些什么,心口却痛到无以复加,泪水直在她眼眶中打转。
陈太医及时注意到昭叶的痛苦,只见他迅速地拿起银针,朝内关穴扎去。数针后,昭叶心口的疼痛得到些许缓解,随后恬然般地进入昏睡态,梦中那些徜徉的记忆来袭,再也抑制不住。
时常出现在梦中如今清晰可见,黑暗之中她挣扎着、呼喊着,却是枉然……
昭叶终是记起了:四岁那年发生的根本不是意外,而是为人所害。那时,她被柳昭仪的宫人牵引到了御花园的一个无人之处,随后被一把推入枯井中。滂沱大雨,无底冷涧,她幼小的身体处在漆黑的暗底之中,饥寒交迫,惊惧万分,却是怎么哭喊都无人应答。
声泪俱下、心力衰竭,心口窒息般的疼痛袭来,直到她彻底昏倒过去。挨了整整一夜,等到被萧后找到时,她已是奄奄一息。虽得太医相救,性命无虞,至此却是诱发心症之因,从此再不可挽回。这大约也是明宗皇帝当时默许萧后对柳昭仪下手的直接原因之一。
昭叶再次醒来时,已经不知是睡了多久,恍惚间看到了明宗皇帝的身影。她不敢相信,只是揉着红肿的双眼,再次确认着,卧榻边坐着的正是她的父皇。一位慈祥恩厚、双鬓已见斑白的父亲,眼角满是倦意,却仍在悉心照看病中的爱女,默默地等待她的苏醒。原本是多么一幅温情脉脉的场景,如果这位父亲不是手执生杀大权的帝王该是多好。
昭叶挣扎着起身想要坐起身来,明宗皇帝扶起她,口中有些愧疚地说着:“叶儿,你终于醒了。对不起,今夜父皇没有保护好你,本以为将你留在汤泉山,便能够让你置身事外的,不曾想却是枉然。你如今知晓了自己有心症,今后便应该更加当心才是,远离权利之争,学会明哲保身。”
事已至此,昭叶不想再装作若无其事,她心中有太多的痛苦需要去发泄、有太多的疑问需要得到解答,“为什么?为什么要杀皇兄?”
明宗皇帝并不理会她的质问,只是递上了一盏温热的汤药,娓娓道来:“父皇老了,也许护不了你很久了,父皇膝下儿女众多,却是难以周全的照看到每一个。今日便与你言明,这皇权终有一日是要交到你齐王兄的手里,你与他不睦,所以父皇不得不为你的将来所筹谋。一个女子一生最重要的便是婚姻,父皇在你的婚事上思前想后,还是觉得将你嫁入张府最为稳妥,张家势大,如此方能护住你的一世平安。”
“一世平安?”昭叶苦笑着,她依稀记着,母后临终之时,父皇曾答应过母后,一定会保住她们兄妹二人的一世平安。如今这昭华宫物是人非,父皇违背了誓言,连天子之诺尚且流于形势,这世间谁又能护得了谁一世平安?
昭叶已经记不起,母后逝去后的那几年,在这昭华宫的多少个黑暗的夜,只有她的皇兄守在她的身侧,给她讲着典籍故事,哄着她入睡,悉心抹去她心底里黑暗的阴影。一直都是皇兄在竭尽全力给她安全感,让她感受着皇室中那不可多得的亲情和温暖;而他自己作为一个风雨飘摇的储君,则始终忍受着的不安和痛苦的折磨。
“你和你母后其实很像,连保护一个人的方式都那么像……”明宗皇帝缓缓道来,“父皇不是不知道,这门婚事也许不合你的心意,可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沈家的那个孩子,今夜你也看到了,与你终是无缘。”
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那么,皇兄呢?一切都是骗人的,昭叶不想再听这些虚情假意,她一把推开明宗皇帝递上来的药盏,反复质问着他:“为什么?皇兄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连一条活路都不肯留给他?虎毒尚且不食子,他不仅是太子,更是你的儿子!”
明宗皇帝见始终绕不开这话题,只得暂时将药盏收回,“朕知道你还在怨恨着,你以为太子是朕下令杀死的。可事实却并非如此,不管你信与不信,朕今夜只是要废黜太子,并未真正下令杀他。”
昭叶气急,她冷笑着指着明宗皇帝,“父皇当我三岁稚子吗?父皇说自己没有下旨杀皇兄,你自己相信这句话吗?十年了,皇兄做了十年的储君,十年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今却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这般悲凉,到底是何人之过?”
昭叶从不曾像今日这般忤逆他,明宗皇帝渐渐失去了耐心,只见他重重地将药盏扣在了桌案上,“叶儿,你再愤怒也该有个限度。太子是自尽的,不是朕杀的!”
昭叶起身,无比愤怒地挥手将那药盏打翻,脱口而出:“对,你是没有下明旨,也没有用刀剑直接刺向皇兄,可是你扼杀了他所有生的希望。”
她声泪俱下着:“无论哪朝哪代,被废掉的太子,结局不是幽禁就是赐死。皇兄用尽一生的时间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当好一个储君,若是连这唯一的希望都被你剥夺了,他又有何希望活在这世上?这些年来朝局动荡,皇兄的太子之位不稳,到底是谁造成的?是父皇你!是你任由齐王他们将污水泼在皇兄身上,任由他们肆意欺凌、凌驾于储君之上。”
明宗皇帝亦是气急,起身拿出了君父的威严,义正辞严地说着,“李适并不是做这天子的合适人选,我必须把大周交到合适的人手上!叶儿,你听清楚,你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源于李氏的传承,都来自于朕。李适的太子之位,你的公主之位,这些都是朕赐予你们的。荣耀恩宠,朕想赐予谁便赐予谁,想何时收回就能收回。即便朕当年立了李适为东宫太子,可是这皇位,只要朕不给,你们决不能伸手去要、去抢夺!自古皇位便是贤能者居之,储君有他自己的路要走,李适如果连这些都摆不平,朕又凭什么放心把大周这万里江山交给他?”
昭叶的情绪十分激动,她捂着还在阵痛的心口,大口地喘息着,断断续续地说着:“到底是皇兄不堪大任,还是父皇您误信了小人之言,鬼迷心窍般信了他会谋反?皇兄没有谋反,也永远不会谋反!父皇你从始至终都知道的,对吗?你有千百种方式可以收回皇兄的储君之位,却不该也不能用这谋反的罪名冤屈他、逼死他。齐王秉性如何,父皇你不是不清楚,却为何一定要选他取代皇兄?”
明宗皇帝虽是气急,见昭叶状况不好,只好缓了一步,说出:“叶儿,事已至此,覆水难收,却是多说无益。储君一事,不是你一个公主可以议论置喙的。从今往后,东宫是东宫,你是你,你不得再与东宫相干人等往来,你只得专心养病,好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昭叶还在气头上,眼泪不住地滴落,却不依不饶道,“父皇永远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圣人姿态,永远在以胜者的姿态任意践踏奚落着败弱者,这点齐王兄真的很像你。父皇自己的皇位如何得到来的,难道忘了吗?父皇口口声声说爱母后,却一直是在利用她、控制她;父皇曾口口声声说着皇兄是太子、是储君,转眼间却废黜了他。父皇说过的话到底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怕是连自己都记不清了吧。”
“够了!”明宗皇帝终是恼羞成怒,顺势抬起了巴掌,却见着孱弱的爱女,怎么也没忍心落下。
明宗皇帝极致的忍让,并未换来昭叶的心平气和的只言片语,“父皇,你为何要让人救我,不如一杯毒鸩将我一同赐死,我们兄妹二人也好结伴去九泉之下陪伴母后。”
明宗皇帝的手还在颤抖着,他屏息凝神,看着鬼门关上走了一回的爱女,终是不忍,缓缓地放下了手掌,只是道:“你病糊涂了,父皇今日不与你计较。好好休息,终有一天你会理解朕在这皇位之上的无奈与为难。”
他转身想要离去时,只听见昭叶“噗通”一声跪倒在了地上。
昭叶坚定地说着,“父皇,这皇宫冰冷的,我一刻也不想再多待下去。最后一次,这是我最后一次求你。求你还皇兄一个清白,让他干干净净的离开这个世上。”
她的皇兄李适,是大周太子,清白自矜,即便是死了,也绝不该承受谋反这样的污名。
明宗皇帝一时间无语凝噎,“好,父皇答应你!”
待明宗皇帝走出殿外,只听到昭叶在喃喃自语着,“父皇,我会好好地活着,长长久久地活着。我倒要看看,你将这宗庙社稷交给齐王,到底是对还是错?齐王又是何德何能,能保得这大周江山万世无虞?”
尘埃落定,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覆水难收,昭叶心中提着的那口气终是泄下了。
她派出去的东宫暗卫一个也没回来,那个局怕是精心布了许久,又怎么会因她生变,她今夜不过是在做无谓的挣扎,若不是一点希望也没有,皇兄又怎会自尽?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这些年围在东宫形形色色的人,又有几人是真心,几人是假意?宿苒、吴映堂或是还有其他什么人……
一整夜,一整夜,她见到的都是背叛……
东宫倒了,谁失势、谁真正获益,时间久了,所有的真相都会浮出水面。她不想去追究什么是非曲直,反正事情已经无可挽回。
昭叶缩在黑暗的角落中,环视着这富丽堂皇的昭华宫,曾经熟悉的一切,如今都让她感到无比的伤心和厌倦。她想要逃避,却不知这天下之大,该逃亡何处。
她索性连夜搬出了皇宫,回到了茉莉苑。明宗皇帝虽知道她是在赌气,却也没有阻拦。大约是太医们怕她触景生情,心绪不稳,帮她找了个合理的借口:说是茉莉苑中温暖湿润,有助于公主殿下养病。
回到茉莉苑后,陈太医为她开了许多安神的汤药,她便终日里迷迷糊糊地昏睡着,不再牵动思绪去想那些徒劳无用的事。
这一病便错过了太子李适的头七,偶有清醒之时,洛梅侍奉昭叶汤药时,会特意与她讲一些东宫的事,说是:“陛下开恩,不再追究太子殿下和巡防营主将吴映堂谋反之事。对外只说是江北大营失火,太子殿下遭遇不测,太子殿下的丧礼,一切礼遇等同国丧。”
昭叶心中了然并非是父皇有多么仁慈,他只是不想自己的青史上再多一条弑子的罪名。她冷笑着,“人都不在了,要隆重的丧礼又有何用?这丧礼再隆重,也掩盖不了皇室的凉薄。”
洛梅轻声叹着气:“这身前身后名,对太子殿下已然没有了用处,可对那些活着的人,尤其是对小世子殿下,却关系到一生。世子殿下还小,不应该背负着父亲的污名长大。”
昭叶虽说着气话,却也知道,皇兄的临终所求,不过是希望昊儿干干净净的长大成人,不受东宫之事所累。这也同样是昭叶所求,为了皇兄的遗愿,她可以妥协、可以下跪乞求。
洛梅继续着:“殿下安心,东宫里太子妃和世子一切无虞,多亏了殿下那夜拦下了飞羽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昭叶平淡着说着,“不是我。”
她内心里清楚,杨氏兄妹能安然无恙,多半是因为那封血书。皇兄在临别之际,用自尽保全了整个东宫,保全了他的妻儿,保全了那些背叛他的人。
昭叶不忍去读那封血书,只因开头的那两句诀别诗已足以令她肝肠寸断,‘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她不知道皇兄当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去赴死,若下手的是齐王,皇兄也许会反抗,也许会想着去脱困,可不是齐王,是他一直敬重的、爱戴的父皇。
洛梅捧着药箱,展示着一些成色极其罕见的灵芝和人参:“齐王府送来了不少名贵的药材。”
昭叶自嘲着,这些虚与委蛇的本事,她是再怎么也学不会的,“齐王既然想要坐上皇位,便得先装出一副仁孝的样子。明明前一刻还在厮杀暗害,后一刻便要握手言和,这场其乐融融的亲情大戏只能继续演下去。”
洛梅又言道:“今日齐王还在朝堂上为吴映堂求情,说是为免太子殿下声誉受到影响,吴将军的家人也不再受到株连。”
“吴映堂?齐王的这颗棋子埋得可真够深的。江北大营那夜,有他一人在,又何愁要不了皇兄的性命?”昭叶心中不自觉地惊诧着,却已是了然,“洛梅,你知道吗?身处高位,有时候不到最后一刻,根本无法看出谁是真正忠于你的?谁又是敌人放在你身边,准备随时刺向你的一柄利刃?”
洛梅闻言,道:“殿下,魏将军前日来看过您,说是跟您道个别,他被调回北境,奉命驻守。”
昭叶心中愧疚,惋惜地说着:“东宫败落,这次魏绍玄是真的被贬谪到北境了。也好,远离是非,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归来?”
洛梅踌躇半天,还是告诉了昭叶,“殿下,你昏迷不醒的时候,沈将军在茉莉苑前驻足了一会儿,却没有进来,眼下应该已经回了北庭军……”
昭叶若无其事地笑着,“江北一役的统领、东宫覆灭的有功之臣,怎么没留在长安接受封赏?好生奇怪啊!”
她戏谑着沈寒清,却也何尝不是在戏谑着自己?
亲情的戛然而止,始终令她无法释然。皇兄的人生都结束了,而她的人生该怎样继续下去?皇兄走了,她不知道还有什么事该坚持下去,还有什么人值得去守护,一切仿佛都没了意义。若世间没有了爱,至少还有恨,至少仇恨能支撑她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