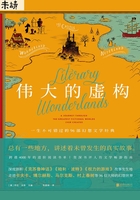熏风午后,先生用数码相机为小睡的她与女儿拍下一组照片。
照片上,5岁的女儿睡得横七竖八,嫩胳膊嫩腿都张着,像是一只张牙舞爪的小螃蟹,更像是一朵天真无忌的剪纸娃娃。
但令她诧异的却是照片上的女子,侧卧在粉紫银灰雨点儿床单上,头靠在枕上,腰背抵住床沿,身体弯成半圆,双手微张,隔着半尺遥遥护守着女儿。墨荷长发半挂于床缘,翠绿真丝睡裙,女子睡姿静美。
“这是我吗?”心里想着,她忽然不认识自己了。
她睡相之恶,向来是众人笑柄。
幼儿园时期,几乎每天都有一个与她合睡的小朋友被蹬哭;9岁,家人早晨起来,发现来做客的小表妹蜷缩在沙发上过了一夜,眼泪汪汪:“表姐踢我……”;大二那一年,全寝室女生被“咚”一声惊醒,唯有滚到床下的她,犹自蒙被呼呼大睡。最权威的自然是先生,每每一副罄竹难书状:“那一次我们在庐山……”她扑上去堵他的嘴。
“从几时起,自己开始睡姿如弓了?”她极力回想,是初为人母吧:一小团粉红的肉抱在怀里,轻得不像人身,却哭,咯咯笑,打喷嚏,是小精灵错投人间,大人稍微一不留神,就会回返天堂。太知道自己的恶睡相,太怕自己会压到女儿,无论多累,睡得多死,她身体的线条总是醒着,如锦瑟新调,绷得极紧,偶尔翻个身,已经惊醒,无端的一头大汗,第二天醒来,腰酸背痛。
她从不知道,睡觉竟会如此辛苦,这是她有女儿后的感觉。
女儿甚得她的真传,一两岁,睡觉时就会以肚皮为圆心,自动旋转。三四岁,不甘蛰居小床,一定要上大床;上了大床,就像《伊索寓言》里进了帐篷的大象,步步进逼。难以想象,女儿小小的身子,要占掉整张床的四分之三。
而她退得步步为营,最后只剩了床边的半席之地,不能放纵自己掉下去,也怕自己守得不够,女儿从手脚的间隙滑落床下。身体曲成弧度,双手张开,是永远的守卫,哪怕,在睡梦里,也要做童话里守护的天使。
每一个母亲都如是,她亦如是;而她的女儿,将来也会如是吧。女子生于血肉,再生血肉,所有的母亲们啊,都走过相同岁月。
看到照片上翠衣的自己,她恍惚看到一支温婉谦卑的缠枝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