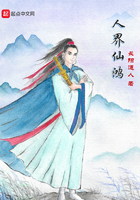《新青年》编辑部的分化只是一种信号,作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最具代表性的群众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也开始由思想倾向的不同而产了裂痕。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多次论战,中国共产主义者为建立中国共产党所展开的各项工作,使五四运动初期由三部分知识分子——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新文记玩一战线,商渐分化。到上1921年下丰年之时,分化的态势已然凸显。而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在《新青年》编辑部和“少年中国学会”内部更表现得极其明显和具有代表性。《新青年》编辑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和指挥部。1919年夏秋之间开始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第一次论战——主要是在《新青年》编辑部内部展开的。由于这场论战所涉及的内容直接关系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向何处去的原则问题,因此也表明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已经开始发生分化。尽管在这场论战中编辑部的其他成员并未卷入,包括这场论战的两个主要人物——李大钊和胡适在内,也仍然在反对封建文化思想和介绍新思潮、探索社会改造的大前提下,继续保持着统一战线的形式,但编辑部内部的分歧已日趋尖锐和表面化。
1920年9月,《新青年》自八卷一号起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后,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大量介绍俄国革命及建设的情况,这使北京方面的编辑部成员胡适等人即开始对刊物内容深为不满,并表示了冷淡,由此引发了一场围绕着《新青年》编辑方针的大争论。11月16日,陈独秀致信胡适、高一涵,表示刊物以后将尽量趋重哲学和文学,以缓和矛盾。胡适在复信中提出解决刊物编辑方针分歧的两个办法:一是“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是“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搬到北京来”,发表一个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编辑部成员中更有因此而提出“暂时停办”的建议。11月23日,胡适又向编辑部成员李大钊、鲁迅、钱玄同、陶孟和和高一涵等写信,继续解释他杂志迁移北京、声明不谈政治的主张。胡适的这封信发出后,在编辑部中引起强烈反应,编委会成员纷纷表示了各自的意见。陈独秀强烈不满胡适的主张,并为此发了脾气。鲁迅明确表示新青年应该谈政治,而不是纯以学术文艺为唯二内容。李大钊则表示如果能够保持新青年内部的团结和精神的团结,编辑部北移北京可以考虑。周作人和钱玄同则认为,新青年杂志作为一个同仁刊物,其编刊人员本是自由组合的,如果在内部主张“统一思想”,是同仁刊物的莫大耻辱,因此不能勉强调和统一,索性让它分裂成两个杂志为好。1921年2月15日,陈独秀复信胡适,明确拒绝将《新青年》移回北京。双方的争论和分歧更趋尖锐。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作为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的《新青年》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于同年9月暂时停刊,以后复刊,则是直接以中国共产党理论机关报的面目出现,成为一政党的喉舌。翌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另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努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同年,胡适等人另行创办《努力》周报,宣传实用主义、“好人政府”等。这样,原来由三部分知识分子组成的新文化统一战线正式宣告破裂。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和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举着各自的旗帜——《向导》和《努力》,公开对峙,分道扬镳。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则继续在文化领域内向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猛烈抨击,继续探索社会人生的新路。
《新青年》编辑部的分化只是一种信号,作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最具代表性的群众性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也开始由思想倾向的不同而产生了裂痕。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是在反对封建思想文化、介绍新思潮、探索社会改造的大前提下结合起来的,针对各种极不相同的思想倾向,学会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但这并不能弥合内部的裂痕。当“问题与主义”之争出现时,学会内部立即有所反映。当上海分会提出“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的建议,以及王光祈以“北京本会同人”的名义对该“建议极表同情”时,巴黎分会很快来函,表示异议。认为“有一定主义,研究学术方切实”。如果没有一定的主义,“本会将日入于消沉,日堕于空虚”。为此建议“协定一共同之主义”。这是学会内部关于学会宗旨的第一次交锋。由于学会内部思想不一,加之会员分散各地,联系较少,会员之间已开始呈现分化。1921年7月学会在南京召开会员大会时,各派会员在讨论确定主义和参加政治活动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会上,北京代表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人一再提出必须“采取或创造一种主义,以为学会的主义”。并认为学会所采用的这种主义“不可不为社会主义”。反对者认为,如果学会强定一种共同主义,必会引起因会员意见不同而致分裂,而且,学会在成立时并非是因相信共同的主义而结合,如果现在强令会员相信一共同的主义,必然会使学会成员意见不一而解散。左舜生甚至强调“学者即不谈主义”,明确表示反对“实行一种主义”。在参加政治活动问题上,邓中夏、黄日葵、恽代英等人认为应“为创造新政治而加入政界”,要求应容许会员参加政治活动,以求探寻切实改革政治和社会的办法。陈启天当即表示绝对反对加入旧政界,认为加入旧政界将会被同化而坏。一些会员则认为学会不是政治团体,也就不应以团体名义参与政治活动,他们对于“学会是否到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时候?会员是否有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表示怀疑。最后,为了缓和矛盾,避免分裂,恽代英在讨论确定主义的议题时,提出了“求个最小限度之一致”的建议。但他随即意识到这个希望是不现实的,因而主张“学会非破裂不可”。南京大会后,少年中国学会虽未立即分裂并继续维持到1925年,主要是由于会员之间的个人感情而致。但实际上,学会已名存实亡,会员也已各行其是,分道扬镳:李大钊、邓中夏等成了中国早期的共产党员;曾琦、李璜等人,组成了反苏反共的国家主义派。其余的大部分成员,则在政治上逐渐消沉下来,单纯致力于教育、新闻、工程、农业和科学研究活动。
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化后,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派”和“十月革命”型的社会主义,不仅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划清了界限,并且实际上独占了社会主义的旗帜;而赞成或者倾向改良主义思潮的人们中的大多数,则抱着可贵的爱国热情,以自己的专长,从事他们称之为“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和“卫生救国”等有益于祖国前途的事业,并对中国共产主义者领导的革命运动,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同情。他们自己大多也成为以后民主党派的积极筹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