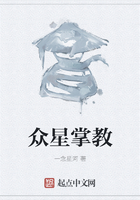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尉越涧早上起来后,发现气候骤然变了。北风吹得一阵紧似一阵,潮湿的雾气罩得看不清人,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阴雨来,从房屋伸出来的烟管,冒出了黄褐色的浓浓的柴炭烟子,朝阳的清晨一片昏沉。
经过一夜的休息,尉越涧沉郁的心情略有放松。他在市委招待所吃过早餐,便匆匆打道回府了。
他没走来时的路,而是选了一条近路。这条路危险难行,回到金江县城,要途经谷脑、脑店、铁厂等乡镇。他是想看看沿途情况,找回一副好心情。汽车过了牛栏江便开始爬坡,10点半到了谷脑的街口。此时,他发现走这条路是一个错误——谷脑正在改造街道。
他从街口一眼看过去,街道上,两旁的房屋被拆除了不少,房屋的土墙被挖垮下来,街道两旁被壅塞起来,散落在地的泥巴坨坨将街道弄得乱七八糟。司机异常小心,车子走在满是泥浆的街心上,好像在扭着秧歌。车子在慢慢滑行中还熄了几次火,司机骂了几次娘,才把车开到了街子中间。街子西面人声鼎沸,成百人吆喝着号子挖方运土。
老张问:“尉书记,我们是朝前走,还是到乡政府?”
尉越涧说:“不必惊动乡上了,我们继续走吧。”
车子继续慢慢前行。施工地段,吆喝声伴着特别尖厉刺耳的叫骂声。尉越涧朝前看去,一个中年婆娘在指着人大骂。司机按了两声喇叭,两个干部模样穿着水鞋的年轻人,看见了县委书记的车子,在稀泥烂浆中跑着跳着过来了,尉越涧看清是谷脑乡党委书记晋阳和副乡长许贵。他赶忙下了车,双脚陷入稀泥汤汤,一双皮鞋被泥浆糊了大半。晋阳的脸上阳光灿烂,许贵的笑容中却现出淡淡的忧伤。他们身后不远,跟着那个穿毛蓝布衣服的中年妇人。女人嘴里不干不净骂着“许贵,你这个烂杂种!”之类的脏话。
晋阳和许贵的裤脚挽到了膝盖上面,裤子上糊了一层厚厚的泥浆,夹克衫被星星点点的泥污染成了迷彩服。
尉越涧心里叹道:许贵被这婆娘骂惨了,依然是一副笑脸,真不容易啊!
晋阳上前双手紧握尉越涧的手,尉越涧感觉这只手糊满了泥巴。
晋阳问:“尉书记,你从朝阳来?”
尉越涧笑容可掬地说:“从朝阳回来。参加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表彰会。到了街口,才知道你们在修街。”
他伸手握住另一双满是泥巴的手,触到了手掌心的血泡。他抚慰说:“许贵,你们辛苦了!”
中年妇人蹿过来站在晋阳旁边,看了尉越涧一眼。尉越涧想缓和一下气氛,对她做出了一个笑脸。不料,这女人手指着许贵大骂起来:“许贵,烂杂种,你的心肠给狗吃了?把老娘家的房子挖了就算了吗?”
须臾之间,尉越涧和晋阳脸上的笑容凝滞了。许贵僵硬的笑脸倏地拉长了。施工地段,人们停下手上的活计,眼光一齐盯着他们这面。尉越涧瞪了这婆娘一眼,又向许贵丢去一个冷静的眼神。许贵似乎没有领会尉越涧的意思。此时,他太恼恨这个刁钻的恶婆了——老婆娘,你让我在县委书记面前丢了面子。
他怒不可遏,紧握右手,大吼一声:“你想咋个?”
妇人毫无惧色,叫道:“赔老娘家房子!”
许贵的拳头握得更紧。晋阳给许贵使了一个眼色。许贵看见了,把拳头放松了,用不高不低的声音说:“给你家补偿,你家不干嘛。”
妇人吼道:“你那一小点钱,是哄娃娃吗?”
许贵无可奈何,只好不开腔了。那妇人嘴里还在骂着。尉越涧冷眼斜看这个婆娘,想着说什么话来劝导。
晋阳劝导说:“曾大嫂,你骂脏话不对。你看许副乡长,人家都忍了。俗话说,‘好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有啥子嘛,好好地说嘛。”
乡书记说了软话,妇人瘪了一下嘴,说话的嗓音小了一些:“晋书记,不是我这个老婆娘硬要骂人。许贵哪里会像你说话和风细雨的。找着他呀,横憋憋地就甩你几句。”
不识字的婆娘也会略施离间之计。
晋阳说:“许贵与你家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怎会与你家过不去。他也是为了谷脑乡的事嘛,修出一条伸展的街子,你们做小买卖的,生意也兴隆一点嘛。说实话,我们累得心头烦,有时说话不好听,你就原谅好了。”
妇人看看那辆三菱车,猜测尉越涧是县上的大官。她瞥了尉越涧一眼,尉越涧是一副冰冷的脸孔,他眼神中含着愠怒。她分析,闹下去定然不会有啥好果子吃。她的态度明显和缓下来,以进为退地说:“晋书记,你说,原谅许贵,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今天就原谅他一回。如果不把我家的事解决好,我是不应的啊。”
晋阳看到自己递去的楼梯,妇人还是爬了。他希望她尽快从梯子上下来,当务之急是把这个女人支走。他笑着说:“曾大婶,你看到的,县上领导来了,我们还要汇报工作,你先回去。下午,你来乡政府,我们一起再商量,好吗?”
妇人听了,露出了笑脸说:“晋书记,还是你说话受听,我这就走了,说话要算数啊。”
妇人说罢,转身一溜一滑地走了。晋阳看着尉越涧开心地笑了起来。许贵脸上泛出了一片苦涩。民工们看这边没事,又开始吆喝着干活。
尉越涧问:“这妇人怎会乱骂许贵。”
晋阳说:“尉书记,我们修这条街,太得罪人了。要拆除一些单位的房子,涉及到的单位,大部分都支持,说是拆了也好,他们可以给上面要钱修新的。只有一个单位拗着不同意。”
尉越涧问:“是中央军还是地方军?”
中央军是指中央和省直管的单位,地方军是指县乡管的单位。
晋阳说:“是中央军。还好,左说右说,总算做通了工作,他们答应给上面反映。”
尉越涧“哦”了一声,没有再去追问是哪个单位。
晋阳说:“拆私人房子就难了,开始工作做不下去,阻力太大了。我和许贵商量,不来点硬的,就干不成事。许贵说,他来唱白脸,说我是主要领导,叫我唱红脸,我们两个一个来硬的,一个来软的,得罪人的事都由许贵做了。不知劳了多少神,费了多少力,总算都拿下来了,就这个姓曾的婆娘家是钉子户,软硬不吃,油盐不进,横竖做不通,骂了许贵好多次了。”
许贵脸色活泛多了,说:“尉书记,只要办得成事,挨点骂也值得。今天下午,这个婆娘肯定还要来吵。我们坚持一条,就是补助标准坚决不改,改了将就她家,就一动百摇了。她骂她的,我们不理就是了。”
尉越涧说:“补助标准定了,就不要改,拆房的都要一视同仁。不过,有人想不通也正常,不管人家怎么骂,你们都要冷静,决不能轻易抓人关人,多讲些道理。”
晋阳连忙说:“尉书记,我们不会关人。”
他又对许贵说:“难为你了,如做不通工作,我们再找人从旁劝说。”
许贵点了点头,倏然一笑。
尉越涧问:“晋阳,你们修街,连我也瞒了?”
晋阳做了一个鬼脸,说:“尉书记,我们不是想瞒你,想把事情做成了,再请你来指导。”
尉越涧哈哈笑了,说:“你们两个鬼得很,还藏着一手呢。街修好了,才请我指导?”
三人一齐开怀大笑,笑得舒畅开心。
尉越涧问:“你们这个项目是怎么立起来的,从哪点找来的钱?”
晋阳不无得意地说:“老老实实地报告书记,要说正儿八经的立项,也倒没有。县上给了一小点钱做药引子。我们发动大家捐资,我、许贵和乡长每人带头捐了500元。县政协的金副主席是谷脑人,他说家乡这条街早该修了,他就捐了1000元。乡机关的干部,还有个体户,都多多少少捐了一些钱。”
许贵说:“晋书记领着我跑省里,跑市里,找朋友讨口化缘,也找了一些钱来。”
尉越涧被感动了,却又不好表扬他们。他在为晋阳、许贵担忧:这两个小子脑袋瓜子灵得很,干劲的确很大,但是,立项都没立,就干工程,风险不小呀。
许贵看着尉越涧踌躇的脸,一下就猜中了县委书记的心思,他自信地说:“尉书记,找来这些钱,晋阳我两个,保证包包头不装一分钱。小平同志今年南巡讲话,鼓励我们大胆试,大胆闯,说干错了,改过来就是了。我们想,把街修好点,给谷脑人民造点福,总没得什么错嘛。”
尉越涧心里一叹,爱怜地想:初生牛犊不怕虎,后生可畏啊!但是,你们毕竟年轻了一点,并不真正懂得官场的潜规则,有些事出了差错,总要去找替罪羊,真要做了牺牲品,改过来再干的,恐怕就不是你们了。
他不想泼冷水,转眼望望那些干活的民工,仰起脸来问:“晋阳,修街这些人,恐怕都是村子里头的农民吧?”
晋阳说:“书记说对了,这些民工都是各村各社调来的农民。”
许贵说:“我们把任务分到村,村再分到社,社分到各家各户,各村各社打轮子,每天抽调百来个农民,早上来,晚上回去。”
尉越涧问:“农民干一天,你们给多少补助?”
晋阳说:“这些农民自带工具,自带干粮,中午吃洋芋,吃荞麦粑粑,收工回家吃晚饭。说实话,我们没给过补助。”
尉越涧心里又是一叹:早已否定的大跃进精神又回来了。不给补助,不是一平二调吗?农民一定意见不小。
他板起脸问:“你们这样办,农民没有意见吗?”
晋阳说:“群众没得意见。我们专门拟了一个宣传提纲,要求村社干部大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农民听了宣传,高兴得不得了,说他们今后赶街,就不会稀泥烂糕的了。”
许贵说:“中秋节的晚上,我和晋阳出来转,看到一个年轻妇女,背着一个娃娃挖土方。晋阳问她,你是哪点的,她回是街子背后的。我问她为啥一个人来挖,她说,他们社把土方分到各家各户,她的男人出去打工了,她又要忙地头,又顾着这点任务,只有晚上才有时间来挖。我和晋阳很受鼓舞,回去拿了工具,与她一起挖,挖到半夜才挖完。我们还拿了月饼来,给她和娃吃了。”
尉越涧心里又是一叹:多好的老百姓呀!此时此刻,他的心底对晋阳、许贵,生出无限赞许之情。他想起了年初研究谷脑班子时,县委常委会还发生了争议,一些同志认为晋阳28岁、许贵23岁,任党委书记、副乡长实在太嫩了。他力排众议,常委才最终作了这个决定。却没想到他们干了不到一年,谷脑的面貌竟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他想:用干部也要敢冒风险,在那些局面沉闷的地方,还得起用有闯劲的年轻人冲冲。
尉越涧没看见乡上其他人,感到有些奇怪,问:“你们乡上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晋阳说:“尉书记,修造街道的事,党委政府讨论过好几次,班子同志的意见是统一的。其他同志都是本地干部,我安排他们下村做其他工作去了。”
尉越涧的疑问消除了,更加放下心来。他想:如果没有乡上广大干部的支持,就你两个年轻人跳独角戏,恐怕不行。
稍后,晋阳手指施工地点说:“尉书记,昨天下午,那个地方炸了两间房子。昨晚下雨,后山又塌方,把那点堵起来了,可能要下午三四点钟,车子才过得去。你们是不是把车开回乡政府,吃了饭,睡个午觉再走?”
尉越涧心里想,说是三四点钟通车,到时恐怕走不了,还要在此过夜,便说:“时间太晚了。我还必须赶回县城。我们马上调头,倒回去,从牛树走。”
许贵说:“尉书记,你倒回去,要多走出三个小时的路。既然你要忙着走,我看这样,我们发动农民把车给你抬过去。”
尉越涧调头看看街那头,又扭过头来,用怀疑的语气说:“怕抬不过去吧。”
晋阳很自信地说:“书记,哪样抬不过去。昨天市教育局长从金江过来,把车子开到这里,他下车看看,也说要倒回去,绕道从牛树走,我们还不是硬把他的车子抬过去的。”
尉越涧还在低头沉吟。许贵就劈劈扑扑地跑着过去,开始发动民工。
许贵高声喊道:“老乡们,请大家暂停施工。县委尉书记有重要工作必须赶回县城,请大家帮个忙,出把力,把车子抬过去!”
民工把手中的锄头、铲子和撮箕纷纷丢到一边。司机发动车子慢慢开到塌方处便下了车。
许贵振臂高呼:“老乡们,力气大的抬车,力气小的,扶的扶着点,帮的帮着点,一定要把车子抬过去!”
农民抢着来抬车。许贵不停地高喊:“注意安全!……”
“起!”
“使力!”
“加油!”
在呐喊声中,车子被摇摇晃晃地抬起来,一些没摸着车的人,扶着抬车的人,推着他们的背。呐喊声、吆喝声中,人们将三菱车生生抬过10多米的堵塞地带。
许贵喊:“大家好好抬着,千万不要放,我喊一二三,大家再放下来。”
老百姓抬着车子,等着许贵下令。
许贵大声喊着:“一、二、三!”
车子一下蹾到路上,人群欢呼了几声。
尉越涧尾随着人们,一溜一滑地走过了塌方地带。他的脑海里闪现着电影《英雄儿女》的镜头,想起朝鲜人民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长的车抬过断路的动人场景;他深深为眼前谷脑百姓的热情而动容;凉风凹事件发生后,缠绕在他的头脑里的阴影全然消失了;他离开朝阳时的阴郁心情被百姓的欢呼声一扫而光。
他穿过人群走近车子,站在车子前头,把腰深深地弯下去,给这些一身泥污、满脸憨态、心地善良的农民鞠了一躬。晋阳、许贵带头鼓掌,农民跟着一齐拍着巴掌。尉越涧慢慢直起腰来,满眼泪水涟涟。晋阳、许贵甜甜地笑了。尉越涧紧握俩人的手,说了一声“谢谢”。他恋恋不舍地上了车,吉普车满载谷脑人的深情厚意奔驰而去。
离金江越来越近,气候也逐渐暖和起来了。尉越涧感觉自己从躯体到心境,似乎从寒冬回到了暖春。吉普车过了水淌河沟,夜幕已悄悄降临了。他看见县城活了,城里一片灯火辉煌。他不由得心花怒放,兴奋地大喊了一声:“通电了!”
司机的心情也很振奋,轰着油门提速飞驰向前,10多分钟就进了金江县城,车子从县委会的老门驶入大院。尉越涧听到月潭公园传来锣鼓声和歌唱声。他想:月潭历来是金江人会聚之地,晚饭后,必有一段时间喧闹嘈杂。离开县城不几日,自己竟会产生如此新鲜之感。车子停稳后,他下了车,侧耳仔细倾听,才觉锣鼓点子纷乱,歌声不似往常,不觉有些诧异。他快步走到新修的县委会堂,顺着楼梯往上爬,爬到二楼走道上。他眺望对面的情景,发现月潭公园游人稀疏,几棵大榕树下竟然搭起了帐篷,帐篷中不断传出鼓声锣声,还有“那呀么,阿弥陀佛”的歌唱声。他还是第一次耳闻目睹月潭公园出现这般奇异情况。他马上断定县上出事了。他从谷脑带回的喜悦,以及初见县城灯火通明的兴奋,顷刻之间便跑得无影无踪。他快步跳下楼梯,直奔新修的县委宿舍楼。他走之前,曾来自己的新居看过,知道屋里已经装了电话。他跑上二楼,从包包里找出钥匙,迅速打开寝室门,看见屋里摆了一套转角大沙发,主卧室里摆了张大床,客房放了张小床。他提起茶几上的电话,先后拨通李聪晔和汪亮福电话,通知他们赶快过来。
几分钟后,李聪晔来到尉越涧宿舍。他笑着说:“书记,今晚,这里恐怕还睡不成。”
尉越涧说:“今晚肯定不在这里睡。我们先在这里研究工作。聪晔,县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李聪晔说:“书记,月潭公园发生了一件怪事。你在路上,没办法联系。”
尉越涧“哦”了一声,定定看着李聪晔,盼着他尽快说出事情的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