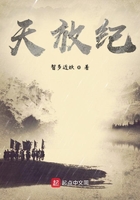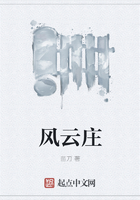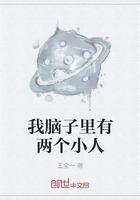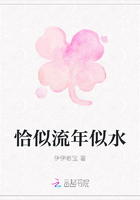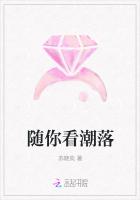1584年(万历十二年),已故内阁首辅张居正遭到明神宗的清算,被后人称为“张居正改革”的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最后一次自救运动宣告前功尽弃。次年,春秋仅历23年的明神宗朱翊钧即着手让臣民为自己营建寿宫。工程穷奢极侈,历时5年,耗银800余万两,相当于万历初年明朝政府两年的财政收入,约折合当时一千万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这就是北京昌平县境内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建陵期间,工匠、民夫中的老弱饥苦者,不胜繁重的劳累,饿死、病死、累死者不计其数,惨不忍睹。
建好了死后的天堂,朱翊钧便毫无顾忌地放纵于酒色之间。他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忤,辄毙杖下。他日日歌舞,夜夜交欢,沉溺于女色之中。除了淫乐外,他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增加皇室私库中的银子。早在1578年(万历六年),他就扩建皇庄,在南直隶长江两岸占地267顷,在顺天府占地21 000余顷。他花起钱来,就像搬动银山一样。皇长子及诸王“册封冠婚”,挥霍白银934万两,而袍服费270余万两在外。有一次光采办珠宝,就费银2 400万两,而宫廷每年所用脂粉的费用高达40万两,年例织造龙袍料多达15万匹。如此庞大的开销,财源是个问题。他开始是向国家各财政部门要。如皇女出生,他诏户部、光禄寺各进银10万两;公主下嫁,宣索至数10万两。但到万历中期,国家的财政已是入不敷出。1592年(万历二十年),平定宁夏哱拜叛乱,费银200余万两;同年冬天,援朝抗日战争开始,首尾8年,费银700余万两,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费银约300万两,国库告匮。而早在1596年,乾清、坤宁两宫失火,1597年,皇极、建极、中极三大殿又付之一炬,营建乏资,主管财政的大臣束手无策,只好奏请捐俸助工。
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库里已经取不出什么银子了,朱翊钧干脆来一个直接掠夺。他向全国各地派出矿监税使,以开矿收税为名,把工商业者作为主要的掠夺对象,聚敛大量财富。对于他来说,他根本不会认为这是一种对人民的掠夺行为。1590年,曾有人批评他贪财,他却理直气壮地说:“朕身为天子,富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的财富,皆是朕的,贪财从何说起?”何况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认为工商是末业,对末业多征一些税,未免不是重农的办法。于是,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朱翊钧派出大批亲信宦官,分赴全国的各矿区和主要工商业城市、港口,充当矿监税使,抛开国家机关,直接对人民进行掠夺。
矿监税使可以专折奏事。朱翊钧对国家大事不予理睬,对矿监税使的奏章却格外重视,所以,“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有了皇权的全力支持,这些矿监税使便如同豺狼一般,肆行无忌,“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邱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他们强夺民财,“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
矿监税使是一批“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王法之事”,所收税款无帐可查,官府也不能过问。据记载,从1597到1605年,各地矿监税使进奉给朱翊钧的白银为300万两,还不到他们掠夺的十分之一。
矿监税使的掠夺,弄得全国“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迁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老百姓们“怒忿无处可伸,郁结无时可解”,于是掀起了抗暴图存的斗争。1599年,湖广荆州商民数千人,“飞砖击石”,反抗税监陈奉;同年,山东临清商民罢市,万余人纵火焚烧税监马堂的衙署,击毙他的党徒37人。1601年,苏州织工葛贤(原名成)领导数千名失业织工,打击税监孙隆,杀死他的参随,焚烧恶棍的住所,将税官投入河中,孙隆逃往杭州。同年,武昌发生民变,反抗税监陈奉。1603年,北京西山煤矿窑民,成群结队到北京示威。1606年,云南百姓杀死矿监杨荣及其走狗200余人。1608年,锦州军民大暴动,反抗税监高淮的掠夺。1614年,福建漳州商民暴动,反抗税监高案。当时全国发生的市民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大小不下数百起,说明明朝的专制皇权已完全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然而,面对人民的反抗,朱翊钧毫不醒悟,直到死去才撤回了这批豺狼。
在朱翊钧派矿监税使四出搜刮、掠夺城市工商业者的同时,明朝政府陷入越发严重的财政危机,于是饮鸩止渴,大肆加派。早在嘉靖时便有称为“额外提编”的田赋加派。1602年(万历三十年),江、浙田赋加派120万两。使广大小土地所有者彻底破产的是“三饷加派”。1608年(万历四十六年),因辽东用兵,按亩加派“辽饷”,共加3次,亩均9厘,全国总额为520万两。崇祯时加派镇压农民起义的专款“剿饷”和“练饷”1 010万余两。“三饷”共计1 530万两,超过田赋正额许多。而官绅地主享有优免特权,加派就全落到贫下户的头上。由于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更是层层加码,“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明末,地方官到北京接受朝觐考察,谋求升职,每人至少要花五六千两银子行贿打通关节。巡按御史到各地查盘缉访,地方官馈遗奉迎,多至二三万金。这些钱款都是官吏从老百姓那里勒索的。所以,当时人慨叹:“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
专制君主、贪官污吏敲骨吸髓的剥削、掠夺,加上明末60余年的连绵灾荒,逼得人民走投无路,明朝政府“欲使穷民之不化而为盗,不可得也”,“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1588年(万历十六年),湖广黄、蕲地区发生梅堂、刘汝国相继领导的农民起义。1622年(天启二年),白莲教徒徐鸿儒在山东郓城发动农民起义,部众达数万人。各地农民抗租、奴仆造反的事件更是此起彼伏。而从辽东溃败的散兵残卒,不但得不到政府的抚恤安置,反而惨遭堵杀,也纷纷加入了抗暴图存的队伍。
到天启末,在明朝黑暗统治下的失业工商业者、破产农民、溃散的兵士,已经汇成埋葬朱明王朝的熔流,只待掀开进发的火口。
然而,腐朽贪婪的明朝统治者,却依然我故。
朱翊钧除了贪财好色外,既不御经筵日讲,也不亲临郊庙祭祀,臣下要求改善朝政的奏章,他一概留中不发,缺额的官员,也都不予补充。官员们对他已丧失信心,很多人上疏退职,也不等皇帝的批示,径自挂印而去。1602年(万历三十年),两京缺尚书3人,侍郎10人,科道94人,地方缺巡抚3人,布、按二司官66人,知府25人。1605年,南北两京大僚强半空署,督抚重臣经年虚席,布按二司缺50~60人,知府缺40~50人。1609年,北京朝廷的阁部大臣,内阁仅有叶向高1人,九卿(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司使)中在朝供职的,只有都御史1人和侍郎2人,其他的则或因缺未补,或闭门不出。
官僚集团不但对皇权失去了信心,而且内部也分立党派,争论不已。1605年,被革职回家的吏部郎中顾宪成(1550—1612年),修复无锡东林书院,提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口号,召集志图改革政治的同道,以讲学的形式,“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希望借此影响朝政。他们被大贵族、大地主集团看作为“东林党”。东林党形成后,与东林对立的有浙、齐、楚、宣、昆各党,他们勾结当权派,迫害东林人士。这一追害到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时达到登峰造极。
总之,在万历年间,明朝已是纪纲大坏,王纲解纽,崩溃的形势已经形成。乾隆皇帝在为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撰写的碑文中说:“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
神宗的荒唐贪婪,加上天启的昏庸、魏忠贤的乱政,明朝走向灭亡已是无可挽回。这时,东北的建州日益强盛,内地的兵变、人民起义日多一日,并且形成燎原大势,明王朝已陷入不可解救的政治、财政危机。虽然崇祯帝一心求治,但已无力扭转乾坤,何况他也不是什么圣明贤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