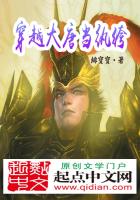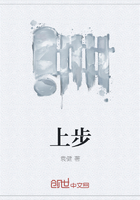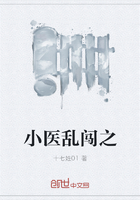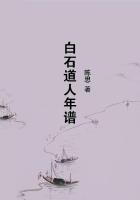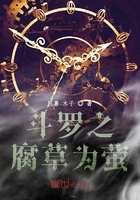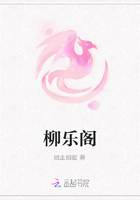根据当时人的说法,张居正是一个权臣,他的权力与宰相并没有什么差别。
按照明朝的中央决策体制,最高决策圈由皇帝与司礼监、内阁组成。司礼监与内阁都不是过去的宰相,因为他们不是百官的总辖,不能对各部、院直接发号施令。他们只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只对皇帝负责。但这只是在皇帝能履行他的正常职能条件下的一般情形。如果皇帝不能履行他的正常职能,那么,他的威权就必然要委寄于内阁或是司礼监,因而就会出现阁臣或是宦官专权的现象。但在明朝历史上,专权宦官多于专权的阁臣,而且影响也更坏。专权的阁臣中虽然也出现过像严嵩那样的奸臣,但由于阁臣不能掌管特务机关,又往往是文官集团的代表和国家长远利益的代表,所以阁臣专权相对来说还能刷新王朝的政治。
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时,正遇上一个不能亲理国事的十岁天子,又取得了司礼掌印太监和天子生母的支持,一切条件聚合在一起,使他成为了实际的摄政者,在1573年至1582年(万历元年至十年)的10年间,能够进行一场被现代历史学家称作“改革”的政治振作运动。
张居正的政治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强公室,杜私门”,也就是要树立中央政府的威信,提高国家机器的效率,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
他的首要措施是推行考成法,提高行政效率。所谓考成,就是考察成效。考成法的具体做法是:各衙门设置三本簿籍,一本登记本衙门的所有来往公文和办理的公务,留为底册。然后将例行公事无须查考的剔除,再造两本同样的簿籍。一本送交与六部相应的六科备注,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如有未按时完成的事务,即由该科具奏请示处理。一本呈送内阁,以备阁臣随时查考六科与六部的事务。
考成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内阁在明朝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用六科来监督六部,是从明初就定下来的制度,但用内阁来监督六科进而监督六部等机关,却是张居正的创造,从而提高和扩大了内阁的实权。
通过对考成法雷厉风行的推行,张居正在掌权期间,淘汰了不称职的官员,注意选贤任能,行政效率大为提高,中央发布的命令和下达的任务,“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行政效率的提高使明朝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振作起来。
在财政方面,严格的考成制度使各地拖欠税粮的现象迅速改观,从而扭转了嘉靖中期以来,政府“帑藏匮竭”的状况,达到“自正(德)、嘉(靖)虚耗之后,至万历初十年间,最称富庶”的局面。
张居正在财政方面的最显著成就是清丈了全国的耕地,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
从1578年(万历六年)开始,明政府用了三年时间对全国耕地进行清丈。清丈的结果是全国的耕地总数为7 013 976顷,比1502年(弘治十五年)的4 228 058顷增加了2 785 924顷。增幅达50%以上。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增长,原因是把相当一部分被贵族豪强和军官隐没的庄田、屯田清查了出来。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地方官为了完成规定的指标而虚报的部分。清丈明确了产权和应该负担的赋税额数,为一条鞭法的推行创造了条件。
一条鞭又称一条编,是将种种不同的赋税徭役项目简化为一条合并征收的意思。它是在地方官几十年的行政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它的基本内容有:(1)赋役合并征收。(2)合并各种力役项目,用雇役取代。(3)除朝廷所需的粮食仍征实物外,其余一概征收白银。(4)赋役银两统一由官府征收解运。
一条鞭法的实施,使明朝的财政体制由实物体制转化到货币体制。这一转变,对明朝政府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有利有弊。
从有利的方面看,它适应了15、16世纪以来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状况,反过来又促进了这种状况的发展。其次,它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实行雇役后,农民用不着亲身去服劳役,有了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对国家的依附关系松弛了。另外,赋役合并实际上就是将课税客体单一化。以前的课税客体有二个,一是耕地,二是人丁(劳力),前者称为赋税,后者称为徭役或力役或劳役,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前者征取的是物化劳动,后者征取的是活劳动。赋役合并后,劳力就逐渐成为次要的,甚至不再成为课税的对象,而以前从劳力征取的那部分赋税就转从耕地上征收。下层劳动群众往往是劳力多而耕地少,所以赋役的合并对于减轻劳动人民的负担,使税赋与财产的占有状况更加一致,从而也就更为合理。
可以说,一条鞭法是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新税制。但是,封建的专制制度却没有为新税制发挥良好的社会效益提供必须的政治环境。
一条鞭法使明朝的财政体制由实物转向货币。在实物体制下,政府的财政是凝重、稳定的,主要与农业的收成及各种国务开支发生关系。在货币体制下,政府的财政不但要受以上因素的影响,而且还要受国内、国际市场的影响。君主专制制度不但没有将这种新的影响转化为积极因素,反而变成了消极因素,使新的财政体制充满了不稳定,显得很脆弱。
一条鞭法的法定支付手段是白银。而白银在当时是以它的自然形态,而不是以铸币的形态充当货币的,这种货币被称为称量货币。这样,政府就无法运用控制货币发行量的手段去调控国民经济和政府财政。
另外,中国是一个贫银国,作货币用的白银绝大部分依靠进口。进口白银的数量虽然很庞大,但仍然满足不了国民经济的需要。其实,货币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可以人为地加以设计的,不过必须得符合客观的经济规律。由于缺乏足够的贵金属充当货币,中国很早就出现了替代物——纸币。我国纸币的起源可上溯到9世纪唐代的飞钱。宋代称为交子、会子。元朝是发行纸币较成功的一个王朝。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纸币发行最不成功的王朝。洪武年间,明朝就发行了“大明宝钞”。但明朝廷既没有准备金,发行量又没有限制,只是一味地禁止民间使用金银贸易,结果,没过多久,宝钞便形同废纸,只能默认,然后是公开承认白银作为货币的合法地位。然而,这样一来就等于明朝政府放弃了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足够通货的努力。这是导致明朝晚期银荒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通货的不足,直接的后果是白银聚敛。由于白银短缺,白银价格上扬,人们就愈将它视为绝对的财富窖藏起来,使数量巨大的白银退出流通领域,加剧了短缺。更为糟糕的是专制皇帝直接参与了白银聚敛的活动。万历皇帝在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到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的25年间,派遣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以开矿收税为名,对人民大众进行巧取豪夺,引起各地市民的反抗风潮,同时对工商业造成极大的破坏。皇帝之所以要直接掠夺白银,是因为他那谁也无力限制的贪欲被白银这种贵金属极端地刺激起来。在实物财政体制下,征收的都是实物和劳役。劳役不能贮存,实物能贮存,但仍有时间的限制,粮食保存不妥就会霉变失去价值。同时,实物充当一般价值的功能有限,只能满足特定的需要,所以皇帝的贪欲受到限制。但白银却不同,它是贵金属,充当一般价值的功能很好,又便于贮存,拥有了它便有了一切,它简直就是财富本身,所以皇帝对它如醉如痴,若疯若狂,想无止境地攫取它,占有它。不但想有生之世占有它,还想将它在死后、在来世永恒占有。万历皇帝在1584年,22岁时(万历十二年),就亲自监造“寿宫”(定陵地下宫殿),费银800万两,相当于万历初年两年的田赋收入。皇室的其他用度更是穷奢极恶。皇长子及诸王的册封冠婚用银,高达934万两。重修宫内三大殿,仅采木一项就耗银420万两。宫女的胭脂费,每年用银40万两。在君主专制时代,皇帝私人金库与国库虽有形式上的分别,但天下都是一家一姓的私产,所以皇帝往往将国库作私囊,经常以花销太大向国库索取大量现银。
私人聚敛白银以皇帝最为穷凶极欲,此外,各级官吏也大都是如狼似虎。因为在政治体制上,当时根本不存在有效的限制官吏贪赃婪贿的机制。
上自皇帝,下到各级官吏的贪婪聚敛白银,使一条鞭法给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所带来的积极作用丧失殆尽。他们一方面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危机,另一方面使人民遭受的剥削愈加沉重,最终人民大众难以聊生,便揭竿而起,与贪婪的统治者玉石俱焚。
可见一条鞭法本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是符合历史前进步伐的,但是,罪恶的君主专制及中央集权,葬送了这一切的好处。要改变君主专制制度和过度的中央集权,是张居正无法想象的。只有到了明末清初,我国的启蒙思想家们,特别是黄宗羲,才对传统的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做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反思和批判。
张居正振作集权政治的措施在边防和治河方面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他调任抗倭名将戚继光坐镇蓟州,整饬并加强了长城沿线的防务。又选派李成梁镇守辽东,一方面防御蒙古,一方面镇抚女真。所以在张居正执政时期及其以后的二三十年中,明朝的北方和东北的边防比较巩固,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明朝与蒙古及女真族的经济文化联系也较密切。1581年(万历九年),顺义王俺答病故,其妻三娘子控制鞑靼政权,接受明朝“忠顺夫人”的封号,与明朝保持和平互市的关系。
1576年(万历四年),黄河在苏北决口,河口淤塞,黄水侵淮,淮安、扬州、高邮、宝应之间的广大地区成为一片汪洋。当时管河官员们的意见不一致。1578年(万历六年),张居正荐用水利专家潘季驯督治黄河。潘季驯采用“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办法,在黄河与淮河之间筑起延袤八百里的两个大堤,把黄、淮分割,只在海口处会合入海。于是被淹没的土地涸出,又变成了良田。潘季驯总结治河经验的著作《两河管见》和《河防一览》,是我国水利史上的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