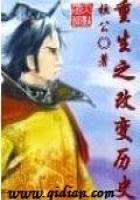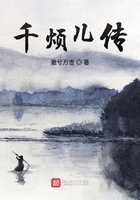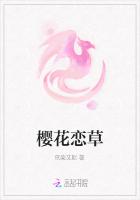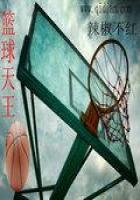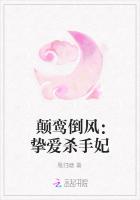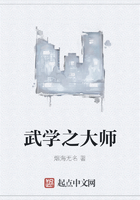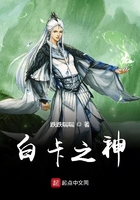1403年2月4日(永乐元年正月十三日),永乐帝在南京的南郊举行完大祀天地的典礼,回到宫城中的奉天殿,文武群臣向他匍匐叩拜,山呼万岁,庆贺大祀典礼的完成。古书上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谓祀就是祭祀,戎就是征伐。可见自古以来,祀和戎一样,在国家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祭天地又是祀中头等重要的。祭祀天地是天子、也就是皇帝的专有权。它象征着天子的权力来自天这一最高主宰,具有神圣性。永乐帝这回是他夺取皇位以来第一次举行大祀天地的典礼,他也许觉得,天并不那么可怕,原来只不过是自己手中的一根魔杖。
他很高兴,踌躇满志,在群臣的山呼万岁声中,宣布恢复被建文帝废黜的周王、齐王、代王、岷王的王位。
诏书宣读完毕,群臣异口同声赞叹永乐帝维护了太祖的旧制。这时,礼部尚书李至刚出班启奏:“自古以来,帝王或是由平民出身平定天下,或是由外藩入承大统,对于肇迹之地,都有升崇。臣私下认为,北平布政司是皇上承运兴王的地方,应该遵照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
李至刚的这番话说到了皇帝的心尖上,永乐帝当即允准,“其以北平为北京!”
2月19日,永乐帝下令设立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北京行部、北京国子监,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其他带北平字头的衙门一律换上北京字头,同时撤销北平布、按、都三司。
1406年(永乐四年),永乐帝下诏从明年开始营建北京。1407年,皇后徐氏去世,永乐帝并没有把她安葬在南京,而是从1409年开始,在北京昌平县的天寿山开始营造自己的寿陵,到1413年(永乐十一年)完工,就将徐皇后安葬在里面。这就是北京明十三陵中的长陵。这说明,永乐帝至迟在1409年已经下定决心要将都城迁到北京。
永乐帝觉得,南京是一个令人感到不安的地方,他在这里找不到安全感。
皇考太祖朱元璋就静静地躺在紫金山麓的孝陵中,默默聆听着大千世界的纷繁事变。他要是九泉有知,怎么能容忍他的这个儿子违背他的意愿,将他亲自确立的合法皇帝的宝座篡夺了呢?为了平息皇考冥冥之中的愤怒,永乐帝曾多次请番僧大做法事,“荐福于皇考皇妣”,希望得到他们在天之灵的谅解。但是,皇考会原谅他吗?
建文帝在位的时候,对洪武时期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特别是重用左班文臣,减轻江南地主的赋税负担,深受士大夫和江南地主的拥护。方孝孺、齐泰、黄子澄为建文帝宁死不屈不用说了,就是在永乐帝夺取皇位一段时间后,还有忠于建文帝的文臣想谋杀他。有个叫景清的文臣,是陕西真宁(今陕西正宁)人,洪武年间进士,在建文时,官做到御史大夫。永乐帝夺取皇位后,他没有立即为旧主殉死,而是委蛇朝班中,寻找机会刺杀永乐帝。后来,他行刺的计划不幸被发现,永乐帝大怒,用五马分尸的酷刑将他处死,又将他的家族全部抄灭,并且牵连乡里,“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乡里为墟”。江南的地主,对建文帝更是充满了怀念,在他们的笔下,建文帝4年的统治是可以与儒家理想中的“三代”相媲美的。
与南京相比,北京给朱棣的是一种亲切和安全的感觉。这里是他的藩邸,经营了二十几年的根据地。他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习惯了燕地的干旱与寒冬,欣赏那里剽悍勇猛的民风。那些从龙的“靖难功臣”,也希望他回銮故地,好光耀乡里,保持与人主的密切关系。
考虑到以上的几个因素,永乐帝急于将北平改为北京,提高根据地的地位,充实它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作为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大本营。
当然,北京究竟与凤阳不一样。凤阳不但人民贫困,缺少建都的经济基础,而且无险可守,历史上从来没有王朝把它作为都城。北京却不一样。远的不说,就说近五百年来,先是辽(南京),金(中都)把它作为都城,后来更成为元朝完成空前大一统伟业的基地和中心。这里是中国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的交汇点。元朝在这里,依靠游牧社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首次实现了中国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的统一,他朱棣这位堂堂大明国的皇帝,难道就不能凭借农耕社会的广土众民,以北京为基地,重建一统游牧与农耕两大社会的伟业?所以,他一方面继承了洪武时期的怀柔政策,封蒙古各部落首领为王,对于那些前来投奔效顺的头目、贵族一律优遇,给予高官厚禄。至于普通的民众,就给他们划拨水草丰美的游牧地。另一方面,采取积极进取的战略,在东北设立奴儿干都司,派宦官亦失哈屡次出巡,又不时派使者联络西域,设立哈密诸卫,以切断“匈奴”两臂。在鞑靼、瓦剌顽梗不臣的时候,他不惜五次亲征漠北,最后死于回师的途中。
另外,从客观的形势看,北京也具备建都的优越条件。当时有人指出:北京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府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