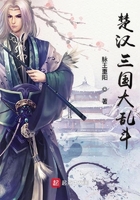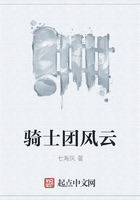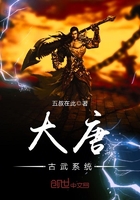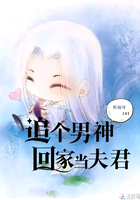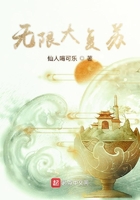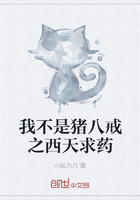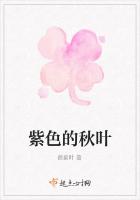朱元璋得了天下,当了皇帝,就想把这份无与伦比的产业永远占有,让它传之子孙后代,没有止境。这是每个专制君主都有的想法,并不是他朱元璋特殊。秦始皇一统中国,创立皇帝这个名号,自称一世,不就是想把嬴家的天下传之万世万万世吗?
然而,历史的实际结果却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那样。
秦朝二世而亡。秦朝以后,依旧是这片河山。主人却不知换了多少个。元朝自蒙古统一中国,版图前所未有的大,但是不到一百年,就被元璋这个出身布衣的天子所取代。他总是口口声声宣称,他取得天下是天命的眷顾。不过他内心最清楚打天下的艰难与人谋的决定作用,天命只不过是愚弄人的东西。为什么这些王朝不能永存呢?他通观从秦到元的历史,得出一个结论:王朝灭亡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权臣作怪。大臣掌握的权力太多太大,就变成了权臣。权臣作威作福,架空皇帝,结果法度不行,人心涣散,或者是造成群雄四起,天下大乱,或者权臣直接篡夺皇位。所以,他要想办法从制度上防止直至清除权臣的生成。这就涉及到丞相制度。
元璋建国时的政治制度都是模仿元朝的。中央设立三大机关:中书省、大都督府和御史台。其中都督府相当于元朝的枢密院,主管军队的征发调遣,将帅的任命,战略计划。元璋自己出身行伍,对行军作战,控制部下这一套最为擅长,因此都督府的事情大多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御史台管监察,是专门找别人毛病的,手中没有太大的军事行政权力。中书省可就不一样了。中书省是全国的政治中枢。它的机构非常庞大,设有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加政事等官,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设尚书、侍郎等官。六部主管人事、财政、礼仪、教育、科举、国防、司法、水利、土木工程等事务。中书省还统辖各行中书省(俗称“省”)。所以,中书省的权利也就特别大。
中书省的最高长官就是左、右丞相。明朝以左为尊,所以,事实上左丞相的权力比右丞相大。丞相也就是中国古代的宰相。所谓“宰”就是主宰,主管的意思,“相”就是辅佐的意思。他的基本职责是辅佐皇帝主管全国政务,地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皇帝发往全国各地的政令,必经由丞相转发执行,各地有事情报告朝廷,必须由丞相作出初步处理后转奏(报告)皇帝。除了都督府、御史台等少数几个部门外,其他部门向皇帝报告事情都必须经过丞相,在法制上,这叫做“不许隔越中书省奏事”。所以,丞相运用这个制度就可以把那些对自己有害的报告扣压下来,这就叫做“蒙蔽”。而且皇帝并不是样样都精通,许多政务都是专业性很强的,因而,丞相对政务提出的意见,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皇帝不太精明的时候,丞相经常将皇帝权力架空,极端的情况就是篡夺皇位。为了防止丞相篡权,历代帝王都想了很多办法,办法之一就是利用自己的亲信来充当秘书,协助处理政务。如汉代的皇帝就用品级较低的尚书官来协助决策和行政。原来的丞相就被架空。但是,原来丞相管的那些事情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是换了一些近侍来管理,不久,这些近侍又演变为丞相。唐宋两朝开始时都是设三省,用多相制来分散丞相的权力,但中期以后,又走向集中。金朝和元朝都只设一省。元朝除了用枢密院、御史台来牵制、监督丞相外,在中书省设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这些官员虽然有品级高低的不同,但都有宰相的权力。不过,元朝仍然出现了权相。可见,元朝的制度,对于维护皇帝的权力,也是不好的。朱元璋于戎马倥偬之间建立了明朝,没有充足的时间来考虑改革旧制度的问题,只好全盘照搬。
明朝的首任宰相是左丞相李善长。善长比元璋大14岁。1354年元璋南取滁州,谋独立发展时,他就来投奔,一直忠心追随。初见面时,元璋嘱咐他协助搞好将领们的团结,他果然不负所望,对各将领一碗水端平,建立了崇高威信,将领们都尊称他为“李先生”。这些人之间以及他们与元璋之间,有什么磕碰,只要李先生一出面,大多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善于处理纷繁多绪的政务,干净利落。元璋每次领兵出征,都让他留守应天。他总是能使后方镇静贴服,确保粮草辎重源源供给。元璋将他比作汉高祖手下的萧何。1364年设中书省,他就做了第一位丞相。1370年(洪武三年)大封功臣,他被推为功臣第一,封韩国公,子孙世袭,给铁券,如果犯罪,自己可以免二次死刑,儿孙可以免一次。当时与他同任丞相的还有徐达。但徐达是武将,长年征战在外,丞相只不过是个虚衔。所以,善长就是中书省的惟一最高长官。
当时的功臣主要是出身淮西地区的将领,他们和元璋、善长间大多有同乡的关系。善长在淮西功臣中享有威望,又掌握了政治中枢中书省,又是功臣第一,常言说,功高震主,他还得加上权大慑主一条。权力就是权力,没有什么道德良心,一个人在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完全取决于权力的大小,这个道理,元璋最有透彻的了解。所以,对善长,他就不能不提防。
所谓提防,就是对丞相的权力进行制约。制约丞相权力的第一个措施便是让御史台与中书省互相监督。元朝的御史台之所以对相权起不了监督作用,是因为御史台的人都是宰相的亲信。所以元璋就用刚正不阿,出身浙东的刘基来做御史台的长官御史中丞。1368年(洪武元年)5月,元璋到开封视察并部署北伐机宜,命丞相李善长和刘基做京城留守。临行,特意召见刘基,要他不要有什么忌讳,敢作敢为。刘基于是命令各监察御史对官吏、内侍的不法行为,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李善长对御史台的作法很为恼火。正巧,中书省都事李彬贪赃枉法的事实被揭露出来。李彬是李善长的亲信,善长亲自到刘基面前说情,请从轻发落,刘基没给面子,拟了个死罪报告元璋。元璋的批复带到京城时,正遇上天旱,李善长忙着祷神祈雨。善长问刘基:“祭神的时候也能杀人吗?”刘基说:“杀李彬,天必雨。”李彬便被毫不犹豫地杀了。8月22日,元璋回到南京,内侍们纷纷告状攻击刘基,李善长也说刘基跋扈。当然,刘基的所作所为是元璋自己允许的,但事情做得如此干净利索,元璋不免感到疑惧,又感到嫉妒。刘基素以才识卓越、料事准确著称,这难道就不会用来为他自己谋利益?想到这里,心中难免光火。当时旱情仍在继续,元璋就下诏让臣下提提建议,看有哪些事情得罪了上天。刘基上奏指出三件事有伤天意,元璋便一一照着他的建议办了。但天还是不下雨,元璋火了,寻思这老头儿(当时刘基58岁)是把自己的主意当作天意来吓唬他,便责问刘基说:“上天示警,殃及百姓。你狂瞽胡言,该负什么责任?”刘基适逢老妻去世,便请告回到老家。从刘基的事例看,用御史台制约相权,不一定就能保证不出权臣。
刘基离开南京前,曾提醒元璋,元朝的将军王保保(扩廓帖木儿)不能太小看了。果然,当年11月16日的泽州(今山西晋城)会战,扩廓部大败明将杨璟于韩店,这是明军北伐以来的首次失利。元璋想起了刘基的忠告,觉得这老头儿还有用,便又将他召了回来。
制约丞相权力的另一个措施就是采取多相制。元璋任命非淮系的文官来做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让他们与丞相之间互相猜忌、监督,使李善长在中书省不能一手遮天。
初设中书省时,元璋就任命元朝的户部尚书张昶做都事,后升为参政。又任命山西阳曲(今太原市)人杨宪等人当检校。张昶有知识有学问,对元朝的典章制度很熟悉,在进行政权建设时,这种人才是很有用的。杨宪嫌当的官小,一心想往上爬,就利用元璋对宰相们心存疑虑的心理,专门打小报告,说别人的坏话。张昶的妻子儿女都在塞北,身留江南,很是思念。元璋为了提倡臣下忠于君主的风气,便将那些忠心不改的被俘的元朝官吏放回塞北,张昶希望也能得到这个待遇,把全盘心思都向杨宪说了,并让他看自己写给家人的信。他还给元顺帝写了一封表章。谁料杨宪弄到了张昶家书和表章的底稿,一并上报给元璋,元璋就把张昶抓起来杀了。
从此以后,杨宪就更加威风凛凛,谁都不放在眼里。他对元璋说李善长没有当宰相的才能。元璋说:“善长虽然没有当宰相的才能,但与我同乡里,自起兵就侍奉我,涉历艰险,勤劳簿书,也有不少功劳。我既然当了皇帝,他当然应该做宰相。这叫做‘用勋旧’,今后不要再说了。”所以,李善长对他感到很厌恶。不过,杨宪一直官运亨通,1369年10月,升任右丞,当时平章政事一职是武将的加衔,他便成了善长的主要助手。
元璋真有用杨宪取代善长的意思,便试探性地询问刘基的意见。他先是说了一通善长的不是,刘基说:“善长是开国元勋,能调和诸将,这是他人所不及的。”元璋说:“他这个人多次想害你,你反倒为他留地步,我就请你担当这个重任。”刘基叩头说:“换宰相就好比换大厦的梁柱,必须有相当的大木。如果用小木头绑起来顶替,大厦立刻就会倾塌。”元璋又问杨宪怎么样,他知道杨宪与刘基的私交不错。刘基说:“杨宪有相才无相器。做宰相的人,必须持心如水,公平正直,不以自己的私利为转移。杨宪不是这种人。”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刘基说:“此人褊浅比杨宪更厉害。”又问胡惟庸,刘基说:“用他当宰相就好比用驿突作驾辕,恐怕会把车辕弄坏的。”元璋说:“朕的宰相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刘基说:“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勉强去做,会有损皇上的恩德。天下这么大,哪能没有适合担任宰相的人才,只是需要明主用心寻找。目前几位,实在未见得合适。”
元璋深通摆弄人的权术,当杨宪正得意时,却将高邮人汪广洋从陕西参政调到中书省当左丞,压在杨宪的头上。杨宪岂能甘心?于是遇事总是毫不退让,甚至顶撞。汪广洋生性柔弱,常常后退三分。杨宪却得寸进尺,步步相逼,做尽了文章,让御史刘炳二次上奏弹劾,将汪广洋贬谪到海南。元璋见刘炳二次上章弹劾同一人,觉得其中有毛病,就将他逮起来加以审讯,刘炳便把杨宪供了出来。李善长乘机揭发杨宪种种专权不法的罪状,杨宪和刘炳便被送去见了阎王。这是1370年8月间的事。汪广洋却因祸得福,不但官复原职,还被封为忠勤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