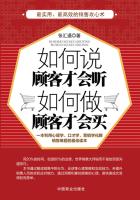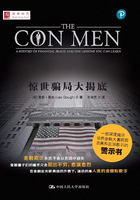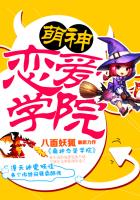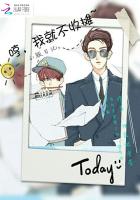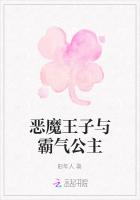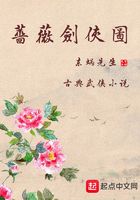在联想集团大家庭里,电脑公司一直被公认是最正规的一支部队。做个不太恰当的比喻,LAS就像匪气十足的游击队,联想科技公司(LTL,后来的神州数码)像是杂牌军,而电脑公司才是嫡系的正规军。这在早期联想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会上看得很清楚。那些叼着烟卷、着装随意的准保是LAS的;另一批着装艳丽、打扮入时的女士很可能是LTL的;而那些整齐划一、不论男女都是一片联想蓝的则肯定是电脑公司(LCS)的。
在LAS一片混乱当中,感到没有任何希望的一批志同道合者,决定弃暗投明,投奔联想正规军。既然在联想干,没有到最正规的电脑公司工作过,那算什么呢?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和一批做公安行业业务的一整套人马去了联想电脑公司。那时LAS北京的负责人还算开明,听说是去电脑公司,一路开绿灯,没费什么周折,就办好了手续。1998年3月,我进入到联想电脑公司。
按照我们当时的想法,本希望连人带业务一起到电脑公司来做。因为那时我们在公安行业的业务已经做得不错了。联想的人口软件已占到全国30%的市场份额;我们的关系已经从公安部的副部级以及主要司局长、处长,一些重要省厅,甚至一些地市全都打通了;我们具有包括常暂住人口、流动人口、刑侦、指挥中心等各种解决方案。以这些为基础,希望能使联想在公安行业上一举成为全国最大的集成商。带着这个想法,我们找当时负责市场销售工作的俞兵谈。很遗憾没有谈通,当时来看也不奇怪,那时的电脑公司主营业务就是PC,做市场销售的主导思想就是你能卖多少PC。我们曾想说明以行业系统集成为主,销售软件,带动销售PC以及服务器。但是当时俞兵最关心的就是能带动多少PC销量,当得知第一年不太可能带动太多PC销量时,就没什么兴趣了。
今天来反观这个问题,联想已经大举进入系统集成业务,按照常理我们大可以说联想错失良机。当时如果遇到战略眼光强一些的领导,很可能那件事就成了。我们看到,后来联想为了切入系统集成业务,不惜花巨资收购一些小型系统集成公司,就是在买他们的队伍和解决方案。为什么不能在当时以最小代价(几乎零投入)扶持自己的系统集成业务呢?
我现在倒愿意以平常心态来看这个问题。按前面所说,在一些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发挥到最佳,也许能把某个行业做出来。但是,那时的电脑公司毕竟没有系统集成业务,不能从整体上突破,不能形成规模优势,这种一枝独秀的局面有多大意义呢?当然我们不妨假设一种最好的情况:假如能以此为契机,扩大为联想后来的系统集成业务,那是最理想的结果。但是从各方面情况分析,达到那种结果的可能性甚微,那样的话,当时硬去做,确实意义不大。这样来分析,公司领导那时的处理大方向是对的,因为确实偏离了公司的主营业务。但从另一角度,也看到电脑公司缺乏灵活性和一定的战略前瞻性。
在电脑公司的第一年是在大客户部做行业市场工作,既然不让做系统集成,那就从头学起,老老实实按照电脑公司的思路来做。那时真是什么都不懂,只是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一到月末,其他处的同仁就神神秘秘地乱忙。后来才知道,那是在跟关系好的代理做工作,赶在财月之前,让他们下单囤货,这样就能有一个好看的报表。这招儿我到后来也没学会,倒是做了另一件事,就是前所未有地召开了一次联想行业代理培训会。我们把联想所有做公安行业的代理召集到珠海,给他们讲行业的特点,讲各种解决方案。这招儿还是挺灵的,那以后,我们的销量稳步上升。最有意思的现象是:当我离开市场系统一年后,继续做那个行业的同事用半个人的工作量(另一半做其他行业),做出了比我们原来三个人多一倍的销量业绩。这不能不说是借助于当时打下的良好工作基础。
反思那段在市场系统工作经历,一方面学到很多东西,像做计划、写报告、按照正规要求做各级考核等。这在LAS是从没做过的。另一方面也看到当时市场系统存在的问题,主要问题是市场销售人员普遍比较浮躁,人们不太愿意去做细致的用户工作,也包括细致的代理工作。最重要的事是去争资源,谁占有了更多的资源,谁就容易胜出。那时最有效的资源就是批点权,也就是给代理多少返点。按道理,什么行业,给多少批点,是有一定之规的,年初都定好了计划,应该是按月按季度来实施的。没想到执行起来满不是那么回事,那些精明的同仁一上来就狮子大开口,超指标地使用批点权,销量一下就上去了。实际上,他们等于使用了其他行业的指标。总指标是有限的,他们超量使用,后面人当然就没得使,等后面人明白过来,一切已是既成事实。造成这种情况的当然是政策制定者,所以制定政策就是鼓励人们去争有限的资源,而不是如何用有限的资源办更多的事,更不是鼓励用最小的资源,甚至不用资源去办事。我很感谢在市场系统里的那些工作经历,它逼迫人们学习很多东西,也思考很多问题。
在我觉得不太适应市场系统的工作时,一个机会向我走来。时任电脑公司总经理高级顾问的江卫星博士准备出国,他希望找个人能接替他的许多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组建公司技术发展部。
我和江博士认识是在北方系统集成公司,那时他是公司软件中心的总经理,我是副总工,经常在一起研究工作。北方集成被LAS整合后,他就聪明地回到电脑公司。这次他要出国,想起了我。
在与江博士几次交谈后,我了解到,公司技术发展部肩负着几项重大职能:
——技术发展战略研究、定期向总裁室提交研究报告、组织VP决策会等;
——技术交流与培训,包括组织研讨会、出版技术刊物、制定技术人员培训计划、出国人员管理等;
——改善事业部研发管理,包括技术职称体系、创新奖励体系、研发投入产出分析等;
——对外技术接口,包括对外合作管理、专利管理、代表公司参与学会工作等。
这些工作很多都成了后来技术发展部,以致产品链管理部的职责。我很佩服江博士,他当时提出的定位设想是那么准确,以致这些职责这么多年多数都没有本质的改变。
当时看到这么多重要职责,真的感到很兴奋,也感到这些工作很适合我。如果说,进联想后,磕磕碰碰几年下来一直没找到感觉的话,那么这次是找到感觉了。
但是还没有太高兴起来,就先受到了打击。由于江博士要走,新部门没有总经理,我们这些人按照联想的“规矩”,是不能破格提拔的。只能先“寄居”在某个部门里,这样,技术发展部就被定成为技术发展处放到了发展规划部下面。但是我注意到,在杨元庆的眼里,他始终认定了技术发展部,经常在不同场合提到某事应该是技术发展部的职责等等,起初我以为是他的口误,没想到他就没改过口,直到技术发展部真的成立。
技术发展部真正酝酿成立是在1999年年底。由于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加上我们一年的工作有些成绩,公司决定,2000年正式成立公司(集团)级的技术发展部。在得到正式通知前,已经听到一些传闻,也有一些高层人士在非正式场合,跟我半开玩笑地提到我将出任技术发展部的头儿。但是领导正式跟我谈是在2000年3月(1999财年底),时任联想集团副总裁的刘军跟我谈的话。
刘军在联想历史上也是位传奇人物,应该是联想集团最年轻的高级领导人,他1998年担任公司副总裁时年仅29岁。1993年从清华大学自控系毕业后就到联想工作,从评测做起,几年后就做到了电脑事业部总经理。他至今未婚,在联想素有“顶级钻石王老五”之称。他人很聪明,再加上运气和勤奋,年纪轻轻就坐上了高位。一些接触过他的人对他的评价较高,认为他虽年轻,但是很有头脑,显得城府很深。我也是很久前就听说过这个人物,真正近距离认识他是在1999年,江卫星走之前,把我正式介绍给他,让我有问题多跟他请教,也请他多帮助我。第一次工作上的交道是因为“Y2K项目”。那时我们没有直接工作关系,集团要电脑公司指定公司级的“Y2K项目”负责人,刘军用手一指,就是技术发展处的李方吧。就这样,我被“糊里糊涂”地推上了“Y2K项目”的“搅肉机”里,好在那个项目完成得还不错,还得到了集团的嘉奖。
在那次谈话中,他给我讲了成立技术发展部的背景,指出这个部门的重要性。特别谈到这个部门的定位和工作方针:
——找准定位。这点特别重要,做好了也很难,可能要随时调整定位。
——要以积极的心态,高站位,代表杨元庆和刘军把握公司的技术方向。
——在管理风格上,他会采用充分授权式的管理,发挥我们的创造力和主动性。
——希望我们要有好的悟性,同时要有耐性和柔韧性。
——部门是公司的对外技术形象,要充分注意树立好这个形象。
——要十分注意与其他部门的配合,像研究院、质控部、各事业部研发部门等。
——部门的发展要采取渐进式,要少而精,逐步发展。
这些问题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体现这个部门的价值、如何找准定位、如何以主动积极的心态工作、如何要有悟性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为了更好地体现部门价值。部门对公司有价值,它才能生存下去,否则就会被撤掉。这些话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我后来的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还谈到了部门的宗旨、职责、组织架构、当前工作等问题。从2000年初那次谈话起,刘军就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后来在实际工作中,他果然采取的是放权管理,充分信任我们,给我们支持。在他的领导下,我感到很舒畅,后来回过头来看,那段时间是我在联想最出成绩的阶段。我很感谢这位联想少帅对我的支持。
第2章 要做高科技
联想想做高科技企业,至于如何去做,按什么标准去做,没有结论。此时的联想正是巅峰期,没有什么迹象可以表明马上会有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得出这个结论似乎也是合理的,也表明是有一定想法的。西丽湖会议还是很有意义的,至少说明联想的管理层开始严肃地思考一些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确实关系到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尽管会议没有得出十分明确的结果,讨论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是很够,但能够开始认识,就是一次巨大进步。
柳、倪的矛盾是源于企业的基本发展思路,柳传志认为企业首要考虑的问题是生存,一切都要为生存问题让路。在发展技术与企业生存产生矛盾时,技术肯定要给生存让路。倪光南认为企业要做大,特别是要做成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就一定要有自己的技术,也就是所谓核心技术。企业只要有一点生存能力时,就要开始注意投向技术,使企业不断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无论“贸工技”,还是“技工贸”,操作得当,都应该是中国IT企业走得通的发展道路。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两种道路原本没有什么优劣之分,也不应有哪条绝对正确,哪条绝对错误的说法。不然就不会出现一方面有联想、TCL为代表的“贸工技”典范,而另一方面,也有华为、中兴、大唐等一批技术起家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