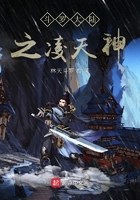夜风徐徐划来,轻拂过一裳窗前的风铃,带起了一片隐隐的清越之声。
一个黑影在风铃声中悄悄潜进一裳的房间,那个黑影什么都没有做,只是站在床前静静地看着睡去的一裳。更深露重,窗外的月始终隐在云层里,看不清黑影的样子,只有模糊的一片。
一裳睡得极不安稳,微蹙着眉在睡梦里挣扎。各种梦境交错在一起,犹如坠进了一个巨大的旋涡中,抓不住一颗可以救命的稻草。
“娘,我想学。”一个无人往来的废弃的园子中,一个大约七岁左右的小女孩儿站在树下可怜兮兮摇着美妇人的手,苦苦哀求着。
“不行!”美妇人一口回绝,不带任何商量的余地。
“娘,等我学会了之后就可以不用再受大姐二姐欺负了。”小女孩儿委屈地放下美妇人的手坐到地上,双手撑着小脸,低头喃喃道。
“总之,娘不准你学,你就不能学!”美妇人仍然态度强硬。
小女孩儿的眼泪一下子掉下来,她越来越不了解她的娘了,越长大就越能看到娘的身上藏有很多秘密,明明身怀武功却总要被那几个娘欺负,明明可以得到爹的恩宠却总要故意做一些错事令爹讨厌。
美妇人怜惜地看着眼前的女儿,不让她学武功是对她好,她害怕哪一天她的女儿也走上她的老路。
“小姑娘,你想学武功?”一个庸懒却饱含危险的声音响起。
美妇人和小女孩儿惊得同时转头望向来人,不远的树下不知何时站着一个黑衣人,全身上下都裹在紧身黑衣中,连脸都不例外,只余两只幽黑的瞳孔露在外面,闪烁着让人琢磨不透的光芒。
“你?你来干什么?”美妇人急将小女孩往身后藏。
黑衣人低低笑起来,似得意,似嘲讽,“呵呵,找了几年,终于找到,原来你已经嫁作她人妇,不过你似乎并没有完成任务就离开了。”
“我的事影主还没有过问,还轮不到你来问!”美妇人的态度强硬起来。
黑衣人轻轻弹掉落在自己身上的一片叶子,漫不经心地说:“如果我说就是影主让我来找你的,你会怎么样?”
美妇人的身体一震:“不会的,影主他明明已经放我走了!”
“七年前,你欺骗他的事,你真当以为你做得一点都不留蛛丝马迹?”黑衣人的声音转冷,阴沉地看着眼前的一对母女。
“以后你女儿武功的武功就由你来教,七年之后我来领她,如果你不用心教,知道她以后的处境会怎样吧?”说完黑衣人就像条蛇一样,扭了扭后一下子就不见了,只是空气中才残留他得意甚至有些不怀好意的低笑。
美妇人紧紧搂住怀中的女孩儿,单薄的身体还微抖着。女孩儿虽然有点害怕,心中却高兴着,终于,终于可以不用再受欺负了!
深夜,野外的墓地上磷火荧荧,透露着阴森与诡异,还有两点比磷火更幽绿的光闪动着,让人心底生凉。
“用力刺!”美妇人站在女孩身后,与女孩儿一同盯着面前的贪婪饥饿的黑狼,对女孩儿命令道。
女孩儿的身体发抖,拿着刀的手狠狠地打着颤,她不敢冲上前去刺它,更怕它冲过来扑倒自己。
“不要再犹豫,刺它的脖子!”美妇人狠声命令道,“今天你若不刺死它,它就会扑过来咬断你的脖子!”
“不!”女孩摇着头,双眼中盈满了恐惧。
但那头野狼却等不及了,它已经饿了好几天,看者眼前这个似乎有些退缩的人,它终于不再惧怕那刀,狠狠地扑过去。
“啊!”女孩闭上眼睛本能地奋力一划,温热的液体滑下来,女孩看着沾满狼血的右手放声大哭:“娘,我学武功不是为了杀野兽杀人,我只想自保!”
美妇人狠了狠心,没有上前抱住她,却在心里暗暗道:“只有让你学会狠心,只有让你经历过这翻折磨,你才能在以后的环境中才能生存下来,不然那个人吃人的地方,你如何自保!娘都是为了你好。”
空旷的石室中,幽火闪烁,光线沉暗,一个充满魔力的声音幽幽响起,“你们之间只能有一个人活着。”
“杀,杀掉她?”白衣女子呆住了,她慢慢转头向她身旁的女子看去。那女子与她一样,身着洁白纱衣,正值妙龄,有着美丽清秀的容貌,此时白皙的脸上有悲哀有恨意还有不服的傲气。
“杀掉她,你就可以取代她。”那个声音诱惑着,却不带半丝情感。
白衣女子转头,看着手中的匕首,身体微微颤抖着。
“开始吧。”黑衣人淡淡说着,仿佛即将发生在眼前的这场残杀,并不能牵动他多大的情绪。
白衣女子还在发愣,另一个女子却将匕首毫不留情地刺过来,直取她的胸口。白衣女子本能一躲,手中的匕首也下意识刺过去。看着眼前的二女终于展开残杀,坐在石室高椅上的人阴沉地笑开了,有如一朵带毒的花忽然绽放。
白衣女子不能想象眼前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子染上鲜血、失去生命会是什么样子?所以每当她要刺中她要害的时候,手腕总是不由自主地收回或转开。
但那个女子却不这么想,每一次都痛下杀招,她清楚的知道这场相互残杀的后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她当然不想做从此消失的那一个,于是手上的动作越来越狠辣,心底还暗暗嘲笑着白衣女子的善良,对她的手下留情丝毫不领情。
白衣女子吃力地对付着眼前的女子,她并不想做杀害同伴的那一个,可眼前的女子却步步紧逼,一点喘息的余地也不留给她。忽然她看见寒光一闪,转瞬脖颈处已觉一凉,七岁时那个像蛇一样的黑影,从此以后母亲严苛的训练与暗自垂泪,那头倒下自己刀下的黑狼,一一在脑海中迅速滑过,她闭上眼睛绝望地刺去,只觉得匕首好象插入一团软软的物体中,腥热的液体喷射出来,溅在她的身上、脸上、头发上。她慢慢整开双眼,眼前的女子缓缓倒下去,脸上还带着不可置信的惊讶以及不甘、愤恨……
“呵呵呵呵……”邪魅的声音再次响起,“从今以后你就是她了,现在你去把她腰上的令牌拿下来。”
白衣女子木讷着脸,慢慢蹲下去,伸出已毫无感觉的手去摸那令牌,却忽然看见那倒地的女子死不瞑目的双眼忽然眨了一下,然后冷冷地看向自己。
一裳全身一颤,猛地睁开眼,冷汗早已浸透了亵衣。就在她睁眼的那一瞬,忽然感觉好象有一个黑影迅速闪进黑暗,一裳看得一惊,是谁?
她不敢出声,也不敢起身点灯,仍静静躺在床上,却已感觉不到那个黑影的存在,是错觉?还是那黑硬已经离去?一裳忽然想起剑儿前些阵子险些遇害的事,心中一震,忙起身点灯去看隔壁的剑儿。
白天剑儿学得欲罢不能,一裳见他兴致这么高,不忍打断他,就留他在闭春馆住下。
荧荧灯光下,一裳见剑儿仍在安稳塌实的睡着,或许是心愿得偿,脸上还带着满足的笑。一裳爱怜地帮熟睡的剑儿理了理额前的头发,又小心地为他掖了掖被角,放心离去。
回到房中的一裳却再也睡不着,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再做过这些梦了,这段日子是怎么了?难道是因为再次被打伤,勾起了前尘往事吗?
“夫人,今天这么早就醒了啊!”端着水盆的蓝儿放轻脚步走进来,看到已在镜前梳头的一裳有些惊讶。
一裳放下手边的木梳,走到水盆前:“昨夜没睡好,今晨起得就早了。”
“咦?”绿浓拿着拧好的绢帕一边走进来一边嘀咕着:“今天好象少了点什么东西。”
蓝儿闻听此言歪起头咬着唇:“的确好象少了点什么。”
“可是少了什么呢?”绿浓在房中扫视一圈,发现陈设简单的房间依旧是原来的样子,并没有哪里改变。
一裳听见两个丫头的话并没有放在心上,她慢条斯理地洗着脸,想则一会儿亲自去叫剑儿起床。
“婶婶,早!”剑儿连跑带跳地走进来。
一裳见剑儿神清气爽地打着招呼不由笑道:“怎么不再多睡会?”
“先生说一天之计在于晨,早晨的时光读书最好。”剑儿一本正经地回答。
“小少爷真懂事!”绿浓和蓝儿忍不住在一旁赞道。
一裳拉过剑儿的手,笑着对他说:“好,婶婶就陪剑儿晨读。”
绿浓和蓝儿侍侯剑儿洗过脸,就领他来到已在院中摆好笔墨纸砚的一裳跟前。
“婶婶,你窗前的风铃怎么不见了?剑儿很喜欢听它的声音呢!”剑儿坐下后对一裳道。
“啊!对了!是风铃!”蓝儿忽然叫道。
“没错,今天早晨我就觉得少点东西,原来风铃的声音没有了。”绿浓也在旁边附和着。
一裳一愣,扭头去看窗前,果然,那串她从江南带过来的风铃已不见踪迹,窗前仅余一根细绳在晨风中空荡荡地摇摆着。
原来,昨夜并不是错觉,真的有人曾经潜入过她的房间,并拿走了那串风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