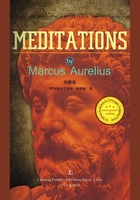平等问佛祖:“人人是平等的吗?”
佛祖:“众生平等,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
平等:“不是,虽然我知道你讲过众生平等,但我眼中看到的为什么不是众生平等呢?”
佛祖:“哦,你哪个眼睛看到了不平等,或者说有什么不平等?”
平等: “我觉得有的人生活得好,而有的人生活得不好,这难道平等吗?”
佛祖:“生活的不同,就让你觉得不平等了,那我问你,古代人生活的是不是更不平等?”
平等:“是的。”
佛祖:“那古代生活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平等:“都已经死了。”
佛祖:“那都死了,是不是说明他们现在都平等了。”
平等:“不一定,有的人还是比别人生活的好呀,那些当皇帝的人生活不是更好吗?”
佛祖:“好的,那些当皇帝的人生活得好的感觉还存在吗?”
平等:“不存在了,但他们当时感觉一定很好。”
佛祖:“哦,难道你不觉得那些已经死了的人的所有感觉都已经空了吗?也许他们当时的感觉就是幻觉吧,或者你怎么知道他们当时感觉好呢?”
平等:“有点儿道理,但为什么会这样?”
佛祖:“因为每个人都只是自然进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细胞,每个细胞的寿命都只有几十年而已。”
平等:“什么?为什么人是细胞,人明明是人,而且还是有感情的呀。”
佛祖: “你说得对呀,但你想想人产生之初是不是只是一个受精卵而已。”
平等:“是的,但我还是无法把一个活人理解为一个细胞。”
佛祖:“好,我再讲讲,如果我们把全人类看成是一个人,而且我们把这个人叫做自然人,每个单独的人看成是这个自然人身上的一个细胞,我把他们叫做细胞人,你能理解吗?”
平等:“可以,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佛祖:“我们看看人类的发展历史,一开始自然人出生,原始社会是自然人的幼年期,所谓的阶级社会是自然人的青年期,而未来的理想社会将是自然人的成熟期。”
平等:“行,这种解释有道理。”
佛祖:“自然人身上的每个细胞都会几十年更新换代一次,就表示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你觉得可以吗?”
平等:“我觉得行,但人人是细胞怎么能说明是平等的呢?”
佛祖:“对的,你总是认为人与人之间有区别,对吗?”
平等:“是的。”
佛祖:“一个人身上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细胞,他们分别要完成不同的工作,对吗?”
平等:“对的。”
佛祖:“自然人身上也有不同的细胞,我们可以把自然人身上的细胞分成五类,一类是脑细胞,一类是嘴细胞,一类是手细胞,一类是体细胞,一类是脚细胞,你觉得行吗?”
平等:“可以。” 佛祖:“脑细胞思考自然人的未来,是人类中的圣人;嘴细胞用来表达人类的理想,是人类中的天才;手细胞指挥人类的工作,是人类中的帝王将相;体细胞构建完整的社会,是人类中的社会精英;脚细胞推动自然人的前进,是人类中的人民。” 平等:“有趣,我觉得人类就是由这五种人组成的。”
佛祖:“那么,当你面对一个脑细胞、一个嘴细胞、一个手细胞、一个体细胞和一个脚细胞时,你难道会觉得它们不平等吗?”
平等:“不会,一定不会。” 佛祖:“每个在历史中生活过的人就是一个细胞人,他们完成了细胞人的使命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下一批细胞人又会继续他们的事业,一代又一代细胞人的努力,推动着自然人一步一步地前进。” 平等:“你说得有道理,每个人完成了他细胞人的使命后,就必须离开这个世界。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一定要离开。”
佛祖:“是的,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有快乐、痛苦和幸福,但当人死了后,这一切就都会变化虚幻。”
平等:“对的,所以,人人是平等的,不平等的只是人们心中的感觉。”
佛祖:“是的,现在的人们都感觉不平等。”
平等:“那为什么呢?”
佛祖:“那是因为自然人还没有成熟,所以自然人身上的每个细胞人当然也就没有成熟呀。”
平等:“哦,那自然人什么时候成熟呢?”
佛祖:“如果我们把一个人30岁看成是他的成熟年(三十而立),那么现在自然人已经活到29岁多了,到30岁只差几十天,表现在人类社会大约几十年吧。”
平等:“啊,你是说人类社会几十年后就会进入理想社会吗?”
佛祖:“也许吧,我也不知道。”
平等:“太谢谢你了,我平等为了等待这一天,已经用了几千年,我相信我一定会看到最终人人平等的世界。”
致谢与感悟
上海的早秋,闷热与干燥,在一间小小的居民房中,激情澎湃,热情洋溢,一群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正在激烈地讨论有关人类与人生的问题,是的,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共同研究和探讨人类发展历史、人类幸福、人生意义和人性哲学的各种看似很玄妙的问题,这群人就是“逍遥哲学”的主要研究成员。经过无数次的研究讨论,《不一样的逍遥游》问世了,献给可爱的中国青年们。
天痕,湖南人,这位清华才子可算是除我以外为本书操劳最多的人了,同时也是本书的总审核与策划人,他一人包揽了后期修改、封面与插图设计和推广策划工作,体现出令人惊叹的艺术与理性兼备的才华。他对内容的策划与审核尤其严谨与独到,记得在讨论本书最终的内容体验时,他尤其坚持的一点便是:内容的抽象逻辑性与思维启发性并重。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感官的美的体验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思想本身不能上升到抽象层次并形成逻辑性,恐怕对人的误导作用便更大于其启发意义了。”由此可见,其对智慧本质坚持的执着。当然了,他从来不是一个局限于一隅的人,本书的很多颇具趣味性与启发性的“亮点”便是在他与我的共同讨论与争论中产生的。
文君,讨论小组唯一的女生,上海人,对老子、佛陀和苏格拉底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提出重要问题,平时话不多,但一说起来就很难停下,尤其善于苏格拉底式提问与反诘,经常问得大家哑口无言而又无可奈何。
书超,河北小伙,讨论问题时一本正经,颇具儒雅之气。问题到了他那里,总能得到某种颇具内涵的理论性解释,有时看起来有些学究气,但同时,他的学究正好弥补我的不足,所谓真理愈辩愈明,不同的理论长短相较才能避免偏见。
会晓,河北人,人很聪明,有自己的想法,但平时不喜欢像其他人一样侃侃而谈,总是把问题放在心里“嚼”上一遍又一遍,但是当他真正把想法说出来时,总会对周围人的感官产生不一般的震撼作用,真是那句古话“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完美诠释。
石页,北京人,说话大大咧咧,是一位典型的实践型人才,与我争论最多的命题便是:“到底是理论为了实践,还是实践是为了理论?”有一次,我干脆回答道:“如果想要在短时间内解决当下问题,当然是理论为了实践,但是如果是为了整个社会与文明的智慧创造与提升,那就是实践为了理论了。”他听罢,沉思良久,转身跑出,回复道:“为理论补充实践素材去。”于是我笑了笑,便在“亚国人的古代史”这一节中加进了一些民族的“青年性格”。
恒宇,云南少数民族人,但是他的想法可并不“少数”,相反,他总是在与其他人的热烈争论中蹦出一个又一个与众不同的“创意”,同时,这些创意的表达又总是以出乎我们意料的“幽默”方式呈现,他就像一个思维润滑剂,使得我们的讨论活动像极了古希腊的戏剧。
我一直有一个信念:世界与人类的本质——一切都无“分别心”。人类、国家、社会与个人应该是一个不断求同的过程,并最终走向大同的境地。《不一样的逍遥游》的写作过程是一个充满挑战、兴奋与苦闷的经历,但与此同时,在想象人类未来大同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就像在构建一个全新的富有人性、充满无限可能的世界,这其中所有人似乎都能够获得一种快乐的感觉,一种源于灵魂深处的、对于人类本质理解的快乐的感觉。
我一直认为自己很幸运,每次人生到了最困难的时刻,总会有贵人出现帮助我渡过难关,有时,我在想:这到底是一种人生的偶然,还是在其中蕴藏着某种历史的、人性的、文明的必然因子?但无论如何,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时代对人们的要求早已经不是曾经的静态与简单的“记忆力”知识了,如果说在过去几千年不懂得识字读书便算作无法在社会立足的“文盲”的话,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工业、信息革命后的当今时代,如果不懂得真正符合智慧理性、逻辑性乃至创造性思维的人便可算作新时代的“智盲”了,这对于我们当代中国青年尤其如此。是的,在东方,在中国,我们早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一个前无古人的思维与精神博弈与创造的大时代,这个大时代里的每个人都将无可避免地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这样的博弈与创造的过程。
时代的兴衰反复,正如人性的善恶正邪:兴,人类精神;衰,人类精神。真心希望所有有志青年都能把握这样的人类精神与思维规律,从而培养出足够的思维能力,以在如今的时代大潮中中流击水,搏得璀璨人生。
最后,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关心生命本质与人类未来的读者朋友们。
逍遥游
2008年秋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