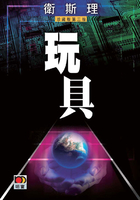紫页长长地出了口气,暗中羡慕她经历过那么多事仍能保持当初的热情。紫页觉得自己的热情差不多已经快被耗尽了。胡亚洲的出现给她带来了许多,同时也带走了许多。他们在一起的一年时间比紫页从前所经历过的所有事情加起来还要多,那个热闹的晚上他们的视线越过重重障碍七拐八弯终于连在一起,想来真不容易。他们是根本不相干的两拨人在同一间酒吧里欢度平安夜,蜡烛,闪烁的小灯泡,晃动的人影把夜晚的酒吧搞得很有气氛,两拨人开始交叉相遇,认识的、不认识的开始胡乱搭腔,男男女女,红红绿绿,有人喝酒,有人唱歌,说着抹了蜜似的情话,其实彼此还是陌生的。
紫页从第一眼看见胡亚洲,就知道他们之间一定会有什么事发生,这是女人的直觉,每个女人都有。胡亚洲站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朝这边看,紫页站起来去取酒的时候注意到站在角落里那人,他们笑了一下,彼此感觉似乎很熟悉。当然他们是陌生人,但他们很快就熟悉了,他们混在许多狂欢的人中间,静静地看着对方,没有人注意到他俩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当他们的朋友再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到紫页家了。
从那天起每个在一起的夜晚都被他们称作“平安夜”,在度过了无数个“平安夜”之后,紫页仍是一个人,还有柜子里那些闪闪发光的玻璃器皿,陪她度过无数个空荡荡的夜晚。
五
一个人的晚上,紫页常常拔掉电话,关掉音响,让自己掉进寂静的深处。如果不把电话线拔掉,她会忍不住拨那一串号码,那串号码就写在墙上,还有他的名字,都写得很大,像一只只眼睛似的盯着她。墙上的眼睛,静止的、不会发出响声来的电话,书,画册,蓝色胶皮手套,这些东西静物一般地陈列在桌上,紫页在晚上很少开电视,电视占去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太多空间,紫页不想让那些乱七八糟的电视节目把自己的脑袋塞得满满的。
玻璃柜子的顶部亮着几盏星星样的小灯,有时候房子里什么也不开,就开那几盏星星点点若有若无的灯。有一回,胡亚洲走进来,一点声音也没有,只有一条人影从紫页脸上掠过,然后无数热辣辣的嘴唇覆盖了紫页的全身,它们仿佛从屋顶上掉下来的,那么突然,一点预感也没有。他的吻把紫页吻得全身酥软,沙发发出咯吱的响动,他来了又走,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紫页不知道亚洲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变成一个影子的。
门厅里有一盏金属风铃,有人进来的时候偶尔它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有时穿堂风吹动它,它也会响。
在那种叮叮当当的声音里,紫页等待一个人的来临。她对自己说他不会来的,可实际上她还是很盼着他能来。那些空寂的、在等待中白白流走的夜晚,紫页感觉自己身上的水分正在一点点蒸发,她逐渐变得像一枚红枣那样干瘪。她看见自己像木乃伊一样的影子在房间里行走,有时撞在玻璃上,会发出“当”的一声响,柜子里的那些玻璃器皿振动着、相互碰撞着,发出嗡嗡的响声。
他的手在黑暗中缓慢移动,先是有些凉的,渐渐的就变得灼热和焦急,拦也拦不住似的往前赶。
他的手好像突然从黑夜里冒出来的,刚才还不存在呢,现在就有了,他的手像一个脱离身体的独立存在,在黑暗里沉浮漫游,贴着她身体的曲线走走停停,在一个细节的地方滞留许久,像一个贪图风景的旅人,在风景好的地方总要停下脚步多逗留一段时间,贪恋着,徘徊着,她身体里的液体随之喷涌而出,使得抚摸变成一种柔软的滑动。
紫页的身体轻飘飘地脱离床面浮在半空中,他的抚摸如水一般包裹着她的全身,潮水一次次地漫过她的身体把她掩埋在下面,这时候,她的全身都已被启动,像一列开足马力的列车,朝着前方不管不顾地开过去。然而,当她睁开眼才发现,那只黑暗中的男人的手是不存在的。墙壁上那些眼睛在黑夜里醒着,一只比一只显得空洞。
门厅里的风铃叮叮当当响了几声,夜又静下来了,什么也没有,脚步声,呼吸声,男人在耳边喃喃催促的声音,全都不见了。
六
办公室里来了一群民工,他们穿着厚重而肮脏的工作服,穿着很脏的靴子在干净的地板上走来走去。紫页问同事小群,这群人是从哪里来的。小群扶了扶细细的金属边近视镜,慢条斯理地说:
“听说是上面派来修隔断的,要把大办公室隔成许多小间,这样便于提高工作效率。”
小群是公司里新来的一位物理学博士,上司对他的工作能力表示怀疑,所以没派给他什么重要的活儿。小群满脸怀才不遇,见了上司又不敢说什么,紫页断定他是那种一辈子都窝窝囊囊的男人,平时很少理他。
紫页坐在办公桌前,看那些穿靴子的男人在她四周来来回回地走,他们手里拿着各类工具,电钻,射钉枪,铁锯还有玻璃刀,这些面目不清头戴黄色安全帽的人在写字楼内部施工,工作人员还要照常办公,各忙各的,各不相干,不管怎么说看起来有点怪。
坐在办公桌前看着别人把自己一砖一瓦地砌在中间,紫页感到四周正在逐渐堆起一座玻璃坟,她就是这座玻璃坟的中心。过了一段时间,她渐渐地也就习惯了,该干嘛干嘛,不知不觉一天已经过去了。
“下班了,你怎么还不走?”
小群的声音从办公室的某个角落里突然冒出来。
紫页坐在椅子上没动,说:
“我不知道怎么走出来,他们没有给我留门。”
小群在玻璃墙外面焦急地张望着,用清瘦的骨节突出的手指在新装的玻璃上留下巨大的手印。
小群的探索使紫页感到绝望,他像戏剧里的卡通人那样机械而又徒劳地运动着,紫页觉得自己仿佛坐在玻璃墙内观看一种独特的舞蹈,表演者动作迟缓而又怪异,他的手时而抬得很高,高过头顶,脖子向前伸着,金丝眼镜滑到了鼻子尖上,还差那么一点点就要滑下去了;时而又将身体蜷缩成一张弓样,在玻璃墙的底部抠抠唆唆,试图找到裂缝。
紫页四周的玻璃墙砌得严丝合缝,物理学博士皱着眉头上下求索了很久,终于得出结论,他说紫页,你只好在里面呆一晚了。
可以给外面打电话……
可是打给谁呢?
就这么着吧,反正我不走,今天晚上我陪着你。
紫页耳边连续传来嗡嗡的声音。
他俩一个玻璃墙里、一个玻璃墙外,足足守了一夜,当紫页哈欠连天地从睡梦中醒来,听到有穿厚重皮靴的人踢踏踢踏朝这边走来。
小群从睡梦中霍地跳起来,就像一个可逮着理的凶汉,斗鸡似的冲那民工吼道:
“怎么搞的?啊……你们……”
小群在玻璃外面焦急地守了一夜,为的就是能找个人出出这口恶气。
玻璃里面的女人冷眼旁观,心里说这下可有好戏看了。那个穿靴子的民工就像变魔术似的手指轻轻一抠,玻璃墙便自动裂开一条缝,“这里有门,只是你们没看出来。”他眼皮都不抬一下,说完就走了。
七
那个夜晚拉近了紫页与小群之间的距离,紫页觉得小群这个人虽然能力差些但心眼不坏。有时候他们一起到公司一楼的餐厅去吃午饭,碰到熟人还开开他俩的玩笑,紫页虽然心里不大舒服,但并不表露出来,勉强一笑。小群看见紫页随和的表情,以为她是在默许什么,就跟在紫页后面,整天问她要不要吃这个,要不要吃那个,紫页不说要,也不说不要。
紫页每天下班总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她坐在小公共汽车上长长地松了口气,心想上帝保佑总算从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里逃出来了。小公共总是堵在长长的三环路上,移动的速度有时比步行还慢,就这样,紫页还是觉得比呆在公司里舒服,没人透过玻璃墙深情地凝望着她(这种凝望想想都让人后脑勺发凉),她可以自由自在想干嘛干嘛。
车窗外有一种过新年的气氛,街面上到处亮着灯,饭店前还布置了无数星星点点的小串灯,岁末所特有的热闹与慌乱就藏在那些无处不在的小串灯里。小饭馆里开着白亮的灯,玻璃擦得光净得就跟没有似的,里面的桌椅一目了然,寂寞也是一目了然。负责开门的女孩无精打采地垂着头,不知是玩手里的一个什么小玩艺儿,还是原本什么也没有她只是在玩她的手指。
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聚了一些人,不知是灯光的关系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那些人依次站在台阶上,高高低低排列有序,却像纸片人似的木然不动。广告牌上有一些真正的纸人,他们的样子被技术不过关的画工画走了形,看上去就像一些天外来客。
小公共车仍以很慢的速度一步一步往前爬,紫页不明白今天晚上为什么车堵得这么厉害,好像全北京的车都开出来了,毫不客气地堆在三环路上,马路变成了停车场,车头顶着车尾,一辆紧挨着一辆,毫无指望,仿佛这辈子就这么耗下去了。坐在车里又冷又难受,而小公共里很暗,在明亮的城市中停泊着,就像把华丽的城市布景用剪刀剪了一个黑洞,而此时此刻紫页就呆在黑洞里,望着车窗外的明亮与繁华,无端地有些伤心,她想过了年又能怎么样,日子还不是得照样过下去,没完没了地等待,没完没了地担心,什么也留不下,时间过去了,手心是空的,青春却一天天地被耗尽了。
回到家浑身上下都被冻透了,连骨头缝里都听到咔嚓咔嚓的响声。紫页一进门就开始脱衣服,她太想有一只热的手贴在她皮肤上,后背或者臀部,那只手滚烫滚烫的,隔好远就能感觉到它的热量,然后,它就靠近了好像刚从冰箱拿出来被冷冻过的皮肤,当这一冷一热相互接近的时候,紫页听到吱吱的响声,然后她看到皮肤上冒起了白烟,吱……如同着火了一般。
乳白色的雾气弥漫了整个空间,镜子的轮廓隐遁在水雾中,变成了雾蒙蒙的一堆墙。紫页知道墙后面藏着他的身体,他此刻正在某个地方注视着她。
洗完澡从卫生间里出来,紫页整个人好像从蒸锅里拣出来的热馒头,胳膊是热胳膊,腿是热腿。脸上红扑扑地放着光,收音机传来好听的音乐。紫页擦干身体钻进被窝,闭上眼睛什么也不想。
身上的毛孔渐渐冷却下来,脑子开始活起来,紫页克制住自己不给胡亚洲打电话,她对自己说这个时间给他打电话是很不合适的,但另一个声音又对自己说有什么不合适的,他只享受相爱的好处,却一点也不愿为它承担责任,他成天跟个没事儿人似的,该干嘛干嘛,两头讨好,心安理得,他倒活得挺滋润的,他都不知道人家度日如年这日子是怎么过的。紫页胡思乱想了一阵才想起晚上还没有吃饭,她从冰箱里找出一只不知哪天买的面包来胡乱啃着,再一看面包的牌子竟然叫做“爱巢”,紫页心里渗出一丝血来。
她手里拿着电话胡乱地拨着号。小群的声音从电话里冒出来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真正想找的不是他。
小群一下子就听出紫页的声音,“是你吗?是你吗?”小群的声音激动得有些分岔,好像音色被特殊处理过,用刀子把每一个字、每一句话劈开来,变成两重分岔的重音,“我一直在等你电话,我现在过来好吗?”
紫页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的,她想着一个男人,却给另外一个男人打了电话,身体和头脑都好像不是自己的了,她一直躺在被子里没动,身体是冰冷而又赤裸的,眼睛肿胀着,忍不住直想哭。
小群的影子从紫页苍白的脸上疾速掠过,他带着外面的凉气在床边坐下来,他的身体把床头灯的光线遮去大半,房间里就像蛰伏着一只巨大的怪兽,他每动一下,怪兽就跟着移动,影子是巨大而又夸张的。
紫页半闭着眼睛,感觉到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丝丝凉气,这丝丝凉气与巨大的黑影仿佛不属于同一个人,影子是影子,凉气是凉气。
八
紫页到处打电话寻找胡亚洲的下落,可是无论怎么呼他也不回电话,手机二十四小时关着,单位和家里的电话都没人接,那令人恐怖的长音在城市的上空一遍又一遍地回响着,都快把她逼疯了。
蓝格出现在紫页的住处,使紫页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蓝格身上涂满了奇怪的符号,细看才知道她穿了件写满字母的衣服。她画了一种奇特的彩妆(据说是最时髦的),眼影拉得很长,向两边大胆地挑着,看上去有几分前卫几分凶悍。
“你跟那个外地男友怎么样了?”紫页问。
蓝格眨了眨藏在浓妆深处的眼睛,问:“什么外地男友?”
“你上次来不是说……”
“噢,他呀,”蓝格又眨了眨眼想起什么似的说道,“那件事早就过去了。”
蓝格坐在椅子上说着神经兮兮的话,她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有一些陌生的、紫页从未听过的名字在她嘴里滚来滚去。她涂了黑色唇膏的嘴唇忽大忽小快速开合,紫页越来越弄不清她到底在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