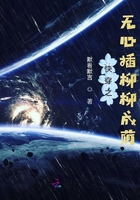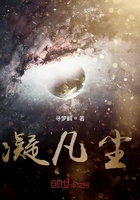夜幕下,我和兰在寂静的死城中步行了好几个小时。这几小时里,我们走过白渡桥,看到干涸的河床里满是白骨,活像个万人坑;我们路过高耸入云、曾经极度奢华的顶级酒店,看到满地碎骨,想象着这些人从几十层楼的高处自由落体的惨状;我们还看到一辆锈迹斑斑的兰博基尼,车门掀起,司机的尸骨横倒伏地。
死亡面前,人无高低贵贱之分,人人平等。
兰看到我东张西望,笑着问:“你应该是第一次来死亡世界吧?好像并不恐惧。”
我呵呵笑笑,不答话。我当然不恐惧,我已经死过一次了。对我来说,世上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事了。当然,这是我当时的感触。事实上,当时我确实已经颇为洒脱,但我并不知道,其实,世界上有很多比死更可怕的事。每当我遇到那种事,我宁可独自挑战一头骨龙。
有朋友可能会腹诽:“骨龙算什么。人家英雄一个人都可以杀一大群的。”
我呸!你杀个骨龙给我看看?告诉你,跟骨龙搏斗的最大问题不在力量的压制,而在于——它本来就是死的,你怎么杀它?
也许又有朋友举手发言:“骷髅不也是死的吗?不是一样可以消灭吗?”
错!绝大多数骷髅,还有绝大多数僵尸,都是灵魂少得可怜的傀儡。一旦肢体被毁,就无法恢复。而骨龙生前是强大的龙族,即便进入死亡世界,依然有着强大的灵魂力量。其智慧堪比吸血鬼。而其体魄,则要超出吸血鬼无数倍。至少它们不畏惧阳光,并且,它们没有心脏。
下面,最后一位朋友发言:“你丫唠唠叨叨跟我们说骨龙做什么?”
好吧,我想说的是,在我和兰走了不下十公里之后,不巧被一头骨龙发现了。
当时,我正和兰横穿一条车辆成堆的公路。她轻盈地在一辆辆破车之间穿行、翻越,而我却显得笨拙得多,不时碰出点声响来。
我问她为什么不变成鸟直接飞过去。她说一定要带上我。因为带上我,就能得到叛逆天使的庇护。我听得直翻白眼。刚才我差点被那个亡灵巫妖弄死,也没见什么天使降临嘛。
当我爬上一辆破败不堪的城市越野车时,脚下一滑,重重摔趴在引擎盖上。蓬的一声巨响引来了不远处一声震撼心灵的龙吟。
很快,两个红色光点浮现在一片漆黑之中。我努力瞪大眼睛,想看个究竟,却被兰拉着手在汽车的废墟中连滚带爬,一路狂奔。
说来奇怪,一般来说,人应该是越跑越热,我却越跑越冷。这时我才发现,我们已经被寒冷的冻气包围。而那两个红点——不用说,一定是骨龙的眼睛——已经从我们的后面挪到了我们的头顶。黑暗的空中,仿佛有把大蒲扇在呼哧呼哧往地面扇着阵阵寒风。空中呜的一声长啸在夜空中回荡不止。
兰突然急停,躲到了我身后。
虽然我被两个软软的凸起顶得鼻血横溢,但依然正义地问道:“你干什么呐?……哇!”
一团密集的霜冻扑面而来,浇得我一身冰凉,腥味冲得我差点呕吐。那感觉,就像在十二月天被人当头浇了一头冰凉的、泡过香港脚的洗脚水。
我怒道:“为什么把我挡在前面?!”
兰弱弱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因为你魔免。”
靠!我也知道我魔免,但是我很冷啊。我说:“但是我会感冒。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兰一声不吭,转身就跑。
刚一转身,又是一道寒冰气息落下,将我们包围在一片寒冰晶体的尘埃之中。我这才发现,兰对魔法的提抗力并不差。难怪她能在巫妖的霜冻攻击下丝毫不伤元气。
我跟着兰冒着骨龙的冰冻吐息跑了一段,觉得这样逃跑实在有些盲目。她似乎对骨龙有着本能的恐惧。
于是,我拉住她的手说:“跟我来。”
兰的力气肯定要比我大一些,但此时,她十分顺从地跟着我奔向一栋几十层高的大楼。看来她真的没了主意。
为了不贬损我们当家美女主角的智商,请容许我稍作解释。我们并不能因为兰对骨龙的盲目恐惧而看轻了她。事实上,她在面对半神级的大魔头时,也是毫无惧色的。她惧怕骨龙,只是因为她的德鲁伊身份。龙,在德鲁伊的文化中,绝对是一种压倒一切的强大存在,其地位堪比至高神的神使。因此,对兰来说,无论哪一种龙,即便是骨龙,也是令她敬畏的。
我就没那么多顾忌了。对我来说,正在攻击我们的骨龙,无非是只比较凶残的鸟类而已——没错,鸟类。撇开其惊人的力量,它的地位甚至还不及那些频频找我麻烦的东瀛同僚。因为对同僚动手,我多少还有些顾忌,对骨龙这样的不死生物,我绝对可以不择手段。
我真的不择手段了。
我们躲进高楼的底层。骨龙的吐息喷不到我们,便降落到地上,把汽车般大的脑袋探进楼里东张西望,四足发力死命往楼里钻。整个楼层弥漫着刺骨的霜冻之气。
我把兰拖进角落,对她说:“我有个办法,可以搞掉那个大家伙。你只需如此如此,然后我如此如此,你再如此如此……”
说了半天,她没一点反应,骨龙的拆屋工作却进展顺利,用不了多久就能把楼弄塌了。
我借着那柄藤蔓法杖上微弱的紫色光芒,发现兰双目无神,表情痴呆,看来是吓坏了,再一摸她的脸颊,冰凉,爽滑。惭愧,我的手开小差了。
我抓着她的肩膀一通猛摇,摇得地动山摇,碎石砖块纷纷落下。不是我,是骨龙干的。再这样下去,我们只有活埋的份。
摇不醒她,我就拍她的脸,越拍越重,眼看就要演变成抽大耳帖子了。下不去手啦!
我猛掐她细细的腰,好有弹性,但是她没反应;我轻抚她的长腿,我袭胸,这个……都太下流了,我不干。抓耳搔腮一番后,我给了她一个热情似火的法式舌吻。
说实话,我并没有任何不良的念头——好吧,或许有,但绝对不是有意为之。我只是急于将兰从惊恐中唤醒。而吻,应该有让人兴奋的作用。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