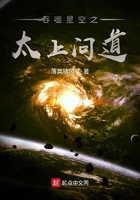今天,她毕业了。
这场特殊的毕业典礼就在养怡院的过道里举行,这里比床边宽敞些,可以容下刘佳芬和十二个老师。她们围着她,为她唱歌,她们的歌声完全改变了敬老院沉寂的氛围。楼下能自主走路的老人正抬头往上看,三楼的几个老人摇着轮椅过来听她们的歌声。他们枯若朽木的身体就坐在不远处,成了毕业典礼的最佳观众。咧着嘴的,用深陷的眼睛盯着他们的,皮包骨头的脸上泛出皱纸一样的微笑。她们的歌声抚摸着敬老院的每一个角落,让每一个死气沉沉的身体都有了短暂的活力。
此刻的吴悦像一颗夹心巧克力糖,被老师们层层包围。九年前的冬天,刘佳芬带着四个老师找到了她。九年中,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没有放弃过。现在,她和十二个年轻人的声音合成一曲《新年好》,新年踩着歌曲的节奏降落于吴悦的耳际,能让她感到温暖吗?来到养怡院七年,甚至连过年时,女孩儿也没有回过家,但阿姨会把轮椅推到楼下的院子里,让她一边就着阳光嗑瓜子,一边听远处与她无关的声声爆竹。每年过年前,老师们都会给她唱《新年好》,她总是拍着手跟着她们唱。这是她唯一会唱的歌,今天,就让这曲《新年好》变成她的毕业歌吧。
这是这家养怡院自建成后举行的第一次毕业典礼,刘佳芬希望这也是最后一次。总有一天,像吴悦那样的孩子都能走进学校,和她的同伴们一起成长。
当老师们齐声向她喊“Yeah”时,她也跟着他们伸出了表示欢呼的剪刀手。
乔雪月说:“今天,你毕业了,以后我们不像现在一样经常来了。”
刘佳芬把毕业证书送到她的手里,说:“祝贺吴悦,和其他小朋友一样从达敏学校毕业了。”
像在运动会得到奖牌时一样,她先是笑,然后又一次哭了,说:“老师,好人!”
这是她能表达的最长句子。
她是个爱流泪的孩子。乔雪月说:“她其实心里什么都懂,感情细腻得像个正常孩子。”
老人们跟着老师们在拍手:“吴悦毕业了!”
“几年前,我看着这些老师们来的,一转眼的工夫,这孩子就毕业了。”这是16床老大爷的声音。他是养怡院的老住户。
学校的送教队伍,从最初的四个,变成了十二个。送教的对象也有了变化。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脑瘫孩子,一个三岁的自闭症孩子,一个外来打工者的脑瘫孩子,一些海曙工疗站的智障成人……刘佳芬和十二个老师寻找着每一个不能来学校的孩子和需要教育支持的智障成人。她要把特殊教育传播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贯穿到智障人的一生。
这是一个将被不断延续的行为。音乐老师陈怡每周的两个中午属于一个三岁的高功能自闭症女孩。家长一星期两次把孩子带到学校来。她来自于刘佳芬和宁波志愿者一起成立的星宝俱乐部。只要听一遍别人弹奏的钢琴曲,小女孩就能把它们弹出来,她对音乐有着超常的领悟力和记忆力,却像低功能自闭症孩子一样,不知道你、我、他的称谓究竟有什么不同,不了解社会规范,不知道如何与人沟通。发挥她在钢琴方面的造诣,或许能让她在掌声和被注视的氛围中获得与人交往的快乐,也能让她在未来有可能以此谋生。
每个星期,姚望的两个中午属于另一个六岁的低功能自闭症孩子。快一学期了,男孩从来不说话,只有姚望在不停地问他,等待着有一天他会有语言回应。“我们画画,好不好?”“好吧,不画。”“这是积木。”“你要直的,直的,还是直的。”“我们找个弯角的管道积木,好不好?”“好吧,不要,还是直的。”“直的没有了,我们要块弯的吧。好吧,重新拆开。”姚望把参与孩子的游戏当作是沟通的途径,当成她和他之间的专属语言,她的课程必须以爱、接纳和尊重为基础。姚望说:“这并不是我的独角戏,他总有一天会说话的。”
张鑫每周的一个上午属于工疗站的十多个智障成人,年纪最大的五十八岁,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每天早上送她来,晚上接她回去;年纪最小的是十八岁的柳莹。有时候,李华会和她一起去看柳莹。张鑫去看她时,不像以往那样挨打了,每次她去,女孩儿都张开双臂,这是拥抱的姿势,只有她最信任的人才能享受这样的殊荣……
刘佳芬把轮椅推回到床边。泪痕还留在吴悦的脸上,她突然用一只手摆出书写的姿势,说“笔”。
“吴悦是不是想写字?”
她笑了笑,顺从地点点头。
刘佳芬递给她一支笔,她就在父母带来的超市免费购物资料上写啊写。
在最后一次“课堂”上,刘佳芬想多陪她一会儿,十三个人把过道也挤满了。
吴悦握着笔,写一个数字,就抬起头,看看校长和老师,然后再低头,写第二个数字。她是在向她们展示她写的字。
“她喜欢写字。活动手指给她带来了满足。”乔雪月说。
吴悦专注书写的样子与蒙台梭利一百年前见到的场景有了奇妙的呼应。刚刚从学校毕业的蒙台梭利在儿童住院部偶然发现一些精神病患儿,他们被禁锢在一间屋子里,在地面上乱抓乱扒,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她问管理人员:“这些孩子是否吃过饭?”“刚吃过饭,而且他们都吃得很饱。”孩子们的行为引起她的注意,经过持续不断地观察、思考和研究,她得到了一个崭新的结论——“关着这些儿童的那间屋子里,四壁空空,没有任何可供孩子抓、握、摆弄等操作的东西,所以这些孩子只能在空地上乱扒乱抓来活动他们的手指,以满足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的需要。”这件事让蒙台梭利获得了灵感,她深信,有时候,智力缺陷和患精神病的儿童,对灵魂的需要超过食物的渴求。而通过运动和感觉训练的活动,可以使他们的身体动作协调,促进智力发展。
儿童智能低下主要是教育问题,而非医学问题,教育训练比医疗更为有效。这也是刘佳芬要让教育走出校门,跟随吴悦九年的原因。
在学校里,有很多脑瘫孩子。有一个孩子不会说话,不会吃饭,不会自己上厕所,只会跌跌撞撞地走路。他的家境不错,因为没有任何自理能力,一个保姆跟读在身旁。与吴悦不同,父母从婴儿期就开始对他进行感觉统合训练,早期恢复得较好。及早进行专业治疗,脑瘫儿童的运动障碍会得到减轻。
“他家本来在单位旁边有一套房子,但是怕被单位同事撞见——有这样的孩子觉得不光彩啊,他们就在海曙买了一套六十多平方米的小房子。两间卧室,一间我和孩子住,另一间他们夫妻俩住,孩子不仅脑瘫,半夜还常常要发癫痫。他父母为了在他发癫痫时能及时地跑过来,晚上我们两个房间的门从来不关。”保姆顿了一下,把声音放低了说,“从我到他们家开始,八年了,我猜他们夫妻俩就没有——性生活了。门开着,谁还愿意做那事呢!他爸要把他扔了,他妈就是不肯!女人的心啊,总比男人软。”
绝望的脑瘫家庭的消息总是不绝于耳,到了刘佳芬心里,每条消息都让她过目难忘。全国约有三百万到四百万脑瘫儿童,每年新发病约有六万例。几百万个脑瘫儿童家庭都过得极度艰难,有些家庭陷入贫困,有些母亲变得疯狂,更有甚者则选择自杀。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余生就像见不到希望的无期徒刑。乔雪月说起过报上那个可怜的母亲韩群凤,因杀死双胞胎脑瘫孩子被判处五年徒刑。她曾经说过:“全世界都可以看轻我的儿子,可我还是坚信,总有一天,我可以让我的儿子走路出现在大家面前。”但儿子最终没有站起来,她不像吴悦的母亲很快接受了绝望的事实,一个长期心怀希望的母亲,比一个一开始就心灰意冷的母亲摔得更重,韩群凤最终选择溺死孩子,然后自杀……“江苏农妇捂死二十岁脑瘫女”、“深圳母亲抱两岁脑瘫儿跳湖”、“夫妻杀死脑瘫儿后相约双双自杀”,这样的新闻标题每次扑入她的视野,都像一把带血的刀子,横陈于她的眼前,成为她的隐痛。
谁能知道在几百万脑瘫家庭中,会不会出现另一个韩群凤?刘佳芬可以想象,一个家庭的压力和绝望怎样在慢慢吞噬着父母的心,让他们对人间的诸多美好失去了激情。生活成为牢笼,一场没有尽头的苦役,几乎让所有的脑瘫儿母亲都或多或少地面临着精神危机、家庭危机。有的家庭关系极度紧张,有的离婚,有的出走,有的患上精神病。
在孩子与家长之间,刘佳芬的特殊教育队伍应该像一道奔跑的阳光,苦难在哪里,她们就把微弱的光打到哪里。
当吴悦的父母发现她终生无法站立又无力雇人伺候时,选择了部分放弃,让她在一家养老院里与一些陌生的老人一起终老。
约四分之一的脑瘫儿童经过及时治疗和干预,智力可以保持正常。刘佳芬想,在情感上那么细腻的吴悦,如果出生于一个富庶家庭,或许能很早获得干预,或许她现在就能站起来了,或许她就能穿着她梦想中的裙子和高跟鞋,走在如今几乎永远不可能属于她的大街上。但幸好,她现在能用简单的普通话和护工李阿姨作基本的交流,能看一点书,填充白天的时光,能在老师们反复训练后,用右脚使上一点力气,帮自己从轮椅里慢慢地转移到床上。
刘佳芬相信,这些细微的进步,对于一个生命的成长,是有意义的。让她难过的是,她最终没有站起来。她们发现她时,还是太迟了。所以,现在她开始寻找智障幼儿,让特殊教育更早地介入孩子们的生活。
刘佳芬记得当初寻找她,是因为在一次开会时,听区教育局说还有几个适龄的智障儿童没有入学。
她立马决定去寻找。在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杂居的城中村吴家湾,她和老师们绕了无数的圈子,一家一家问,才找到了铁门紧闭的吴悦家。
当她在那个破落的旧房子里看到半身残疾的吴悦时,她的决定很快就下了——“把吴悦的名册挂在学校,把学校的教育送到学生家里。”
家里一张掉了红漆的圆桌,几个人一起趴在桌上,嘎吱嘎吱响。她们就在这张旧桌子上开始上课。她越来越重,祖母搬不动她,于是便连轮椅也舍去了。除了上厕所,她的二十四个小时就在这张床上度过。这张床,成了她的餐桌、课桌、睡榻和草坪,没有了轮椅的帮助,她甚至连院子里的太阳都见不到了。睡在床上,天花板就是她眺望的天空。上课时,她用双手托着自己的身体从床头移到床尾,乔雪月她们四个就和她一起坐在床尾,教她认识自己的眼睛、鼻子、嘴巴,帮她用语言重新拼出一个完整的自己,手把手教她涂色、写字,用水果来做算术。上完课,她双手托着自己的身体,慢慢移回到床头。
“她在家里老是捧着学校的书,看了一遍又一遍。总是用手摸书上的字和人。”祖母说。
刘佳芬没有想到,这其实是吴悦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父母还在身旁,天伦之乐还是完整的。那时的小吴悦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正在悄然变化,她无法预料接下去的日子将在养怡院与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们共度余生,他们像幽灵一样躺在床上,等待着死亡把他们一个个带走,而吴悦就像一轮早晨的太阳落入黑夜的泥淖之中,脱身不得。
因为刘佳芬的一个决定,在悠然养怡院出现了一群特殊的年轻人。
刘佳芬有空时也跟着老师们一起去。那个房间永远是不断变换面孔的老人和不变的小吴悦。
“雪月,这么多年,你们坚持下来,我来这里一次,就对你们的敬意增加一分。”在回去的路上,刘佳芬说。
“我常常想,如果命运让我变成小吴悦,我该怎么办?我需要什么帮助?”乔雪月说,“这样一想,冬天刮风下雪时,骑着电瓶车来看吴悦,就没有打退堂鼓的想法了。一年前,吴悦妈妈给我们写了封信,让我们一周送教两次。我们就把四个人分成两组,每次两个人去。父母有要求,说明没有完全放弃。”
“你看她和我们告别时,又流泪了。当孩子们因为我们流泪时,我们所做的,一定要配得上她们的泪水。”刘佳芬说。
三个月前,当她接过“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奖状时,也是这样说:“我的工作获得了政府的认同,我得了这个荣誉,不渴望为自己添光彩,而是希望通过我,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智障孩子。”
“我们这么做,其实也受了您的影响。我们不站在您身后跟着跑,怎么行呢?”乔雪月说。
“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跑,跑不了的,也给我们喊喊加油。我相信,随着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在不久的将来,政府对渐老的残疾人和行动不便的智障人士的帮助会从提供经济补助转为建立一个制度,比如由收养机构、银行、第三方监督机构组成一个托养组织,当遇到像吴悦一样无法站立的孩子时,会有专人把他送到学校和其他孩子一起读书,家长离开人世时,不用担心重度智障孩子何去何从。这个制度会代替父母们照顾孩子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