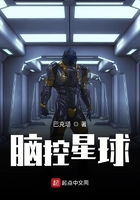可他并没有关手机,天黑后李小菊的电话来了,气咻咻的:
“画家,怎么回事,都等你呢!”他急颠颠地说:“早出门了,堵车呢。”
他飞身下楼。
他握着方向盘的双手明显在抖,他使劲摁着喇叭。他的心在狂跳。他变得像个孩子。他马上要见她了。这太像奇迹。这一天的到来似乎是无可抵挡的。似乎是十多年前早就安排好的。似乎有当时那样的学生气的暗恋,必然有今天这样的成人味的见面。似乎所有的暗恋,总会找机会变成实实在在的恋爱,以证明暗恋和恋爱是多么无关。他的车在疾驰,像一匹激情四射的野马,而街头披着霓光的景物像一场酝酿已久扑面而来的伟大恋爱。他需要强力克制,才能让自己看上去像赶麻将场的人。
他问:“你们在哪儿?”
李小菊答:“春来茶舍,308.”
他又问:“春来茶舍在哪儿?”
李小菊答:“群艺馆斜对面,你到哪儿了?”
他说:“快到了快到了。”
他一边应承一边极度厌烦着自己。
但是,不久他看见了光影迷离的春来茶舍。
他停好车,有穿旗袍的小姐迎他进楼,直接领向308.两侧的房间里尽是麻将机搅拌麻将的声音,他感觉自己双腿发软,气喘吁吁,谁知是因为恐惧和激动。他实在不能想象,十多年后他和祖玲会在俗气冲天的麻将馆见面。
他说,生活真是一个嘲讽大师呀。
他说,好吧,我倒要看看,生活能恶毒到什么份上。他敲响308的门。
他一眼就认出了祖玲。
是她,几乎还是十多年前那个人,几乎毫无变化。眉眼间那份平静和慵懒还在,看人时一刹那的郑重还在,难以复制的忧伤还在。
她只是礼貌地对他笑笑。
他故作平淡地走进去,目光从她脸上轻轻扫过。这一瞬间,他心里掠过一丝悲凉,含义模糊的悲凉,甚至有一丝心如刀割之感。仿佛他是被房间里的三个女子劫持来的,这场麻将似乎是一场处心积虑的骗局。更为重要的是,他断定,他心中的祖玲将和眼前这个名叫祖玲的女子快速合而为一,阴谋般合而为一,或者说,他心中的祖玲将被一个实实在在的吃饭穿衣拉屎撒尿放屁叹息的女子取代,一个忧伤的神将不复存在,一个长久的幻觉将从此消失,而且,他即将触摸到她的手指,甚至她的肌肤,甚至有可能在某个时刻拥抱她,甚至还有可能进入她的身体,他已经感觉到了几丝来自身体的微弱冲动——它是如此诱人又是如此令他心如刀割。他明明白白地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这张脸将终生被我伤害!”
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似乎是:
“我将深深地爱上她,至死不悔!”
他坐在那张空着的座位上。
连这个座位都像是骗局的一部分。
除了祖玲和李小菊,还有一个戴着贝雷帽、抽着烟的女子,名叫冯佳。三个人脸上都有一丝等待的疲倦,都有等米下锅的味道。
麻将桌上是用不着客套的,连介绍都不用,大家似乎早就是熟人了。祖玲刚好在郑安安的下手,郑安安可以不经意地随时观察她。他发现,她面色依旧苍白,目光脆弱、令人怜惜的印象似乎更强了。当然,他忽略了灯光的作用。他注意看她摸牌出牌的样子,他觉得,她精致的双手是他见过的最迷人的一双手,和另外两个女人的完全不同,令他想起两只雏鸽,舐犊情深,相濡以沫,安静而忧伤,仿佛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证明所有东西的粗糙,包括所有目光的粗糙。他真想立刻扔掉狗日的麻将,去车里取来画架和颜料,试试看,自己能否把这样的一双手画下来?她手上的动作是四个人里面最迟缓的,每次出牌时总是犹豫不决,有时还会悔牌,被李小菊戏称为“弹簧手”,她不恼,但也有些不好意思,脸红着对他解释,对不起啊,我刚学会。她的脸红是一个明确的标志,在他眼里,她忽然不是一个幻觉了,不是一个忧伤的神了,而是一个会害羞的总是出错牌的很可亲近的女子。他感觉良好,他已经不知不觉忘掉了她原来的样子,喜欢上了她眼下的样子,他用鼓励的眼神看着她,说:“没事,就是玩嘛!”两个人的目光有过最初的细微交流后,她开始试着和他说话,她问:“你在哪儿工作?”他耸耸肩,说:“我?我是个无业游民,早就辞职了。”李小菊拍了祖玲一把,说:“你个大脑子,人家是大画家,想找你当模特儿!”祖玲有些惊讶地反问:“我?我能当模特儿?”他故作平淡地说:“等有空了,给你好好画张肖像。”
冯佳说:“还有我。”
李小菊也说:“不管,先画我。”
郑安安爽快地说:“都画,都画。”
祖玲说:“记住,你们可都是沾我的光。”李小菊说:“看把你臭美的。”
冯佳说:“臭美臭美臭美。”
祖玲问郑安安:“你说是不是?”
郑安安说:“没错没错。”
李小菊站起来伸手戳了郑安安一指头。郑安安不禁脸红了。
祖玲看了一眼他脸红的样子,这一看分散了注意力,等下手的李小菊将牌摸在手里,她才如梦初醒地喊:“我打错牌了,我抠了!”她同时就推倒了牌,果然,把她刚打掉的二条取回来,夹在幺鸡和三条里,是完美的自抠。
另两个人阴着脸僵住不动。
郑安安缓缓推倒自己的牌,以示认可。
祖玲对他吐吐舌头。
李小菊终于也认可,说:“下不为例呀。”
于是继续抓牌。
他在心里说:够了,用不着更多了,眼前这个祖玲更好一些。谁知道以前的祖玲是什么样子?不,只有眼前,只有现在,没有历史。历史是不存在的。事实会在一瞬间内修改掉历史。除了爱上她,不可能有别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