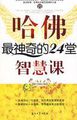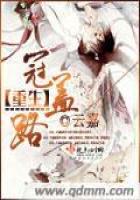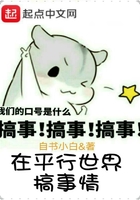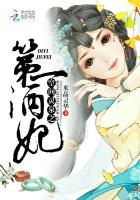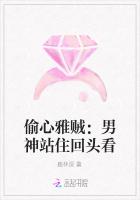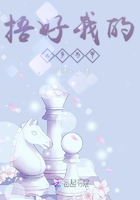有个非洲女孩儿在中国纪念郑和下西洋的展览馆参观时,无意间看到一只当年远航壮士使用过的粗糙瓷碗,她当即在那座展柜前泪流满面,长哭不止。
社会开放之后,编纂族谱的风习渐起,自南方蔓延至各地。人们渐渐意识到,中国民间修编家谱不是什么封建余俗,不是助长宗族黄头的坏事。我们杨氏今日出谱,算来晚了几十年。
我们这一支杨姓子孙,世世代代在桐柏山以南,也就是湖北省应山县(今为广水市)县城之西的一条丘陵地带上繁衍生息。历代多以务农为生,男耕女织,偶出一两个读书之子,均未能远离故土,赖以田亩持家度日,说不上诗书传家,也说不上清德雅望,更不曾出过达官显贵。然而,杨氏一门注重传承勤劳节俭之家风,以耕为本,以勤治家,以善立身,以诚待人,以忠义纯朴取信和结缘于乡里。无论是国难之际,还是大灾连年,无论四方如何混乱,杨氏子孙里也没有出过汉奸走狗或盗贼恶棍,于乱世中彰显了朴实的爱国情怀和正直的家族遗风。
在人类无数漫长的遗传链条中,每个家族都是其中或长或短的一支,每个人都是各自家族遗传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会被或轻或重地烙上“出身”的标记,这种标记通常是指他(她)的家庭所处的某种社会类别或阶层属性,比如现代社会的工人、农民、商人等等。说到出身,往往会延展到某个人的整个家族乃至家族史。很多人也会有意无意地追询起自己的前辈,并且没有辈数限制,似乎是愈久远愈好,直到说不清为止。这种追询,虽然不同于“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何处去”那种对人类社会终极命运的询问和哲学思考,但它依然带有神圣的色调。因为这种追询本身,体现了人类社会的一种重大进步。动物不具备这种意识和灵性,在人类先祖的母系社会,原始祖先们也不具备这种寻根问祖的意识,因为那时人们能够明确的长者,只有母亲和外祖母等这种模糊而简单的亲缘线索。
前些年,有个非洲女孩儿在中国纪念郑和下西洋的展览馆参观时,无意间看到一只当年远航壮士使用过的粗糙瓷碗,她当即在那座展柜前泪流满面,长哭不止。因为这位一头黑发的美丽黑人姑娘,发现碗上的花纹和她家里祖传的一只瓷碗一模一样。她在这里认定了自己几百年前的先祖,就是郑和船队的中国人,就是当时被重洋所阻隔、终生困在异国的某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男子。她有理由痛哭,对自己祖宗的确认使她如此百感交集。看来,寻根问祖不仅仅是中国人的文化情结和心灵缘由。
还是说我们这个家族,因为若干代之前的先辈在艰辛的迁徙途中遗失了族谱,以致今日我们无法追寻到更远的前人。就龙泉这一片来说,现在能够说上来的一个最早的男性长者,据说是个穷困潦倒的汉子,家徒四壁,冬天靠裹草御寒,因为他意外娶了个河南女子为妻,才有了我们这个杨氏族系。不知道谱中写了这个“源头”没有,如果有根据,就应该这么写。中国有很多大姓氏的族谱,都不约而同地把各自的祖源追溯到周文王那里了,浙江奉化的蒋氏族谱和湖南韶山的毛氏族谱也在其中。至于杨氏,很多族谱也不约而同地追溯到东汉杨震和隋代的杨坚那里,开国帝王杨坚起于随,也就是今天我们广水的邻县随州,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一点,否则攀隋文帝为宗的周边杨氏子孙的积极性会更高。这样编出来的家谱只能是歪曲祖根,只能让人感到荒唐可笑。
以先辈为荣,不为错,更不为过。但先辈没有给我们留下显赫和荣光,后世更应努力进取。好在近世几代,许多杨氏子孙崇文尚学,发奋苦读,有些已经学有所成,流布四方,并竭诚报效社会。
我们的前人有些早已入土为安了,健在者也大多是白发苍苍,风烛残年,我等亦两鬓染霜,垂垂老矣,只有殷切地寄厚望于来者。但愿有更多的后世之人,更能奋发向上,更能有所作为,更堪为人世之杰。同时也坚信我族后生定能不负天地造化,自初孜孜于学业,诚实做人,踏实做事,牢记忠孝大义,坚实地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敢怀高远之抱负,敢领未来时代之潮头,以告慰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李清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