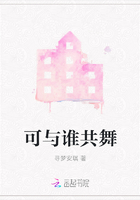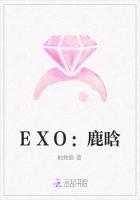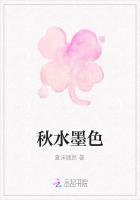读书,尤其是读某些与自己写作兴趣对路的“看家书”,重要的不在于能否记住具体内容,而在于能否从中启发出自己的思索来。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总算有一方对自己读书写作较为方便的陋居。年年月月,寒星孤灯,不停地做些“雕虫”文章,所得虽很微薄,但一年累计下来,约莫也能顶上大半年的薪水。这笔收入除用于抽烟外,剩余部分几乎都用到购书上了。曾戏曰:羊毛出在羊身上,只当是“文革”那阵子没稿费。
最近,我却越来越怕进书店了,倒不是自我满足,离“家藏万卷”还差得远呢;也不是怕花钱,彩电、钢琴之类的高档家庭设施对我来说,可能是二十一世纪的事,亦不觉为憾。只是那三千余册藏书,外加一些期刊和剪报,早已让四架书橱超载,壁柜、木箱也利用了,现在又开始向写字桌底下的空间挤占。进了书店就想买,买回来又愁没地方搁。
曾经几次想剔除一部分,可清出几本又不忍舍去。像我这样在业余时光写点杂牌文章的人,没有时间跑图书馆,主要靠自己的书籍作参考资料。有些书眼前似用不着,如果哪天又需要它们呢?对书而言,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读者,多数书是为用而买的。不少书到手后即读过了,但对其内容只留有大概印象。甚至有些在生活和写作上可能要用上的一般性知识,由于是后来“补的课”,也记不大清楚。那几年在部队,机关组织干部拿大学文凭,每临考试,诸如某个历史事件的重要意义有几点的答案,常常背得叫人头脑发胀。因而,当我得知有些前辈学者能够准确地复述他们的少年时代读过的书,写作往往不必借助资料时,不由生出一种自惭的感慨。后来转而一想,并非我们这些人天赋太差,而是我们“背书”的年龄作了那场浩劫的牺牲物。况且,读书,尤其是读某些与自己写作兴趣对路的“看家书”,重要的不在于能否记住具体内容,而在于能否从中启发出自己的思索来。故要认真去读,边读边思,正如清人申涵光言“学而不思则罔”,是也。
这般想来,我感到自己还是多置几本好书。所以仍不时去书店走走,只是注意挑选那些更可能用得着的买。在质量较高的前提条件下,一要资料性较强,二是内容较新,没有多少与过去出版物交叉重复的。对现今出版的一些叙事性读物,一般不购,但很注意读。我采取的是“后睹为快”之策,当某著某文轰动之后或大家都称其好时,我才借来阅读,当今文海浩瀚,我以为自己只能如此。
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但我们如能正确地运用它,一次足矣。
——英国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