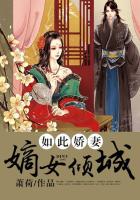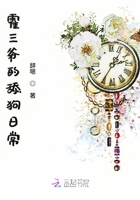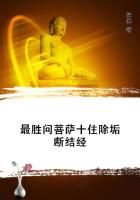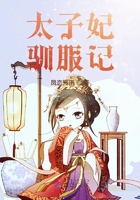“草原的上空,天蓝得耀眼,朵朵白云无依无托,缓缓飘移,有几只苍鹰在白云下自由翱翔。草原的远处,有莽莽群山,山与山的深壑间,有浩如烟海的白云缭绕。山的阳坡长着茂盛的青草,阴坡则长着大片葱郁的森林,森林碧绿苍翠,青黛一色。”
世人皆感疑惑,这可是几千年间一直被认为是没有开化的“蛮荒之地”?然而,从苍冥中伸来的那支时光的手指不可更移,伟人注定要从翠亨村走出!
广东出版界的卢锡铭先生和几位朋友听说我要写辛亥革命,再三邀请我去中山故里看看,去广州看看。在一路呼啸的“高铁”车厢里,我很久保持着半躺的姿势,在思索这场革命的发动者和引导者,思索他赋予这场革命的宏伟境界和革命最终出现的抱憾结局。
孙中山是谁,我们都知道,其实又未必“知道”。
他是伴着陈年拷贝划出的丝丝杂音出现在银屏上的那个手执文明拐杖,如木偶般颠跳着行路的一个洋气老头儿;他是伴着年轻的宋庆龄出现在各种印刷物上的一个头戴白帽,身材并不伟岸的政治领袖。很少有人刨根问底地说起这个家喻户晓的伟人究竟伟大在何处,很少说到他对历史做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那时我们印象中的这位历史风云人物就更像失真拷贝里的孙中山那样,容貌不那么清晰。
多少年来,我们读到的是他不改不弃地奔走于大洋之外,苦口婆心地募捐,苦口婆心地联络发动,还有绞尽心血地苦苦策划,然后伫立于海涛彼岸苦苦地等待,但一次次等来的都是失败。如果是仅仅是个人的一项事业,我相信他早就挥手而去了。可他是为了实现中国有史以来一个最崇高的信念,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健康而持久的社会。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曾经掩卷沉思,先生所以伟大,所以高山仰止,所以前无古人,最感人的壮举正是体现在这种永不言败的信念追求上,正是体现在这些坚韧不拔的革命行动上。
十九世纪中叶,古老的中国被变异的气候折腾得愈来愈坐卧不宁,萌动的中华大地在期待一个人物,而在这个辽阔的国度,许多地方都有可能孕育出这样一个超凡的人物。但是,数百年间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京畿地区被排除了,历史上长期是帝王之州的中原地区被排除了,三秦被排除了,荆楚被排除了,连在历史上出尽了人物的东南沿海也被排除了。最后,历史的目光停留在南海之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稍加辨认,它就以极其肯定的手势指向了香山县的这个小小村落。
世人皆感疑惑,这可是几千年间一直被认为是没有开化的“蛮荒之地”?然而,从苍冥中伸来的那支时光的手指不可更移,伟人注定要从翠亨村走出!
有资料介绍说,翠亨村东临珠海,西为群山起伏的五桂山脉。其实,我感到没有必要为一个小村展示那么大的地理背景,倒是展览馆的一座沙盘让我们领略了翠亨村的“风水”所在。在香山县两道不高的山岭之间,一条兰溪蜿蜒流过,溪流一侧有个叫山水井的地方是片平畴,翠亨村就坐落其上。
不过,所谓风水宝地并没有给更夫孙达成带来什么优裕,他们一家人过着贫寒卑微的日子。今天的游人通过展室的照片来看,如果说这个极其普通的农家有什么与众不同,那就是其男主人面容清癯,女主人则显得富态端庄,而他们最有作为的儿子却承接的是母亲之“福相”。虽然没人将这种遗传结构称作“最佳遗传模式”,但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游人发现,此后出现在湖南湘潭韶山冲那个举世闻名的农家,在这一点上与其有着惊人的相似。
伟人所以从这个沿海小村走出,是因为历史已开始进入海洋时代,过去偏僻的海隅变成了时代的前沿。历史的风声雷鸣在中原大地上经历了几十个世纪的呼来滚去之后,不由转移到了南中国海滨,历史的焦点一时间也随之南移了。
或许,中华民族一个灾难的世纪是从南中国海开始的,这里就必须孕育一个超凡的人物来拯救这个民族。
对于孙家来说,他们之所以能够培育出这个伟大的儿子,是因为翠亨村村头的那条小路通向辽阔的大海,通向外面的世界。父亲孙达成早年在澳门当鞋匠,做裁缝,长达十六年,三十三岁回到村里,虽然他依旧贫穷,靠租种别人的土地和兼任村里的更夫养家,但他在幼子心中朦胧地描绘了一个不同的社会图景。同时,孙达成的二弟、三弟和长子孙眉也都到海外谋生。勤勉孝敬的孙眉曾经给地主做过长工,后来闯荡到檀香山,开商店,办牧场,几经打拼,终成雇工过千、拥有两万亩牧场的一代富侨。孙中山十二岁那年,他按照兄长的安排,随母远赴檀香山就读。第一次漂洋过海,使他“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这次为期五年的海外求学,催生了这位中国少年的壮志情怀。
一代伟人留给翠亨村最深的记忆,还是当初那个与村里其他小伙伴一样拖着长辫,一样见到货郎来了就往村口颠跑的小男孩。所不同的是,这个小男孩稚气的脸上有时候多了点难以觉察的少年之沉稳,有时候还能从他嘴里听到不像孩子的见识。当年的光脚男孩不叫孙文,也不叫日新和逸仙,只有个幼名“帝象”。这个名字巧合到伟人身上,是别有意味的,我不知道它是否给伟人故里留下过什么话题。
翠亨村那段苦难的童年使孙中山立志要改变中国,而他后来远出大洋的经历使他懂得了怎样改变中国。
我们今天看到的孙中山故居,并非是他出生时住过的屋子,而是在他二十多岁时由他的“大款”哥哥提供资金建造的,孙中山断断续续地在这座院落住过多年。
故居的院落并不宽敞,大门和围墙都很简洁。游人远在院外就可看见墙里面的一株躯干倒卧的酸子树,还有室内陈设的八仙桌及其人工仿制的形色逼真的满桌菜肴,号称“九大簋”。那些独特的牡蛎墙、做工比较考究的褪色桌椅和古朴的海碗鱼肉,让人感悟到南海的乡风,但无法与长期奔波海外的那位革命家联系起来。不过,走近那座小院,我们就想到有功于中华民族的孙氏兄弟。
当年的长工孙眉,无意中为他曾经受过苦难的“长工社会”培植了一个最为重要的掘墓人。
母亲杨氏比孙父年小十五岁,这对贫困的老夫少妻当然未曾料到,他们生育的第一个孩子改变了他们的家庭,而第五个孩子却改变了整个国家。
当年杨氏带着孙中山远赴檀香山求学,那天清晨,走在村口小道上的这对母子,在高高的蒲葵下显得那么矮小。这位勤劳慈祥的母亲当然也不会想到,此时此刻她爱怜地牵起的这双柔软稚嫩的小手,后来牵引了一个民族,牵引了一场伟大的变革。
如能善于利用,生命乃悠长。
——塞涅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