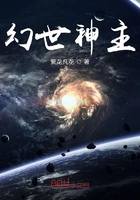徐志摩与德国之表现派
郑寿麟译
本刊顷承郑寿麟君(北平文津街一号德国研究会)惠告,北京大学教授德人洪涛生君(V。Hundhausen)以德文译编之《琵琶记》剧本,现经德国爱好艺术之人士,于本年一月十五日,在柏林Lyceum Club公演。按洪涛生君歆慕中国文化,致力文学作品之翻译,成绩甚伟。已译成德文者,计有:《中国诗人》,《庄子》,《卖油郎独占花魁》,《西厢记》(以上均一九二六年),《陶渊明》(一九二八年),《琵琶记》(一九三〇年),凡六种。前年春,洪君在北平天津亲自导演《琵琶记》(德文)时,本刊曾有简单之记述。又去年十二月六日(徐志摩君追悼会)之日,洪君曾以德文撰纪念徐志摩文,刊登天津德华日报。该文对徐志摩君推崇备至,谓其以诗人之资格,领导中国新文化运动,推翻旧模型,新开辟道路,业已成功。篇末附录徐君《雪花的快乐》一诗,并由洪君译之为德文诗。洪君又谓徐志摩君可比西方之浪漫派,而异于西方之时髦的表现家。但洪君此文篇首曾引德国表现派诗人施达德来儿(Ernst Stadler)之诗一首。此诗今由郑君译为中文,观之可略知德国表现派之主张。郑君所译该诗如下:
模型与门闩必须破坏,
世界当穿过开通的管子,
模型是和平,愉快,乐天的满足,
我偏要掘翻土块。
模型要束缚我,压制我,
我却将我的存在驱到大千世界。
模型是明白而没有慈善的,
我却要追寻昏昧的人,贫乏的人
我要毫无限制的解放自身
使我充满了生命。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一一期)
我对于徐志摩的认识
唐诚
“但是事实是咱们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短篇。每回我望到莎士比亚的戏,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一类作品,比方说,我就不由的感到气馁,觉得我们即使有一些声音,那声音是微细得随时可以用一个小拇指给掐死的。天呀!哪天我们才可以在创作里看到使人起敬的东西?哪天我们这些细嗓子可以豁免混充大花脸的急涨的苦恼。”
——徐志摩《猛虎集·序文》
“徐志摩是仅有大诗人底浮光,而无大诗人底实质的……我们试看所称为世界最伟大的诗人席勒,葛德,莎士比亚,莫里哀,但丁的,哪个不是……才能得以达到他们那伟大的成就,伟大的人格呢?”
——杨丙辰大诗人——天才——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
我在本刊第二百零九期中,读了杨先生那篇论徐志摩的文字之后,我就联想起徐志摩《猛虎集》的那段序文。志摩不愧有自知之明,而杨先生也的确称得起是志摩的知己了。
一个作家的最后评定,原不是他同时代的人——更不是他的朋友们所能确定的。所以像什么追悼会上的演说词,什么哀悼专号里的纪念文,其意义原不过等于一副挽联,一首挽诗,一篇祭文,一块碑志而已。从友谊的立场说起来,当然有它们的意义在着,可是若从文艺批评的观点来看,那些文章,也不过是韩退之的谀墓文字一类而已,本来不甚靠得住的。杨先生这次竟认乎其真的定要推翻他们给志摩的私谥——大诗人——天才,定要打倒志摩的“诗圣”“诗哲”的招牌,似乎太过于认真了。其实几十年几百年后,世人对志摩的批评,究竟怎样,我们固然无从知道,就是当代的人,也没有给志摩一个公认的评价。就是志摩本人,对于他自己的认识,也并没有自视特高,想插足大诗人之列,这有《猛虎集序》文为证。就是他的朋友们也并没有把志摩算做莎士比亚葛德但丁同等的大诗人——天才。他们至多,只不过拿他和雪莱相提并论而已。
然而志摩毕竟是诗人,是天才,假如诗人和天才不一定必须莎士比亚葛德但丁那样的人才配称的话。李杜韩白固然是诗人,温李冬郎也还是诗人;苏辛周姜固然是词家,温韦正中也还是词家。内容之雄浑深厚与轻新微妙,至多借以判别作者之大与不大,伟与不伟而已,却不能赖以断定作者是不是诗人。文艺欣赏本来主观的成份居多,所以志摩的作品,是不是好诗,不是旁人用文字说明可以拥护或打倒的。志摩的三部诗集,才是最坚实的凭证。大家读了他的诗,自会鉴定的,我现在凭记忆所及,随便提出几首来,我个人认为的确是诗,是好诗。散文诗如《婴儿》、《毒药》;土白诗如《一条金色的光痕》;歌谣体如《盖上几张油纸》、《海韵》;长篇如《康桥再会吧》;短章如《天国的消息》、《偶然》以及《一块晦色的路碑》。
不过志摩对于中国新文艺的将来,假如有相当的贡献时,据我看,并不在他那些诗篇的本身,都在他那创造的精神和尝试的工作上。志摩的诗,我个人以为的确是新文学运动发生后十几年来可贵的一宗收获。但是绝非杨先生所要求的“对于人生有最深切的认识及最正当的了解”,“反映全时代的痛苦欢乐,全民族全人类的一切情感”,而“用最优美和谐的形式吹嘘到了纸上头去的”,“浑然天成圆润精颖的一致的个体”的那种理想的作品。虽然我个人怀疑这种理想的作品曾否有过,然而志摩的作品,不能算是“登峰造极”的作品,这是无庸疑议的。所以我说志摩的诗之本身,对于新文艺之将来,其贡献并不能算怎样的大。可是志摩他那种运用西洋诗的格律来创造新的诗体,居然有了相当的成功,这一点我认为是志摩和他的朋友们的功绩。有人说他们这种工作,只是抄袭,只是模仿,哪能算得创造?我觉得不然。中国诗的格律,无论怎样的演变,终没有跳出阴阳平仄的范围,四言变而为五言,古体进而为近体,诗演为词,词化为曲,都离不了阴阳平仄。现在志摩他们居然独辟蹊径,应用西洋诗的抑扬轻重的音尺到中国诗里来。中西文字,根本不同,这能不说是一种创造吗?现在他们这种试验,距完成为期尚远,(鄙意若望完成,恐怕非先体验出一种新的读法不可。此非题内之文,容另详。)然而已经可以看出它的可能性了。将来倘使继起有人,这便是划分时代的一种运动。艺术的作品,无论怎样总不能不凭借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吧。否则,仅是一点意像,绝不是一件艺术品。就算最空虚缥缈的音乐吧,也得凭借音调节奏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不然,悲多汶纵有更多的音乐的意像,恐怕也不能使他成为伟大的音乐家了。诗歌是比较有实迹可寻的艺术,当然更免不了形式的限制。这一点,我知道杨先生是一定赞同的。不过他理想中之诗的质与形之关系,是“一点精妙和谐的内心为它(诗)整个的底盘,而一切表面的精彩,譬如说声调与形式,俱是要由这一点内心里发露了出来,然后才能令人们觉得,它是浑然天成圆润精颖的个一致的个体,一首好诗。”所以他主张“每一首诗都各有自己的一个形式。”换句话说,杨先生是反对“诗有定形”的。这种理想,当然极高,但是事实可能吗?语言文字是这样的圆满无缺的表现工具吗?我们极普通的意念,语言文字的表现力尚且有时而穷,何况极微妙的诗歌呢?任你多么伟大的天才,恐怕也不能超越这种语言文字自身的限制吧。形式变化最自由的,莫过于散文了,然而散文也有散文的极限呵。而意像呢,那是极富有变化的东西,所以杨先生的那种理想,恐怕不易实现。莎士比亚、葛德、席勒、莫理哀、但丁诸伟大诗人所写的诗,不也是限于一定的形式吗?
我相信内容与形式,确乎有相当的关系,譬如说,一首绝诗的内容,不能装到古风的形式里去。一首小令的词,不能演而为近慢,元曲的内容,不能移而入词,所以散曲究竟是散曲的意味,绝不能与词相混,都是这个原故,而新文艺之所以要另创新文体者,也是这个原故。但是其相关的程度,也就止于此,如若不然,那就根本无文体之可言了。
因为杨先生批评徐志摩的出发点在此,所以上边特别提出来讨论一下。现在要回到本题了。杨先生指出志摩的缺点在于偏重形式,的确是一针见血的论断。然而人的才能究竟有限,我们假如知道志摩一面是在写诗,一面还在尝试诗的形式时,我们便可以宽恕他的诗内容欠充实的缺陷了。我们能希望一个在试验室里做试验的人,要像工厂里的工人,那样纯熟老练吗?志摩的诗,露出“努力从事粉饰雕琢的破绽”,原是当然的结果。然而他的诗,居然能够“声调流利好听,形式轻盈优美”,不已经是难得了吗?
大凡创造或是最初应用一种新文体的人,都是费力不讨好的。譬如介绍十四行诗到英国文学里去的Waytt吧,他自己做的十四行诗,当然比不上斯宾塞、莎士比亚、华茨华斯、雪莱、罗色蒂他们,然而这创始之功,却不能说小,所以Wyatt在英国文学史里,依然有他一席的位置。志摩现在干的工作,也就是Wyatt当年所干的工作了,不过中西文字差的太远,所以更难讨好罢了。不幸志摩早死,未能竟其全功,现在只有盼望他的朋友们,继续努力,有以成其志而已。
杨先生要在志摩身上就发现到莎士比亚、葛德,那样伟大的诗人,未免太早,当然要失望。志摩的朋友们把他比做雪莱,虽然有几分相像,恐怕也有点过分。我现在希望他做中国的Sir Thomos Wyatt(1503—1542),我想志摩是当之无愧,至于继起者,有没有斯宾塞莎士比亚一流的人,已死的志摩是不能代为负责的。
编者按:本文作者唐诚疑为唐钺之误。
(原载: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一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二一二期)
论诗人徐志摩
——对于杨韩吴唐诸君的文章之批评
并敬告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先生
张露薇
按:自本刊近顷登载杨丙辰(第二百零九期)、方玮德(同上)、韩文佑(二百十一期)、唐诚(二百十二期)诸君评论除志摩君诗之文后,一月二十八及二十九日北平晨报学园亦刊登吴世昌君《论志摩》一文。嗣后本刊收到关于此题之来稿甚多。今选登张露薇君一篇,本问题就此结束。其余诸君之作,以限于篇幅,概从割爱,分别退还。其中重要者,有(一)杨丙辰君回答韩文佑君文,解释彼原作中“妤玩”二字之意义。谓徐君一生“作事(离婚,交友,写文章,作诗)底动因,皆为浅浮的外表所诱惑,而无悲壮深刻的意志与澄澈宏阔的识力来把许多从各方面说皆不利于他的诱惑斩断的”,故称之曰好玩。(二)济南李鲁人君文,谓徐君甚有功于新诗运动,但其所作未为精到。又谓新诗以爱情颓废为主,乃其缺点云云。
又按:张露薇君此文甚长,前半今略去不登。其大意可撮述如下:〔1〕批评必须有明确之立场,且须负责。不当为字句之攻驳,亦勿徒作虚浮之颂誉。〔2〕细阅《晨报》哀悼除志摩君诸文,惟胡适君能略言徐君之理想,吴其昌君能略状徐君之生活,外此则林徽音君及叶公超君(叶君文载本副刊二百零二期)之文颇能显示徐君之生活与价值。余皆无益之谀词而已。〔3〕批评徐君之诗者,仅见三篇。一为《小说月报》十七卷朱湘君论徐志摩的诗,二为《北晨学园》哀悼专号中于赓虞君志摩的诗,三则杨丙辰君之文。以上三篇,皆褒誉徐君之作。〔4〕杨君文有一定之立场,并非谩骂,惟欲于朦胧云雾中将徐君之真价值显露于人间而已。惜韩文佑、吴世昌、唐诚三君误会此旨,徒事辩驳,流于感情意气。以致双方隔膜甚多,几变为琐屑及滑稽之论争。予今作此篇,自抒所见,未敢苟同,亦并无左右袒。视诸君或异撰耳云云。此下可接读张君原文。本副刊编者识。
徐志摩是个什么形象的人,我实在不知道,据他的朋友们说,是漂亮得了不得。因为漂亮,所以可爱,因为可爱而会写诗,所以是古今少见的大诗人。我承认志摩是诗人,但是他的诗人的成分并不是纯洁的,也不是如他的朋友们所称他是怎样空前伟大的天才,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诗,所以尽说些阿媚奉承之词,而损污了志摩的诗之真正的价值。的确,我相信,志摩是诗人,志摩有天才,但是他的天才没有发展到极点,所以这位不幸的诗人只是一颗陨星。我们除了怜惜之外,再难以加上什么毁贬之词,这是真情。然而,为了中国文艺的发展,我们对于志摩的诗之批判不妨苛刻一点。有些人总认不清这点,往往以为批评某作家的作品,便是批评某作家的本身,这真是绝大的错误。
为了说明志摩的气质或天才,我们不妨学学斯宾诺沙(Spinoza)的哲学意旨,把志摩分成“诗人的志摩”和“凡人的志摩”两部分。我曾说过,志摩是有天才的,从他的诗中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这诗人的志摩,的确是我们可以崇敬的人物。在他的诗里明确地表现出他的个性,有一种特异的美点。他有他的世界观,他有他的哲理,他有他的丰富情感,他有他的特异的风趣,然而,你如果细细的考察起来,都染着现世纪病态的情状之浓厚色彩。任你拿出哪一句来,总没一句是健全的艺术,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但这不能怪他,他的思想是时代的反映,是时代的污点,要怪,你也只好怪这不谐和的时代——杨君的批评忘记了这点,所以他的批评只是以诗论诗,而并未考察一下志摩的诗之来源,以明了他何故“追求腔调的铿锵”,“只有大诗人的浮光”“而无一种真挚坚贞的性格”。我以为,这就是杨君的文章最使人感到有遗憾的一点。至于如韩吴二君者,不批评杨君批评的立场,而只意气从事,我们读者自然是不会满意的。
志摩的一生是求美求爱求自由的,这不容我们否认。美是人生最高的目的,爱是人生最真挚的快慰,自由是人生最美妙的理想。世界上能否有真美真爱真自由,这是另外的问题,但是,需要美,需要爱,需要自由,这确是人类普遍的要求,摩登少女最求美,浪漫青年最求爱,狱中囚徒最求自由,然而我们并不能以其所求,而直称之为“诗人”,直称之为“伟大的天才”。这种追求者是否是一个诗人,完全在于追求的方式。合于方式的追求,便是诗人;不合方式的追求,便是凡人。因此,我们观察一位诗人,我们便不得不观察他的气质。正如培根所说,诗是一种谎话,我们要从谎话中再去认识诗人,这才是我们了解诗人的途径!
志摩的诗大约可以以其诗集之卷数,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志摩的诗》的时期,第二是《翡冷翠的一夜》的时期,第三是《猛虎集》的时期。
一在第一个时期,大约是受了太戈尔及当时时谓“新诗”的潮流之影响,所以,除了《雪花的快乐》等几首情诗以及其他几首胡式(胡适之式)的人道诗而外,多半是哲理诗。哲理之入诗,本来就勉强,把哲理拖进诗行里,更是勉强而又勉强。我的意思是说,好的诗可以含着哲理,这种哲理有诗的灵感后才使人感到的;并非先有了哲理,硬把哲理用诗行表现出来。志摩初次的诗篇多犯了这点毛病,因为硬把太戈尔式的哲理添满诗行,虽然得了“诗哲”的雅号,但是诗是失败了的。其原因就是,哲学是理智的追求,诗歌是情感的描摹,理智与情感根本矛盾,根本冲突,相反相成的机会只不过是偶合的事实。所以,要企图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无论如何是要失败的。志摩的第一本诗集之失败就在这一点。其次,占一部分的胡式人道诗,也是同样的失败。这失败的原因自然要归罪于当时的文学运动,因为诗人本有好奇心,有了新的形式或新的意境他总要试一试的。当时的思想界庞杂混乱的堆着一些零碎的思想,什么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什么易卜生式的社会斗争……贩运者便大喊其口号,居然的登宝座称孤道寡的自命“思想界的权威”了。志摩受了这种时代的影响,便写出他的《太平景象》、《盖上几张油纸》、《一小幅的穷乐图》、《先生!先生!》等等含着人道主义的怜悯与伤感色彩的诗,虽然描写的技术是比胡适君的《人力车夫》进步,但其意识之不正确,语句的滑稽,实在使我们不敢相信这类的诗是志摩的杰作。在这本“献给爸爸”的诗集里,有几首情诗,倒是很好。除了那首有名的《雪花的快乐》而外,其余如《她是睡着了》、《我有一个恋爱》等诗,还含着真实的灵感。我以为,志摩的诗最成功的,还算他的情诗,其余者虽不忍说一句“卑不足道”,但是总比情诗差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