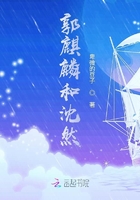《旧唐书》编成于五代后晋:由宰臣刘?领衔主编。至北宋中期,欧阳修、宋祁又奉诏重修《新唐书》。两书编纂年代相隔不久,但评价却颇不相同,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旧唐书?文苑传下》有李白传,其前为王维,其后为杜甫,三大诗人的传排列在一起,其中李白传篇幅最短,王、杜两人传则较长。《旧唐书?文苑传序》在列举唐代各体文章的代表作家时有云:“王维、杜甫之雕虫。”(此处“雕虫”指诗歌)举王、杜而不及李白。更足注意的是《杜甫传》后面节录了元稹《杜工部墓系铭序》的大段文字,引文前以“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曰”起句,引文后以“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作结,肯定了元稹的看法。《旧书》所引元稹文字,前面叙述历代诗歌演变,中间竭力赞美杜甫诗歌成就,认为“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最后一小段论李杜优劣,文曰:
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云云,是指五言排律(一称五言长律)而言。杜甫的《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即是一篇长达千字的长篇排律。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两百二十字的五言排律,《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是两百字的五言排律。杜甫五言排律叙述详赡,具有“铺陈终始”的特色;又其集子中五言排律数量颇多,也有部分佳作。五言排律篇幅较长,往往对偶工致,声调和谐,具有“排比声韵”的特色。元稹认为李白诗成就不及杜甫,在五言排律方面差距很大;《旧唐书》编者肯定元稹的这种看法,表现出扬杜抑李的鲜明倾向。
《新唐书》编者并不扬杜抑李,而是李、杜并称。《新唐书?文艺传序》总论唐代文学、文人时有曰:“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并列李、杜,只是李白名在杜甫下面,或许认为李诗稍逊于杜甫。《新唐书?文艺传》中列有两人传记,篇幅差不多。《李白传》末曰:“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曼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以此结尾,显然寓有褒美之意。上引元稹文中曾赞美李白诗“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新传》引用唐文宗诏命,把李白诗和张旭草书等并称,也是对李白诗歌纵恣奔放的特色作了高度肯定。《新唐书?杜甫传》后面附有史臣赞语,表明对杜诗的特殊重视。赞语中赞美杜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人”,还引用了元稹“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的评语。赞语又曰:“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对杜甫的五言长律也有所肯定。赞语末尾曰:
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明显地表现出李、杜并称,不应扬此抑彼的看法。这种看法同元稹、《旧唐书》史臣的主张,可说是针锋相对,对元稹、《旧唐书》扬杜抑李之论,寓有针砭的意义。
《旧唐书》对李白的评价何以不高呢?《旧唐书》署刘?撰,实际出自赵莹、张昭远、贾纬、赵熙等史臣之手。(参考赵翼《廿二史答记》卷十六《旧唐书源委》条)编纂时代为五代后晋。其时虽经历唐代中后期韩愈、柳宗元等一些古文家提倡古文,但影响不很大,在文坛以至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仍是骈体作品(包括骈文、骈赋、律体诗等),骈体文学较之古文占着明显的优势。《旧唐书》编者崇尚骈体诗文,该书每篇末尾史臣的论赞,常用骈文体;其纪传的叙事部分,句式、气格也与古文不同。《新唐书》编者对《旧唐书》的文风很不满,认为其编者是“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曾公亮《进唐书表》)。古文家贬低骈文时,常常使用“气力卑弱”一类话。《旧唐书》由于崇尚骈体文学,于诗歌就推重律体诗(包括篇幅有长、有短的律诗、平仄调协的绝句),因而对擅长古体诗和乐府歌行,不爱多写律诗的李白,就评价不高。上文所述《旧唐书》编者同意元稹说李白在五言排律方面远逊杜甫的话,就是一个明证。
《旧唐书?文苑传序》有一段话,明显地表现出编者崇尚骈体诗文的态度,文曰:
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于昔贤,要取名于今代。实以淳朴之时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故饰以文言,考之弦诵,然后致远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近代唯沈隐侯斟酌《二南》,剖陈三变,摅云、渊之抑郁,振潘、陆之风徽,俾律吕和谐,宫商辑洽,不独子建总建安之霸,客儿擅江左之雄。
在这段文字中,编者在讨论文质问题时,肯定文,反对是古非今,这实际上是肯定汉魏以来骈体文学的发展。又“饰以文言”句中之“文言”,似即指相传孔子所作《易传》中的《文言》,篇中颇多偶句。《文心雕龙?丽辞》有曰:“《易》之《文》(《文言》)、《系》(《系辞》),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即指出《文言》中多骈偶成分。在下面,《旧唐书》编者又特别对沈约加以称颂。沈约提倡区分四声,提倡写作新体诗,是把古体诗引向格律化的有力倡导者;他们所写的新体诗,是唐代律体诗或近体诗的前驱。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叙述历代文章(以诗赋为主)发展,指出汉魏文风经历了三次变化,又大力主张区分四声,使作品音韵和谐。《旧唐书》编者肯定这些主张,并且赞美沈约的制作能继承汉代扬雄(子云)、王褒(子渊)、魏曹植、西晋潘岳、陆机、刘宋谢灵运等辞赋、诗文名家重视文采骈俪的传统,并有新的发展,成为一代文豪。由此看来,《旧唐书》编者对待文学的基本态度是反对是古非今,充分肯定后代文学的新变和发展,肯定汉魏六朝的骈体文学。他们十分推崇沈约,因为沈约的理论和创作,为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启了先路。
如众所知,李白在理论上鄙薄魏晋以来追求词采华美的诗歌,曾经宣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其一》)又据孟?《本事诗?高逸》载:
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
李白的这类话不免有些片面夸张。实际,他写了大量的五七言诗,七言诗成就尤为杰出,四言诗却写得很少。对建安以来以迄梁陈的各代名家,他还是向他们多方面地吸取营养。然而这类话毕竟反映了李白鄙薄南朝绮靡文风,要求诗歌恢复古代雅正刚健传统的思想倾向。李白也的确不愿多受声律束缚,故律诗写得颇少。李白鄙薄魏晋以来的华美诗歌,鄙薄沈约所提倡的声律论和声律论指导下的诗歌创作;《旧唐书》编者却是大力肯定汉魏六朝的骈体文学,推崇沈约的理论和创作。李白的诗歌,律体颇少。这样看来,《旧唐书》对李白诗评价不大高,也是很自然的了。
《旧唐书》肯定骈体文、律体诗的态度,还鲜明地表现在对元稹、白居易的评价中。《旧唐书》卷一一六为元稹、白居易传。传末有一段较长的议论,模仿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体例,综论历代文学,然后归结到传主。这样处理,就说明《旧唐书》编者对元、白评价甚高,认为元、白代表了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其地位犹如刘宋的谢灵运那样。传论中评论元、白有曰:
若品调律度,扬榷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
《旧唐书》对李白评价不很高,它不可能把李白、杜甫两人并列作为唐代诗歌的最高代表,于是找到了元、白。传论纵览历代诗歌发展,突出了三个时期和六位诗人:一是建安时期的曹植、刘桢,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二是永明时期的沈约、谢?,标志着新体诗的产生和格律诗的滥觞;三是元和时期的元稹、白居易,标志着唐代近体诗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旧唐书》对元、白诗的评价,可说是高极了。
元稹、白居易两人兼长古体诗、近体诗。两人的讽喻古体很有名。但在当时社会上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除《长恨歌》、《琵琶行》等少数歌行外,还有近体诗。其近体诗,有流连“杯酒光景”的短章,也有“驱驾文字、穷极声韵”的长篇排律,当时风行遐迩,被人广泛仿效,号为元和诗体(见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参考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论《元和体诗》节)。《旧唐书》赞美元、白诗为广大人士所喜爱,流播之盛,迈越前贤,又把两人与沈约、谢?相提并论,显然也是着重从近体诗成就的角度来评论的。李白以不长律诗被抑,元、白以擅长近体见扬,可见《旧唐书》编者推重律体诗的立场是很鲜明的。
《新唐书》纂修者欧阳修、宋祁都是古文名家,他们站在古文派的立场评价文学,提倡古文,反对骈体文;对律体诗虽不排斥,但也不像《旧唐书》编者那么重视。上面提到,《新唐书》编者对《旧唐书》的骈俪文风很不满,认为“气力卑弱”。《旧唐书》传记中多引用当日骈体文字,《新唐书》编者甚至对此也不满而加以删除。赵翼《廿二史?记》曰:“欧、宋二公不喜骈体,故凡遇诏、诰、章、疏四六行文者,必尽删之。”(卷十八《新书尽删骈体旧文》条)可见其厌恶骈体文的程度。对于律诗,古文家较为宽容,不但不排斥,自己也参与写作,只是文词尚清淡而不尚浓丽。但长篇排律,特别重视排比铺陈,其体格与四六文颇为接近,故古文家也并不欣赏。上文提到,元稹推重五言排律,因此扬杜抑李,《新唐书》不表赞同,即是明证。《新唐书》也肯定元稹、白居易的诗歌,但不像《旧唐书》那样高。《新唐书?文艺传序》有曰:“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元、白位置在杜甫、李白下面。又《新唐书?白居易传赞》引用白居易《与元九书》的自叙,分其诗为讽喻、闲适等四类,接着说:“又讥世人所爱惟杂律诗,彼所重,我所轻。至讽喻意激而言质,闲适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视其文,信然。”可见《新唐书》编者主要肯定白居易的讽喻、闲适两类诗,而不是肯定其律诗。因此,在《新唐书》编者看来,李白的律诗写得少,成绩也较差,是不影响他在诗坛的崇高地位的。
李白、杜甫两人作为唐代两大诗豪,在元和时代已得到很多人的公认。除上引韩愈“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诗句外,在白居易的作品中也有明白的反映。白居易《与元九书》有曰:“诗之豪者,世称李、杜。”说明当时大多数人并称李、杜为两大诗豪。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在大力提倡讽喻诗时,虽对李白讽喻诗写得太少有所不满,但在其他场合就不同了。他的《李白墓》诗有云:“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对李白诗评价极高。他的《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一诗,对李杜两家同致赞美,相提并论,誉为“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无所轩轾。白居易虽也爱写五言长律,其《与元九书》称赞杜甫诗“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也含有杜甫律诗成就超过李白之意,但说得较有分寸,并没有从长律方面过分贬抑李白,态度比元稹通达。
与元白同时的韩愈,推尊李杜之语不少,除上引“李杜文章在”两句外,其他如:“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荐士》)“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随。”(《醉留东野》)都是显例。晚唐五代,文士同时推尊李杜之例也常见,这里略举一二。如杜牧云:“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李商隐云:“李杜操持事略奇,三才万象共端倪。”(《漫成五章其二》)黄滔《答陈?隐论诗书》曰:“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干天。”此外,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顾陶《唐诗类选序》、韦?《才调集序》都对李杜备致推崇。可见自元和以来至五代,大部分文人已公认李杜为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元稹、《旧唐书》编者对李白的贬抑,只是在唐五代骈文、律诗盛行时期,少数一部分文人对李白诗歌的偏见。
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