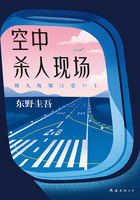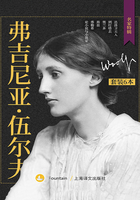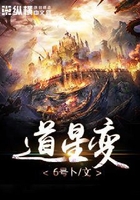一、传承京派创作风格的经典小说:《受戒》
《受戒》最初发表于《北京文学》 1980年第 10期的小说专号,随后荣获《北京文学》1980年度优秀作品奖。小说描写的是菩提庵(“荸荠庵”)环境下,小和尚明海与少女小英子之间青梅竹马的爱情故事,从他们的相识到渐渐情窦初开,小说写得清新含蓄而又质朴自然。作者对于地方风物、景物、人物、习俗等各式各样的生活细节,满溢着一种欣赏、玩味的和谐情趣。这篇小说无论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手法都与常见的小说风格迥然不同,一问世,立即引起文坛的高度重视,后来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评论者对它也赞誉不绝。
汪曾祺说:“四十多年前的事,我是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总和。 ”《受戒》发表之时的 1980年的文坛主流是余波未歇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受戒》的“另类”,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实际上,《受戒》本身对于汪曾祺而言实属顺理成章之作。他早年在西南联大师承沈从文,深谙京派的神韵和创作风格。汪曾祺是京派的最后一个传人,他疏离政治,是一个散淡、随和、热爱生活的人,同时也亦如京派作家一样追求唯美、和谐、圆融、恬静的艺术境界。他力求“出去净火”“享受生活”。他希望用文学去表现被压抑的人性。他创作了一系列的小说,关注凡人小事,关注风俗民情,试图用健康美好的人性温暖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隔阂。八十年代已是六十岁老人的汪曾祺喜欢回忆往事。他给小说下过定义:“跟一个可以谈得来的朋友很亲切地谈一点你所知道的生活。”这位老人历经沧桑,颇有学识,那些浓烈的激动的悲伤的故事被他娓娓道来,淡泊、飘逸、舒缓有致,开合自如,很有一番坐看云起云落的达观与洒脱。
《受戒》是汪曾祺回忆年少梦境的作品。在这个梦里,有一对美丽少男少女的清爽朦胧的爱情,有清澈的水乡情思,有健康淳朴自由的人性,还有和谐欢乐的世俗风情。这是一个可以荡涤现实粗燥灵魂,唤醒人性,去粗去燥,给人以温情的理想之梦。
汪曾祺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这与 30年代沈从文书写人性优美、健康、自然的《边城》是一脉相承的。
二、诗意的散文化小说
汪曾祺小说创作数量不多,却以其清新淡泊,平实耐读的散文化笔法给长期以来小说单一的审美定势带来强烈的冲击。汪曾祺的创作开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汪曾祺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坛一位上承京派下启寻根的具有文学史意义的著名短篇小说家。
汪曾祺的小说被称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其表现特点如下:
首先,缺失戏剧冲突的诗意的小说。汪曾祺的小说追求诗的意境。小说情节因素很弱,较少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性。《受戒》中明海和小英子的初恋,没有波澜起伏的曲折戏剧,作者着力表现了其健康明朗的诗意状态,写的含蓄节制,意趣盎然。如“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正是作者擅长的富于诗意情趣的细节描写,这使得整篇小说虚实相间,清逸朦胧,意境悠扬。
汪曾祺认为散文化小说就是抒情诗,他多次自称为“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受戒》具有清新浓郁的诗意之美,它没有重大的题材,没有剧烈的冲突,没有戏剧性的无巧不成书,有的只是对于生活的凝视,对于人性的张扬,像一股清泉,细柔无声地滋润着读者的心田。
其次,缺乏完整故事的生活流小说。传统的小说依靠人物来展开情节,追求故事的完整性,有一个连贯的引人入胜的一环扣一环的故事。而汪曾祺的小说不同,缺乏完整的故事,常常如同一段生活流,通篇没有一个连贯的故事。汪曾祺说:散文化的小说“只是平平静静,慢慢向前流”。《受戒》没有一个集中的故事情节,不像一篇真正的小说,更像一篇散文。小说的一开头写荸荠庵,引出出家的明海,当地与和尚有关的风俗,明海出家的过程,荸荠庵的生活方式,小英子一家的生活状态,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至于标题所说的“受戒”,直到小说的最后才出现,而且还是通过小英子的视角来写的。《受戒》的叙述就是自然如水的流淌。整个故事不拘一格,浑然天成。
《受戒》的生活流描写,表面上看起来是无拘无序,实际上却潜藏着一种内在的秩序,所有的纵横枝节和横生的插叙都暗含着这种内在的秩序,读者读到结尾,甚至是最后一行字,也许才恍然有所悟。
汪曾祺说他的小说的“散”是有意为之的。汪曾祺是一位自觉的清醒的文体家。《受戒》是他博采众长,打通诗歌、散文和小说界限,使用生活流手法,貌似信马由缰,实则富于诗意,内蕴丰富,韵味悠长的成功之作。
三、精彩赏析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
一九八○年八月十二日,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是《受戒》的结尾。“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是点睛之笔,是作者心迹的表白。结尾表面是景物的描写,实际上是写人物。“芦花才吐新穗”是明海与小英子的朦胧爱情的写照。“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的芦穗,是两个少男少女情意绵绵美好恋情的曲折描绘。水鸟“扑鲁鲁鲁飞远了”是心情的放飞。这些景物实际上是在艺术曲笔地歌颂生命的灵动和青春的活力,歌颂明海与小英子纯洁美好自由的爱情。作者用诗意含蓄的语言为读者描画了一幅江南水乡清新水墨画,谱成了一曲赞美健康美好宁静的人性牧歌,荡漾着一个四十三年前的理想之梦。
附:相关评论
1.读了高中二年级,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危急。我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在庵里大概住了半年。我在《受戒》里写了和尚的生活。这篇作品引起注意,不少人问我当过和尚没有。我没有当过和尚。在这座小庵里我除了带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人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父亲也看了沈从文的小说,说:“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
我的小说也有人说是不像小说,其来由此。
我的小说似乎不讲究结构。我在一篇谈小说的短文中,说结构的原则是:随便。有一位年龄略低我的作家每谈小说,必谈结构的重要。他说:“我讲了一辈子结构,你却说:随便!”我后来在谈结构的前面加了一句话:“苦心经营的随便。”他同意了。人不喜欢结构痕迹太露的小说,如莫泊桑,如欧。亨利。我倾向“为文无法”,即无定法。我很向往苏轼所说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我的小说在国内被称为“散文化”的小说。我以为散文化是世界短篇小说发展的一种(不是唯一的)趋势。
汪曾祺:《自报家门》,载《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2.相当有趣的是叙述者对于“荸荠庵”这个名称的解释。这个庵本来叫菩提庵,是富于佛教意味的,但“俗人”们把它叫讹了,叫成了荸荠庵。这一讹称很具隐喻涵义,它代表着一种民间化的、世俗化的“阐释”(对佛教的解读)。
庵里的和尚也接受了这种“俗称”。
这实际上是对于自己宗教信仰的一种有意的“省略”或“忘怀”。
“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是俗人约定俗成的想法,可是“荸荠庵”住的却是和尚。这一看似荒谬的事实说明这里的和尚对于名分、形式是看轻的。而当地的人们,也对此习以为常,这正好印证了和尚的俗人化与宗教的世俗化。这些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读者阅读期待中和尚与佛教的神秘性与神圣性。
李朝全:《〈受戒〉赏析》,载汪曾祺之友网,2009年 2月 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