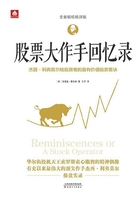我命马骅返回上党郡潞安,吩咐他们继续监视并等待机会,不要轻举妄动,我会想办法为他们制造机会。如果他们得隙进入冯小怜的小佛堂和卧房搜查,不但要找出她身后是否还有黑手的线索,还要找到赵蒙恩的“命根子”。同时我还吩咐小末去了解养鸽子的事宜,如果可行就找个行家里手来开始为我筹建“通信班”。
近乎软禁的日子还在持续,从外面打听回来的消息中可以感觉到整个朝野上下都在紧张压抑的气氛中等待着什么。这个消息终于在狩猎回宫后的第十五天传来了:突厥大军悉数北归。我松了口气,而小末从外面打探回来的情况看,朝臣们却没有松气的迹象,他们等待的似乎并不是这个消息,或者说这个消息只是那个被等待消息的前兆。
当天下午,那个朝野上下怀着不同心态等待着的事情终于被证实了:赵王、陈王、越王、代王、滕王将被解职并赶出京城,遣回封地。历史原有的轨迹还在继续。
“赵蒙恩确实说父皇已经下旨了?”我问
小末肯定地说:“是啊,主上,他说诏书已经拟定,太上皇已经用玺了,明天就要颁布了。”
“诏书上具体怎么写的?”
“他只跟奴才讲了一下大意,就说五个王爷劳苦功高,是宗室社稷的光荣,为了旌表,扩充了他们的封地并册立为国,以洺州襄国郡为赵国,以齐州济南郡为陈国,以丰州武当、安富二郡为越国,以潞州上党郡为代国,以荆州新野郡为滕国,各封食邑一万户,请他们各自归国,拱卫大周江山并颐养天年。”
燕骏接口道:“五个王爷都还不到四十岁,正值盛年,就颐养天年了?”
小末白了他一眼说:“赵蒙恩说诏书上是这么写的,又不是我说的。”
我微笑说:“这些都是托词,明发的诏书上几乎从来不会写出真实的动机,就算有也不会是全部。”
“赵蒙恩虽然没有说,但奴才想,太上皇必然是怀疑猎场行刺的元凶在五王之中。”小末说。
我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何况父皇对那五位王爷的疑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燕骏点着头说:“太上皇借此机会解除了他们手上的实权,虽保留王爵还分别封国,其实明摆着就是将他们遣回封地圈禁起来,也同时把他们都给隔离了。”
我终于明白朝野上下在等待什么了,他们在等待谋刺案最终的处理结果。此前出台的责罚和封赏不过是序曲,有没有查出元凶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根导火索最终引爆的会是什么。之所以要等到突厥撤兵的消息传来之后才发作,显然是顾虑到沙钵略可汗万一不按预料的就坡下驴,而是挥戈南下。宇文赟也不敢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与五王翻脸,否则很有可能造成内乱与外患并发。一旦处置五王的诏令在突厥撤兵前发出,滕王就可能借大敌当前为由拒不交出兵权,甚至有可能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军事政变,南陈再趁势而动,天下顷刻间就会大乱,北周立即就会被推到生死存亡的边缘。
由此看来,宇文赟并不是一个极端弱智的皇帝,他和他的势力集团还是有着不可低估的权谋和实力。但历史证明了他自撤藩篱却为杨坚主政铺平了道路,而我现在还势单力孤,无力阻止历史的车轮在老路上继续前进,想到这里我就毛骨悚然,那意味着两年后的那把利刃仍旧朝着我的脖颈一步一步地逼近。
随着五王封国归国的诏令颁布,我被“囚禁”的日子也就结束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但敏学斋里少了三位帝师,只剩下了毕王宇文贤。因为他是明帝的儿子,是宇文赟的堂兄,显然没有足够的势力,构不成对宇文赟的威胁。
恢复正常秩序后我第一次去天台请安,赵蒙恩恭恭敬敬地领我进去了,宇文赟肯定有什么话要跟我说,我也想听听他要说些什么。
宇文赟的精神看上去很好,两撇胡子似乎也格外的上翘了,他笑着问我:“衍儿啊,这段日子不好过吧?你在正阳宫都做了些什么啊?”
“回父皇,儿臣一直在学习本朝的官制、法典。”
宇文赟深深点头说:“嗯嗯!其实父皇都知道啦!此次狩猎时就发觉你似乎心智变得成熟了,少年老成,言行已颇有乃祖武帝的风范。这些天又听说你详读我朝律令典制,天心甚慰啊。足见父皇早早禅位于你可谓英明。”
我敷衍道:“儿臣年幼无知,社稷之重还要仰赖父皇,儿臣惟愿日夜苦读,以尽早为父皇分忧。”
“嗯,不仅要在典籍文牍中学习,也要身体力行多加历练。前次你随父皇巡幸东京时还无甚表现,而此次狩猎就已大有长进,尤其是为你姑姑、燕骏等求情,就颇为得体。同父皇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可谓恩威并施,显示了天家的气派。”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纯属牵强附会,竟有拿我的言行给他脸上贴金之嫌,我心里暗骂。
他接着说:“待五位叔王各自归国后,父皇准备再带你外出巡视,多见一些地方大员,既是对你的历练,也是让朝廷上下和万千子民认识你这个少年天子,树立起你的威望。”
这到是我求之不得的,但宇文赟虽然说得冠冕堂皇,其实他的真实想法一望而知:威胁到他的王爷们都被料理了,他可以无所顾忌地游山玩水、纵情淫乐了。外出巡游就可以秘密招幸冯小怜,这也是他热衷于巡幸的重要原因。想到这里我忽然心念电闪,生出一计。
我点头说:“父皇所言甚是,儿臣确实应该尽快熟悉朝廷大员并了解大周各地情况。不过这次巡幸儿臣以为父皇不可亲往。”
“何出此言?”
“父皇,请先回答儿臣一个问题。”
“呵呵,你在打什么鬼主意?问吧。”
“儿臣想问父皇,您认为猎场谋刺的始作俑者是不是在五王之中?”
宇文赟盯着我看了半天,说:“衍儿真是聪慧过人,其实这些也不必瞒你,并非父皇对族亲叔王们不信任,实在是为了我大周江山万年永固啊。你皇祖临终时欲传位于我,而叔王们却鼓动朝臣阻我继位,对皇位的觊觎之心昭然若揭。其实这都是当年你皇祖与他的两位兄长相继为帝的缘故啊,使这些叔王们产生了非分之想。你皇祖乃一代雄主,尚有卫王谋逆,待他殡天,那些叔王们的狼子野心还如何按捺得住啊?你皇祖仁德,虽传位于我却并没有对他的兄弟们稍加敲打和贬抑,可这却给父皇出了一道难题啊。叔王们权倾朝野又步步紧逼,父皇万般无奈才杀了为首的齐王,才暂时阻住了他们的篡逆之图。父皇虽然苦心经营,重用了蹹拔穆、普六茹坚等一班忠臣,也敬叔王们是长辈,没有过分为难,望他们能念在宗族一室的份上抛弃异志,与我同心协力。奈何他们贼心不死,竟联合起来逼父皇对突厥和南陈用兵,他们手握军政大权,企图制造出危局,父皇就不得不依赖他们,使他们的权势更重,便可寻机谋逆啊。”
“哦,难怪在朝会上父皇不支持主战派。”
“唉,是啊,幸亏有蹹拔穆这样的社稷干城,没有让他们得逞。谁料他们竟因此丧心病狂,意欲行刺我们父子,这实在太令人齿寒了。父皇已做到仁至义尽,被他们逼到这个份上,只好将他们大发回国了,都还是给他们留着很大的体面,毕竟是一家人嘛,唉……”宇文赟一脸无可奈何状。
“父皇,儿臣以为这也不能确定是他们或他们中的某一人谋刺了父皇和儿臣啊。”
“衍儿啊,你还是太年幼了,不知道宫廷的凶险。父皇于狩猎前一天才下令准备狩猎,第二天上午还召开了紧急朝会,若不是拿出了不战不和的良策,狩猎也就作罢了。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不是朝中大臣又如何会知道狩猎之事?能在一两日之内就派出刺客并能成功潜伏在猎场的人又能是什么人?这是其一。我们父子被害,谁又将是最大的受益者?大周是我宇文家族的天下,有那么多位高权重的王爷在,别的什么臣子谋刺我们等于为王爷们做嫁衣,谁会那么傻?这是其二。”
他的分析不无道理,我点点头问:“儿臣还有两个弟弟呢,如果我们被害,他们可以继承大统啊。”
宇文赟大摇其头:“你的两个弟弟都还太小了,即便被扶上皇位,那必定也是傀儡啊,大权必然尽数落到那些王爷们手里,他们迟早都会重演王莽篡汉的那一幕啊。”
我心想:等你死后,我就会成为傀儡皇帝,而杨坚就会变成王莽。
宇文赟见我不说话,就问道:“父皇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你说说为什么父皇不应外出巡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