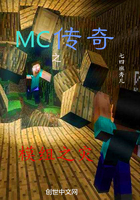天台御极殿里早已摆上了丰盛的婚庆酒宴,入席的官员们都脱去了厚重的朝服,一律便装与宴。按规矩,并不是所有前来朝贺的官员都有资格吃上这喜宴喝上这喜酒的。只有在外从八命以上、在京从七命以上的官员和皇室的近枝宗亲、各国使臣有资格参加宴会,此外就只有皇后的娘家人和少数特许的人员可以参与。而在这少数特许人员中,就有宇文温、尉迟炽繁小两口。宇文温虽也算皇室宗族,却系旁枝,他是太祖皇帝宇文泰兄长宇文颢的曾孙,血缘关系已经很远了,按理并无资格参加,却被宇文赟口谕特许了。对此当然就有不少无缘喜宴的官员就不免私下议论,有的认为是因宇文温的父亲宇文亮正在淮南作战,为了表示激励和嘉许因而特许;而有的则认为还是托了尉迟炽繁她爷爷蜀国公尉迟迥的福,四辅官多次调整,唯一始终稳如泰山的只有尉迟迥,可见圣眷不衰。
宇文衍和司马令姬同席坐在了天元皇帝的左侧,右侧就坐的是阿史那朵、杨丽华、朱满月和陈月仪,李娥姿太后和大着肚子的元乐尚已然回各自的寝宫休息去了。殿内已坐得满满当当,只在大门与天元皇帝的主席之间留出了两丈宽的狭长空地,做歌舞表演之用。
宇文赟做了简短致辞之后,全体起立举起了酒杯为小皇帝夫妇新婚大喜祝酒,一番琴瑟和谐、天地同庆、江山永固的祝福之后,宴会正是开始。最近一段时间闭门造车苦苦编排新舞的冯风拿出了他的新节目《盛世乾坤》,他领唱领舞,十余个天台乐坊的舞女伴舞,在长袖翻飞中且歌且舞,倒也非常的喜庆精彩。
一曲既罢,热得快的官员们便开始离席敬酒了,当然无一例外的是从天元皇帝开始,敬完太上皇夫妇,再敬小皇帝夫妇,宇文衍和司马令姬不能饮酒便以乳酪代替。向皇帝敬酒之后,官员们便可以相互敬酒了。不出意料,赵王、越王、代王、滕王的席前冷冷清清,只有些孤高自恃的大臣去与他们敬酒,如太史庾季才、大辞赋家庾信之流。反观四大辅臣的席前则是络绎不绝热闹非凡,新国丈司马消难自然是最受热捧,官员们排着队的前来敬酒道贺,令他简直应接不暇。新迁四辅的韩建业也颇受欢迎,他也显得十分兴奋,来者不拒举杯豪饮。而一旁尉迟迥的席前则被特许入席的郑译、王端、刘昉等几个太上皇跟前的幸臣团团围住,似乎不约而同地要给这位老爷子献殷勤。尉迟迥生性豪迈,也没多想,跟他们几个说笑着也是连连饮杯。到是首辅杨坚夫妇的席前相对安静些,虽也都来敬酒,但并不热闹喧哗,可能是碍于杨坚不苟言笑的性格。
宇文衍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在司马令姬耳边低声说:“就要有好戏看了。”
令姬不解,嚼着鱼脍不清不楚地问道:“啥好戏?”
宇文衍说:“你看郑译他们几个围着尉迟迥畅饮,那是在为太上皇打掩护呢。”
“打什么掩护啊?”
“你还不知道吧,咱们这位太上皇的第五位皇后也在下面坐着呢,他让郑译他们几个心腹引开尉迟迥的注意力,最好能把尉迟老爷子给灌醉了,好掩护他下去灌醉尉迟老爷子的孙女呢。”
“什么?你说尉迟炽繁?太上皇看上她了?”
“前不久宇文温和尉迟炽繁新婚来宫里谢恩时就被瞄上了,史书也明确记载了尉迟炽繁被天元皇帝灌醉强奸……”
“啊!天哪!瞧瞧你摊上个什么样的老爸!真是荒淫无耻到了极点!你也不管管?”司马令姬愤愤不平地说。
“这会儿没法跟你详谈,总之你记住了,太上皇作孽咱还真不能管,就要让他自取灭亡,咱们当家作主的那一天才能尽快到来。”
司马令姬露出了不忍的神色:“可炽繁她……他们小两口也曾到司马府拜谢过,我觉得她好漂亮,当时还想怎么没穿越到她身上呢……”
宇文衍乐了:“呵呵,若是你附在了她的身上,从宇文温手里横刀夺爱的就轮不到太上皇了,我就第一个出手了!”
令姬听了先是高兴,随即又柳眉倒竖,嗔道:“你该不是为了她更加美貌吧?”
宇文衍顿时翻起白眼做晕厥状:“我说你有完没完啊?刚才为司马令姬争吃醋,现在又跟尉迟炽繁争风,穿越那么久了,你还精神分裂哪?”
令姬一笑,不置可否,继续大嚼那个年代的生鱼片——鱼哙。
新的歌舞又开始表演了,是亢奋激烈的胡风舞,加之此时已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殿内的气氛也更加放松和热烈了。只见宇文赟端着酒杯起身离席,先是对四辅臣举杯致意,却只轻轻呷了一口酒。他走过四位叔王席前时,坐在代王宇文达身边的冯小怜似有意似无意地扬起了脸,用一双妙目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然而宇文赟只朝这边撇了一眼,不但对四王毫无表示,对冯小怜更是视若不见,径自走了过去。这令冯小怜如当头淋了一桶冰水,脸色都变了。而此时宇文达正转过头来看她,她只能急忙用罗帕擦嘴掩饰过去,然而眼睛的余光仍旧追着宇文赟的身影。
胡人好酒,酒后便大多会将汉化的面具丢到一边,只知道率性狂欢了。宇文赟就是在这样的喧闹中穿行在群臣门的席案之间,看似兴致颇高的随意跟这个碰碰杯、跟那个打个哈哈,很平易近人的样子,弄得被光顾的大臣和夫人们都有点受宠若惊。其实宇文赟曲折前进的目标是在大殿的东南角,殿中一干或微醺或酩酊的大臣们谁都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太上皇正走向宇文温和尉迟炽繁的坐席,冯小怜却看得清清楚楚,视线已率先落到了尉迟炽繁的脸上,冒出了刻毒的寒光。
宇文温和尉迟炽繁小两口正跪直了伸长脖子看前面的歌舞表演了,喧闹中毫不留神身着便装的宇文赟已经到了他们面前,待看清楚不由大吃一惊,急忙诚惶诚恐地拜了下去。
宇文赟很随便地坐了下来,笑道:“免礼吧,今日是小皇帝的大喜之日,你们俩也刚新婚燕尔,天特来跟你们喝一杯,同庆同喜!”
宇文温赶忙用双手端起了自己的酒杯,宇文赟却看着尉迟炽繁问:“你的酒呢?”
尉迟炽繁十分紧张不敢说话,只好看自己的丈夫,宇文温忙代答道:“天元大皇帝陛下恕罪,贱内不会饮酒,由微臣代她敬大皇帝陛下吧。”
宇文赟始终就没看宇文温一眼,眼睛没有离开尉迟炽繁的脸,摇头道:“不行不行,咱们鲜卑女子怎能不饮酒?何况今日这是小皇帝的喜酒,必须饮!”
宇文温也不敢坚持,只好示意尉迟炽繁端起酒杯。尉迟炽繁看看宇文赟又看看自己的丈夫,终不敢违拗勉强端起了自己面前的酒杯。
宇文赟点点头道:“嗯,很好,干杯!”说罢举杯与她们两人的杯子一碰,仰脖一饮而尽。宇文温跟着饮尽了杯中酒,尉迟炽繁却只抿了一口就愁眉喝不下去了。宇文赟见状将脸一沉,道:“怎么?!是这小皇帝的喜酒不好喝,还是天特来与你们同庆同喜的面子还不够大?”
尉迟炽繁待要求情,宇文温却已先慌了,忙用胳膊碰碰妻子道:“赶快喝了吧,这……这可是大皇帝陛下的隆恩啊。”
尉迟炽繁委屈地看了懦弱的丈夫一眼,只好咬牙将一杯酒灌入了腹中,立时被呛得剧烈咳嗽起来,一张俏脸也涨得通红。
远处主席的侧案前,刚刚下去给大臣夫人们敬酒回来的陈月仪坐到了杨丽华身边,低声在她耳边说:“丽华姐姐,太上皇他竟去挑逗小尉迟去了。”
杨丽华并未做出什么反应,只是抬眼朝大殿的东南角看了一眼,默不作声。一边的朱满月却说话了:“月仪妹子啊,这种事还是不要知道的好,咱们能保自身平安就已是福大了。”
“可那是蜀国公的孙女、淮南行军总管的儿媳啊,又在大庭广众之下……”陈月仪还不依不饶地说着。
杨丽华终于低声喝道:“住口!别说了!”喝罢不无尴尬地瞟了一眼旁边的太后阿史那朵。阿史那朵喝了一口酒,仿佛自言自语道:“当年先帝的心也不在我身上啊……”
杨丽华也跟着喝了一口酒,眼圈发红,低声叹道:“那是因为先帝的心在天下百姓的身上。”
阿史那朵点点头,感慨道:“嗯,我比你幸运。”
此时,在大殿的东南角,出生至今首次饮酒的尉迟炽繁已然醉态尽显,只觉得心慌气短天旋地转,她无力地靠在了宇文温肩上,含含糊糊说:“我们……回家……”话没说完就彻底晕厥过去了。宇文温见状又是心疼又是尴尬,一边抱住妻子的身体,一边慌乱地对宇文赟说:“大皇帝陛下恕罪,贱内……她实在不能饮酒,君前失仪,罪……罪该万死。臣请先行告退,在家中等……等候处分……”
宇文赟笑着摆摆手,显得颇为大度地说:“无罪无罪,你看她醉成这样,且令侍女扶到暖阁,喝一碗御医配置的醒酒汤,休息休息再走不迟。”说着就向侍宴的婢女招手。
宇文温感激涕零地谢罪谢恩,便欲起身扶着妻子一同去暖阁,谁知宇文赟却道:“咱鲜卑大丈夫怎能如此儿女情长?你留下来继续饮酒,夫人由侍女们照料就行了。”
宇文温闻言,不敢违命,只好放开娇妻滚烫却无力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