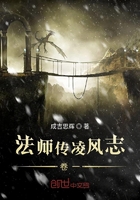建康城,皇宫北书房,一个两鬓斑白的男人身着朴素的白袍负手站立在窗前,眺望着烟波浩渺的北湖。虽已深秋,长江之南依旧满目葱翠,风和日丽,鳞光万点的北湖祥和得可以令人心醉。但此人并不是在欣赏风景,他的心头更不祥和,紧锁的眉头和游移不定的眼神表明,他此刻正在思考大事,非常棘手的大事。此人就是南陈当今皇帝陈顼,年已五十有二,在位十年了。
陈顼是南陈开国之君高祖武皇帝陈霸先的侄儿,世宗文皇帝陈蒨的弟弟,原本是南陈第三任皇帝其侄儿陈伯宗的辅政大臣。十年前,有大臣意欲削弱甚至谋夺陈顼的辅政大权,陈顼察觉,先发制人,镇压了反对他的势力。本就志向远大的他并未就此罢手,认为是侄儿皇帝要夺他的权,便一不做二不休篡夺了皇位,成为南陈第四任皇帝。
陈顼继位以来,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励精图治,强兵富民。趁周齐交兵组织北伐,重夺了淮南大片沃土,一度开创南陈最兴盛的时期,称得上是一位有为的明君。但自从第三次北伐精锐尽没,名将吴明彻被俘之后,他受到沉重打击,自觉有些力不从心了。为国殚精竭虑的他也已年过半百,身心开始疲惫了,忧虑和烦恼也接二连三地袭来。
此刻让他深感烦忧的就有两件事,而且是极其严重的大事。
一件便是北周军队已大兵压境,去年他虽成功组织抵御了北周滕王为帅的南侵,但现在他却对韦孝宽与梁士彦联袂指挥的攻势严重缺乏抵御的信心。遍观本朝,已无精锐之师更无可用之将,自己辛辛苦苦组织北伐夺来的淮南之地已危在旦夕了。为此他深悔自己前不久在北湖和长江瓜步阅兵耀武的行为,他以为北周天元皇帝宇文赟昏庸无能,必会被自己诈称十万的新军和数百战舰所震慑,短期内不敢出兵来犯,让自己能争取到将新军继续扩充并训练成精锐的时间。但是他错了,昏庸的宇文赟居然像识破了他的虚张声势,不退反进,兴兵南下了。唉,也许不搞大阅兵还不至于惹火烧身啊。
另一件便是北周陈王宇文纯的突然到来,他声称自己饱受昏君迫害,已与北周朝廷决裂,愿投效南陈,帮助抵御韦孝宽的南下大军。宇文纯身为老一代的北周亲王,投奔过来自然不可能是配合韦孝宽军事行动的卧底,并且此前宇文纯就已派萧四郎前来暗通款曲,有意助陈抗周。这一点虽无顾虑,但陈顼却有更深一层的担心。他不须旁人提醒就想起了侯景之乱和前朝南梁的命运。侯景原效力东魏及北齐,因拥兵自重不容于北齐朝廷,率众投靠了南梁,梁武帝贪图侯景的地盘和军队,不顾众臣的反对,接纳了侯景,封以高官显爵,还出兵援救于他。结果如何呢?侯景一反再反,后来竟策动梁武帝的侄子里应外合攻陷了建康逼死了梁武帝。蜂虿有毒,豺狼反噬,前车之鉴犹在眼前啊,陈顼怎能不心怀惴惴?
尤其麻烦的是,这两件事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若没有韦孝宽的大兵压境,便无须考虑对宇文纯的应对方式,即便收留了他也只是虚名相待束之高阁而已。若没有宇文纯这个来自敌方的百战之将相助,又对韦孝宽的攻势一筹莫展,忍看坐失江北沃土吗?利用宇文纯化解国家当前的危局,便不可避免地让宇文纯建立起地位和势力,只恐将来变成尾大难掉之势,外患改内忧,心腹、肘腋之间的祸乱,只恐国祚危矣。
若在十年前,甚或只是五年前,陈顼必然有绝对的自信控制和驾驭宇文纯,既利用了他对付来犯之敌,又不至于令其坐大无法收拾。可如今,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越来越虚弱的身体,让他豪气不再,信心衰减。吴明彻的全军覆没不但严重打击了他,也改变了他的用人方式。他不再敢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之后朝中再无可以令他委以重任的大臣。其实并非没有可用之才,而是越老的人也越没有安全感。陈顼既害怕将大军委于一人,此人闪失则全军尽没;他也害怕身体变得衰弱的自己一旦撒手人寰,他那个整日价只知道花前月下、吟诗作赋的太子陈叔宝根本无力驾驭重兵在手的权臣。
在陈顼的内心深处无时无刻都不会忘记自己叔父陈霸先是如何建立南陈的。陈霸先不过是寒门出身,要不是在侯景之乱时被委以重任,一路平叛越打越大、越打越强,最终凌驾于南梁朝廷之上,又何来南陈代梁自立的一天?陈顼当然不能不惧怕这样的历史再在他的子孙身上重演。
“陛下,始兴王殿下和尚书仆射陆大人到了,在门外候见。”常侍的一声禀告打断了陈顼一筹莫展的沉思。
陈顼回过身来,用略微有些嘶哑的声音说:“请他们进来吧。”
不一时,一个英武的年轻人和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快步走进了北书房,他们就是始兴王陈叔陵和尚书仆射陆缮。
陈叔陵是陈顼的次子,年仅二十五岁,从小就机智勇武,因骁勇善战,十六岁时便被封为都督,统领江、郢、晋三州诸军事,就开始独当一面。十八岁时又被升迁为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诸军事,平南将军。去年又得授扬州刺史,都督扬、徐、东扬、南豫四州诸军事,已俨然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宠儿,风头大大超越了他的哥哥太子陈叔宝。
陆缮,一个年过六旬却还精神矍铄的老人,现居尚书仆射,虽二品之职,却是陈顼目前最为信赖人之一。他与始兴王陈叔陵隐隐然便是当今南陈皇帝的左右手,陈顼但有难决的大事要事,没有不请他们出谋划策的。
二人施礼后照例赐座,陈顼待二人坐下,踱步来到他们中间,眉头深锁,声音暗哑地说:“稍后宇文纯便要再次觐见了,朕想再先听听你们的意见,用宇文纯来协助抵御北周大军,究竟妥或不妥,利弊如何?”
昂然而坐的陈叔陵眉毛一挑,朗声道:“父皇,此事毋庸再议了。儿臣前日便已表明了态度,这宇文纯来得蹊跷,又未携家眷,居心叵测,万不可收留,更不要说启用他了。不若将其绳捆索绑押送到长安,那宇文赟见逆贼就缚,没准就此罢了韦孝宽南下之兵,我朝或可因此避免一场刀兵之灾。”
陈顼听了他的话,没有表态,依旧眉心紧锁,沉吟一会,将目光移向了正襟危坐的陆缮。
陆缮用手轻轻捋着自己银白的长须,缓缓道:“臣以为,齐亡之后,陈周之盟便已名存实亡,再存着与周划江而治永为睦邻的念想已经太不现实了。周武帝驾崩之后,周师南侵之势已愈演愈烈,两国已到了势同水火不同戴天的地步……”
陈叔陵有点不耐烦地翻着白眼插嘴道:“陆大人,你绕那么大圈子干嘛?直接说吧,你考虑了两天究竟是个什么主张。”
陆缮也不以为意,点点头继续说道:“两国既然已是你死我活不可共存的局面,委曲求全绝不是长久之计。江北之地一旦尽失,休要说再图北伐了,便是倚江自守也是难以为继了啊。故而,臣反复斟酌,认为应该抓住宇文纯投靠的机会,利用他保住淮南江北之地,才是守住了我朝与北周一争天下的最后一线希望呀!”
陈顼还没说话,陈叔陵又抢着大声说:“谁说我们自己就守不住淮南江北之地了?照陆大人的说法,我朝的命运还掌握在一个叛逃过来的落魄亲王手里了?这不是视本朝无人嘛!”
陈顼沉下脸来呼喝着陈叔陵的字,道:“子嵩,怎可这样同仆射大人说话!目无尊长!”
陆缮微微一笑似乎毫不介意,对陈叔陵说:“殿下啊,这韦孝宽的大军又不是因为宇文纯的叛逃而发的问罪之师,他们绝对不会因为我们绑缚宇文纯送交长安而罢兵的。而宇文纯其人,身经百战,素有武略,又谙熟周师内情,引以为援对抗周师,不仅可解燃眉之急,还能保有南朝长存之望啊。”
陈叔陵又要争辩,被陈顼摆手阻止了。陈顼则沉吟道:“可是士繻啊,卿忘记了侯景之乱吗?侯景投梁,名曰为梁谋夺北齐之地、对抗北齐之师,其结果呢?梁师不仅惨遭败绩,梁武帝还遭侯景反噬,终至萧氏国破家亡。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卿不虑宇文纯会是第二个侯景吗?”
陆缮笑了,从容道:“陛下多虑了,这宇文纯与侯景有三不可比。其一,侯景叛齐在先,北齐兴师问罪于后,南梁接纳侯景便是引火烧身。而宇文纯则不同,周师兴不义之兵于前,宇文纯弃暗投明在后,我朝接纳正为抗拒北周不义之师。道义天理之向背不同也。其二,侯景之乱时周、齐、梁三国并立,且均参与其中,形势远为复杂,致梁武帝难以控制,实非得已。反观今日,陈周两国而已,情势相较于侯景之乱时简单明了多矣,以我主英明,何虑不可驾驭?其三,侯景投梁时带甲数万,虽遭北齐重创,仍余八千精锐,纳其入梁等同于引狼入室。宇文纯呢?仓皇来投,不及二百亲兵相随,势弱力单,陛下何虑之有?”
听了陆缮的分析,陈顼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了,他还未表态,这时常侍进来禀报:“陛下,周陈王宇文纯到了,在外候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