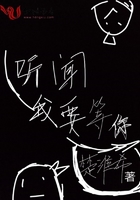北周朝廷为此次淮南之战集结了近十万大军,志在必胜。经行军元帅韦孝宽的部署,行军总管宇文亮率领三万歩骑为西路军,先行出发,自己则与梁士彦率主力五万余为东路军,迟于西路军十日后出发,另外还留了万余留守彭城,作为预备部队。
发动此战的目的在于攻城掠地、开疆拓土,将南陈势力尽数压缩到长江南岸去,所以在战术安排上以步骑和攻城兵为主,尽量避免水战。南陈的精锐水师和名将吴彻明虽已在两年前遭前任徐州总管王轨全歼,但南陈的水战能力依然不可小觑。韦孝宽深知南陈在瓜步阅兵的十万大军虽是诈称,但其新建成的五百艘巨舰却丝毫不假。己方善马步战,不善水战,所以必须扬长避短,若遇敌方水军,能避则避,不能避也只能借秋去冬来的北风,用火箭退敌,不准备以船战船。
韦孝宽尽量深入浅出地向宇文衍讲述了自己的作战计划,宇文衍不懂军事,自然是无不认同,更何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战场上瞬息万变,做君主的只需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就足够了。临行前宇文衍让韦孝宽也带上了几只信鸽,叮嘱他常常通报战况,自己在长安静候凯旋的消息。
韦孝宽的主力大军开拔后,完成了拜帅、劳军、誓师任务的小皇帝一行也踏上了西归长安的旅途。也不知是想着将要大胜南陈尽收江北之地的振奋之情,还是回到长安就可以名正言顺迎娶司马令姬为后的兴奋,宇文衍一直处于莫名的亢奋之中。他在暖和的龙撵车厢内,趴在巨大的淮南战事地图上,借着长江做参照物,回忆着、对应寻找着与一千多年后全然不同的地名。
一旁的司马泳却显得异乎寻常的冷静,甚至是有那么一点忧心忡忡的样子。
宇文衍看地图看累了,直起身来看了一会车窗外愈发萧索的秋色。从彭城西去之路也在北上,虽才走了三天,就已能明显感觉到更为深浓的秋意,阔叶林随时都在风中抖落着枯黄的叶片,铺满黄叶的道路只有在午后的阳光下才能释放出些许回光返照般的暖意。
看了一会,宇文衍放下窗帘,回头见司马泳又锁着眉若有所思,便问道:“先生,这两日朕见你老是心事重重的样子,在想什么呢?”
司马泳太过入神,竟完全没有听到小皇帝在跟他说话,一旁的小末连忙捅了捅他,提醒道:“主上问你话呢。”
司马泳回过神来,忙欠身告罪道:“陛下恕罪,臣方才走神,未曾听到陛下说话。”
宇文衍不以为意,又问:“这两天你在想什么啊?”
司马泳沉吟了一下才说:“臣……臣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不祥?!”宇文衍立时严肃起来。
“哦,陛下不必紧张,臣的不祥之感并非指淮南之战。淮南之战有韦老将军指挥,又合天时地利,毫无悬念,胜利指日可待,万无一失。”
宇文衍听了心下一宽,便也更加好奇,问道:“那先生预感何事不祥啊?”
司马泳再次沉吟,过了一会才说:“臣觉得邢炳义的纸条案处置得似有不妥。”
“哦?有何不妥?”
“这个……臣也说不上来,只是有一种不太好的感觉……”
“当时韦老将军建议放走邢炳义,并令其如实回报陈王,先生怎未当面提出异议?”
司马泳脸上红了红,躬身道:“韦老将军的提议行的是堂堂王道,光明正大,臣又没有其他具体的处置思路,实不便提出异议。”
宇文衍低头想了想,点了点头感慨道:“是啊,诸位叔祖亲王个个人才了得,若真能知其雄而守其雌,堪为大周最坚实的柱石啊,如此大周幸甚!”
司马泳点点头,微微皱眉道:“话虽如此,怕只怕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臣也不知韦夐先生的规劝因何而发,但总隐隐担心……”
“担心什么?”
“陈王不知道陛下也看到了纸条也就罢了,担心的是陈王如何揣测陛下看了纸条后想法。他会不会将坦诚的点醒理解为最后的通牒呢?”
“最后通牒?”宇文衍若有所悟,“除非……除非他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但他会怎么做呢?难道会造反吗?”
司马泳摇摇头:“这也正是臣未曾想透之处啊……正如陛下所言,关键要看陈王此前已经做了什么,做到了哪一步,这是影响他对纸条案做出何等反应的关键。可是目前,臣除了推断其策划了两次假行刺意欲独宠晋身外,并不知悉陈王还有什么图谋和行动。”
宇文衍听了也锁紧眉头,喃喃道:“先生的意思是,若说者公义,听者怀私的话,堂堂王道之举反而有可能促其铤而走险……”
“陛下圣明!但愿韦夐先生只是杞人忧天似的劝人向善,但愿陈王并无二心从善如流。”
恰在此时,车外忽然传来了燕骏的声音:“陛下,长孙将军的前哨来报,陈王在前方驿站等候多时,求见陛下。”
宇文衍和司马泳立时大惊,瞪大了眼睛对望一时无语,小末也跪直了身子嘀咕道:“嘿!说曹操曹操到啊。”
宇文衍很快镇定下来,撩起窗帘做好奇状问道:“陈王求见?知道他有何事要见朕吗?”
燕骏回道:“据报称,陈王只说特来君前请罪,已在驿站大门外恭恭敬敬地立候多时了。”
司马泳来到窗前问道:“陈王带了多少人?”
“据说只有几个随从。”
“好,朕知道了。”宇文衍懒懒地说着放下了窗帘。
半个多时辰之后,宇文衍的车架来到了一处名为胡家集的小镇上。此镇已在豫州地界,有百十户人家,朝廷在此镇设有官方驿站,供传信驿卒歇脚换马之用。镇前有一条河,其上有一座木桥,桥的另一头就是镇子的牌楼,因年久失修,牌楼上“胡家集”三个字已斑驳难辨。驿站就紧挨着牌楼,几步之遥。此刻这个小镇已经被禁卫军彻底戒严,驿站内外也都被反复搜查过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地设满了禁军卫士。
宇文衍还没下车,隔河就看到了道边躬身侍立的陈王,不再是前番东郡黄河上救驾时那般神威凛凛的样子,而是身着亲王朝服斯文得甚至有点局促的陈王。陈王身后仅有两名侍卫和两名内侍早已跪伏在地,他们身后还跪着几个看服饰就知道是驿丞和驿卒的人。
一般来说,在设有官方驿站的小集镇上,驿丞就自然成了镇长。前两天这里的驿丞接到通知,小皇帝车马一行只会经过此地而不会停留,殊不知陈王忽然到来,并要在这里拜见小皇帝,结果小皇帝便要在此歇脚,弄得镇子上好一阵忙乱,他们受宠若惊又诚惶诚恐。
小皇帝一亮相,陈王立即俯身跪地大礼参拜:“臣宇文纯拜见皇帝陛下!”
宇文衍从车上下来立即热情地上前扶住宇文纯的双臂,大声道:“九叔祖何故如此啊?朕前番东巡有你保驾,此番西归又有你路迎,让朕好生感动啊!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宇文纯听了小皇帝这话似有弦外之音,眼角不经意地抽动了一下,但依旧恭敬地行完了叩拜大礼才站起身来。
侄孙和叔祖俩携手走进了简陋的驿站,驿站并不宽敞的院子里听着一辆两匹马拉的马车,想必就是陈王所乘的车辆了。
进入临时打扫布置出来的驿站会客厅,宇文衍坐了首席,司马泳、小末侍立左右,燕骏等四大侍卫两旁站立。宇文衍给陈王赐座,陈王却不坐,黝黑的脸上似乎有些黑里透红,他再次跪拜下去,看了看左右人等,不安地说:“陛下,臣特来请罪,不胜惶恐之至,陛下若念先帝武皇乃臣皇兄之情,敢请屏退左右,令臣稍存体面,臣感激涕零!”
宇文衍闻言侧头看了看司马泳,司马泳皱眉轻轻摇头,示意不要同意。宇文衍微微一笑,便对宇文纯道:“九叔祖说哪来话来?什么请罪不请罪的,你何罪之有啊?快起来坐下说话。”
宇文纯却依旧跪伏在地,看上去脸涨得更红了,抗声道:“陛下,臣有罪。既然陛下非要臣当着正阳宫诸位臣属的面说,臣便这样说就是了。”
宇文衍连忙说:“莫忙莫忙,既然九叔祖执意要请什么罪,朕岂可不为你稍存体面?”说罢就对司马泳、燕骏等人摆手,示意他们退下。
司马泳有点急了,但又不敢说话,只能用眼神极力表示反对,燕骏和小末看到司马泳的表情,也紧张地看着小皇帝,不知是否应该退下。
宇文衍非常从容自信地冲着司马泳笑了笑,大声道:“你等暂且退下吧!”
司马泳不得已,只好跟着燕骏、小末等人退出了厅堂。来到门外,燕骏看了看个个全神戒备的正阳宫侍卫和院外按剑而立的长孙晟及其禁卫军,困惑地小声问司马泳:“先生方才何故不愿退下啊?有何不妥吗?”
司马泳眉头紧锁,并未回答,似乎还在紧张地思考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