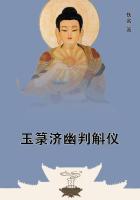“前面就是厕屋,公子快去快回。”脸绷了一路,小厮满脸不快地朝少年抬手一指。
一介布衣,谱儿摆得比官家子弟都还要大,真是让人讨厌。
少年忽而展唇,露出糯米白的一排贝齿,乌眸瞅着院桥处的几株云杉,感慨地低叹:“都这么高了。”
唇朱而齿白,模样秀丽,比养在闺阁中的少女也不遑多让。
或许是那一笑释放出了柔和之意,小厮心头一跳,鬼使神差地叮嘱了一句:“别乱跑。”
摄政王府防卫严密,便是府中下人也不得随意走动,暗处还有潜藏的暗卫,若是被人发现“心怀不轨”,那可是祸及身家性命的大事。
少年弯着唇角,稀薄的日光下容颜似乎透着白,他眸色极淡地瞥了眼小厮,就此转身。
好心没得谢,小厮立马又不爽起来,气哼哼地扭头,去欣赏远处走来的俏丽婢女去了,居然没发现,少年竟堂而皇之地避开了厕屋,消失在月洞门处。
烈一得了罗成的吩咐,暗中跟踪少年,见他这样轻易就甩开了小厮,抱着酒坛在王府里大摇大摆地,心里是又惊又奇。
少年选的路径不算偏僻,每每行走,十分“意外”地与路过的下人或侍卫错过,关键是他那副“久未回家满眼怀念”的样子是什么意思?
烈一不懂,心底更为惊震,他究竟是谁?
摄政王府前身乃是圣祖皇帝下旨敕造的淮王府,恢弘大气不输当年的东宫,在先帝还未登基前,朝中百官曾有议论,以为淮王会取先帝而代之。然而,淮王虽幼却机敏聪慧,以游学之名远离了凉都,多年未归。
先帝薨后一年,薄氏发动宫变,长孙徽音自揽朝政,被尊摄政王,王府也随之扩大了,但却未曾邀过什么外人过府。但看少年的轻车熟路,显然对府中很是熟悉。
狐疑的眸色愈发沉暗,烈一心思一动,对隐在暗处的暗卫们打了个手势,让他们静待己处,自己则继续跟在后面。
少年七弯八拐的,绕过垂花门,从夹壁甬道进去,推开尽头的一扇小门直接入了后院。
爬满枫藤的墙壁之处,曲径通幽而来,粉红的山茶开在沙白的怪石堆里,将那扇小小的门恰到好处地遮掩住,故而许多人都不曾知那成片的碧色后面竟是道不起眼的门,即使烈一这样在王府生活好几年的人。
抖抖身上的落灰,少年从山石间穿过。
烈一好奇,偌大的后院,他要去哪儿?
莫非是哪个姨娘的院落?
然而,出乎他意料,少年压根儿就没去他脑子里想的地方,可当他停下时,烈一觉得自己脑子都炸了!
怎么会是长乐馆?
朱红的大门上挂着铜锁,少年溜溜的乌眸落在锁上,眼底闪过一丝不自在。尔后,他想鼓足勇气做了个决定,用手去拉了下锁,哪知看着锁得挺结实的铜锁居然轻易地就被扯开了。
他秀气的脸庞上流露出意外的惊喜,马上推了门走进去。
飞檐碧竹,楼阁精巧,一方碧水清潭,几株千瓣莲谢了花,只余几片荷叶仍旧碧翠。只是,本该赏心悦目的院子里却长了不少的杂草,许多草木甚至没有修枝,乱哄哄地散着枝丫。
深秋里,阳光微冷,满园萧瑟。
少年信步走在抄手长廊里,廊檐下的轻纱染了稠厚的尘埃,美人靠也换了灰白了的颜色,走上去烙下一个个脚印。
这里是好多年都没有人进来了吗?
光彩熠熠的乌眸瞬间灭了那星光月华般的颜色,他一步一步,缅怀似的在长乐馆中走了一圈,最终坐在一株镰刀形的梧桐树下的青瓷花桌旁,目光呆呆地看着放在桌上的酒坛。
烈一伏在一株松沙树间,饶有兴味地摸着下巴,他算是发现了,少年根本不是来王府使坏的,反倒是来“回家”的。
尽管这词儿用得怪,可烈一觉得很贴切,他除了好奇少年的身份外,更对他的和王府的过往有兴趣,或者说是少年和自家主子的往事。
为啥这么说?
烈一跟着长孙徽音的时间不长,觉得吧,主子就是寡言少语冷漠难测的人,这世上要说有谁能牵动他的情绪,除了已逝的文德太后容华外,即使皇陵太皇太妃薄氏,想让他皱个眉头都难。
自摄政王之名传开,王府内也被仔细清理过,可谓铁通一般,哪怕后院的莺莺燕燕众多,也无法将手伸到前院来。
众人说到摄政王,莫不噤声敬畏,使得许多打着和摄政王有亲缘关系的人都望而怯步。
可这少年却毫无惧色,借治花之名独闯王府,畅通无阻地进了内宅,来的还偏偏是长乐馆。
据他所知,长乐馆是原淮王府最大的院子,是长孙徽音的寝院。容华未进宫前,长孙徽音有意求娶于她,将院子按照两人的喜好彻底改建,并换名长乐馆,谓之天终地久长乐无极。
可天不遂人愿,容华在离奇失踪后被找回来,就一意孤行地进了宫。长孙徽音心痛之余,就搬出了长乐馆,除了洒扫的下人再也不许任何人踏足此地。
一晃多年,容华早逝,他就彻底将长乐馆封闭了起来。如今,王府谁人不知道,摄政王从不歇在后院,长乐馆更是府中的禁地,连靠近几分都要被惩处。
少年哪儿都不去却来到这里,除了和王爷的旧事有关,他可想不出别的。
烈一稳稳地和树干贴在一起,心道,他非得给看出了一二三来才行。
就在他满心盘算时,一声女子的厉喝突然响起:“你是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