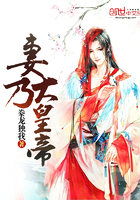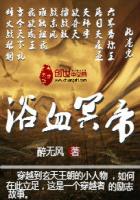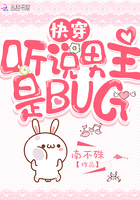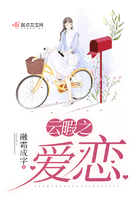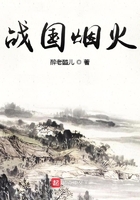崇祯现在的总方针,就是抓紧时间处理内政,首要是解决财政收入的难题;军事方面就交给了孙承宗与袁崇焕,孙承宗负责整训京师三大营与京师周边的防务,袁崇焕则负责辽东防务以及加紧训练关宁铁骑的野战能力。
至于什么外交,这时还只是礼部下署的理蕃司,崇祯暂时还没什么心思去管。哪怕是非常重要的郑芝龙,崇祯也只是将其交归兵院,强调要加强对其水师的管理;唯一有些针对性的措施,就是除广州外另建立三大市舶司,加强海关税收的征管,断除郑芝龙的财政来源。
辽东的袁崇焕现在正是意气风发,平息了宁远、锦州兵变,军饷粮草又随后送到,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这时,锦州、杏山、高桥三城及十三站以东21座墩台俱被后金摧毁,袁崇焕立即选任将官,指挥军民一一修缮城池,又招募流民充实各军部伍,仔细调配城头火炮,严阵以待来犯建奴之敌。同时,军令严传各处,各级将官均须听从调遣,互相配合,以克期复辽。
在袁崇焕的严令整治下,辽东各城得以恢复,形成了坚强的防御体系,后金不敢再轻易攻掠,边事一时安宁下来。
就在修筑锦州城、大小凌河等周边卫堡,加强训练关宁铁骑的野战能力时,朝廷秘密押运来一批新火器,袁崇焕感觉真是如虎添翼。
原来的红夷大炮,虽然打击的距离与威力都令人满意,但炮弹的装填速度却是太慢了,前装炮是不可能快的,也就只能守城用用。
然而这次的火龙炮野外演练,完美地解决了中距的火力连续覆盖问题,其车载发射形式,就是野战也可发挥作用。至于掌心雷,袁崇焕则是有些懊恼自己,这跟现在的火蒺藜差不太多,就是模样不一样,怎自己就没想到呢,听说这也是崇祯皇帝的发明;虽仅只是外观的改变,但作战应用却大大改观。
袁崇焕的眼前,似乎展现出一片图景:建奴骑兵猛冲过来,火龙炮一排又一排地不间断发射覆盖,即使有漏网之鱼冲到近前,也会遭到如雨点般地投掷掌心雷,这时关宁铁骑再冲阵,已是不费吹灰之力。
景象再换:双方野战偶遇,有掌心雷密集投掷以守住阵脚,随军的车载火龙炮覆盖发射,断其后续骑兵,最后再以关宁铁骑的冲锋陷阵,想是胜算不难了。
与押运火器同行而来的太监,在宣读完对袁崇焕平息兵变的嘉奖后,见其对这些新火器的欣喜之情,不由得替崇祯皇帝吹嘘了一番,什么天人感应、神来之笔、妙手天成,简直就是真正的真龙天子。
在替崇祯的吹嘘中,忍不住透露出,崇祯帝还打算改进鸟铳,听说是能够连续发射的。袁崇焕听得是将信将疑,如果再解决了鸟铳的连续发射,原来还有些含糊的“五年平辽”,还不是易如反掌之事。
太监替崇祯帝吹嘘完后,屏退左右侍卫,传崇祯帝口谕:加紧练兵,掌握新火器,严守关宁锦防线,广派细作探查,重点关注建奴与蒙古间的关系,不急于出兵收复失地。
皇帝的口谕,与袁崇焕心中所想完全一致,自是领旨遵从,只是奇怪为何要重点关注蒙古,难道担心会联合蒙古来攻?
这道口谕的后半部分,锦衣卫北镇抚使吴孟明也收到过,但又增加了部分,同时还需关注关宁锦防线与毛文龙的觉华岛。
袁崇焕这边严防死守,而皇太极这边却是有些耗不起。
自立国以来,父汗努尔哈赤一生征战,百战百胜,唯一次失败就败在袁崇焕手下,最后落得伤重不治而亡。皇太极初登汗位,自是要为父报仇,更是要扬名立威以巩固汗位,哪知就来了个宁锦大败,虽没伤了筋骨,却也损失惨重。
好在明朝内讧,临阵换将,袁崇焕辞职还乡;哪知峰回路转,大明换了皇帝,又重新启用袁崇焕。
就在两个多月前,袁崇焕快马到任,宁远兵变刚刚平息;被皇太极探知消息,立刻派兵试探着进犯黄泥洼。袁崇焕重回辽东,关宁军是军心大振,祖大寿挥军迎击,将后金兵击退。这次战役虽然规模不大,却未试探出关宁军在防守上的破绽;此役,关宁军斩首180级,获骡马120匹,取得了不小的战果。
皇太极几次对大明用兵,都是折戟而归,若不是东征朝鲜、西征蒙古都得胜而还,他这汗位还真是坐不下去了。现在的状况,另三大贝勒对此是颇多微词,在政务处理上总是掣肘。
在崇祯帝着力内政事务的时候,皇太极为扩编八旗实力,加强大汗集权,开始着手削弱四大、四小贝勒等八和硕贝勒旗权。
皇太极的内政外交,较父汗努尔哈赤更具有策略性、迷惑性。然而他对汉人更为缓和的策略,却遭到其他贝勒的反对,皇太极为削减诸贝勒的旗权,打着“为各旗贝勒分忧的名义”,断然提高固山额真的地位和职权,命他们参议军国大事,总理旗务。
皇太极设置总管旗务的八大臣,给予各旗固山额真以实权,“总理一切事务,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出猎行师,议定启奏,各领本旗兵行。凡国中大小事,皆听稽察”。皇太极的这一断然措施,既对诸贝勒以分权,又未伤及诸贝勒的根本。
后来,皇太极照本宣科,又两次设置******臣,“佐理国政,审断狱讼,不令出兵驻防”,“出兵驻防,以时调遣,仍审理词讼”。
皇太极设置八大臣、******臣,使他们入则赞襄庙谟,出则办理国事。这无疑是在努尔哈赤遗留的“共议国政”,在体制上打进了一个楔子。尽管这个楔子令诸贝勒不太舒服,在无法直接反对的情况下只好接受;这一强有力的举措,扩大了皇太极汗权的统治基础。
皇太极设置八大臣辅政成功后,又以“黄色是汗”,“黄衣称朕”的名义,改旗易帜,将自领的两白旗,变更为两黄旗。
后金的八旗制,由努尔哈赤创立,其中的两黄旗自是由努尔哈赤将领;其死后,两黄旗就传给四小贝勒中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三兄弟。
黄色为皇权专用,后金自是为汗权所专用,是八旗最高权力的象征。皇太极身为大汗,却只是白旗旗主,很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意味,使得皇太极无法摆脱“八王共治”的羁绊,十分不利于实现“钦承宸断”。
皇太极在“不削夺皇考所予户口”的条件下,行险用急,大胆地变易旗帜,欺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三兄弟年幼,将自领的两白旗与三兄弟所属的两黄旗易帜,即皇太极将领两黄旗,三兄弟则领两白旗。在不伤原旗筋骨的情况下,年少的三兄弟只得接受,而三大贝勒对此,也是只能是默许了。
后来,由于莽古尔泰冒犯皇太极威权,又将其所领正蓝旗收归己有。从此,他独领两黄一蓝三旗,在八旗中实力最强。
有宁远、宁锦的两次大教训,皇太极再也不敢小瞧了明朝的军事实力,更对袁崇焕这个蛮子顾虑重重。前次黄泥洼的试探,无功而返,损失了近两百人马;这是一次典型的野外遭遇战,双方可说是势均力敌,只是关宁铁骑的三眼火铳厉害,这才不得不退了回去。
宁远是完全的守城之战,宁锦是依托城墙的攻守战,而这次黄泥洼的遭遇战,是双方骑兵的对攻战,这种种战事的变化趋势,令皇太极感到忧虑。尽管他相信,明军的骑兵仍不足以同他的八旗骑兵相抗衡,但这种趋势却引起了皇太极的警觉。
皇太极现在需要时间,左右两翼的蒙古与朝鲜,还需加强稳固。蒙古的科尔沁、翁牛特、郭尔罗斯、克什克腾等部,已先后投奔后金;现在的蒙古大草原,只余察哈尔多、土默特、喀喇沁等几个相对较大的部族。朝鲜却是有些“身在曹营心在汉”,对后金多是虚应事故,对此皇太极是心知肚明。
大明朝的崇祯帝,又何尝不需要时间,大明已是千疮百孔,经不起长久战事的折腾,与后金建奴之战必是雷霆一击,才有可能让明朝有喘息的时机。
因此,辽东前线,在这大战的间隙,对峙的双方反而显得较为平静。虽然明朝对后金早已实行了贸易禁运,但各大边镇的贸易仍是不可避免地再次繁荣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