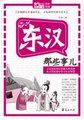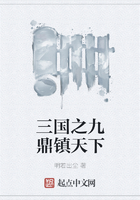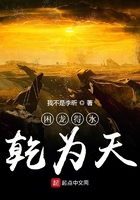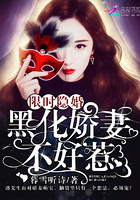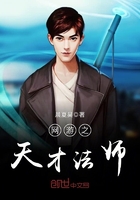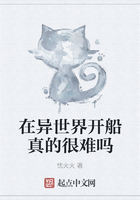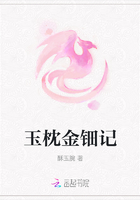日讲,崇祯听着听着,就有些走神。
这一个来月的皇帝生活,美女倒是享受了不少,可是学习、工作的任务却一日重似一日;就是现在发动变法,思考未来国家走向等战略问题的时间都没有。
每天的奏折,根本就看不完,他已经牺牲了八小时外的所有业余时间;有时看不过来,还要向日讲官请个假,突击一下成堆的奏折。
崇祯总担心这些古代的大臣们,治国时不以民为本,一味地满足官僚地主阶层的利益;也担心治国理念的古旧保守,对政局的痼疾沉疴无有效方法。
崇祯的古文阅读水平尽管进步神速,但离一目十行还差得太远,这都影响了他处理政务的速度;他更担心的是自己,别不了解明朝实情,就自以为是的胡批乱改,那更糟糕。
日讲,对崇祯是很重要的,这是他了解大明政情,很重要的一个渠道。原来,日讲以“四书”、“五经”和《通鉴》、《祖训》等经史为主;现在,崇祯要求以《通鉴》、《祖训》、“各朝实录”等史书为主,四书五经为辅。这也是他同大臣们再三要求后,才改为现在这样。
崇祯有些想不明白,历史上的那个“崇祯”,怎就能十几年如一日,天天处理如此多的政务,而且越是后期,就越没一件能令人开心的消息。
实在是有些佩服那个“崇祯”了,自己坚持了一个月,就开始叫苦连天了。如果以后仅是这些事务性的问题,就让他忙得不可开胶,没有时间去思考一些问题,恐怕结果更糟糕,还不如那位呢!
这些经史大家们,为自己度身定制的历史讲解,对自己非常重要,他深刻理解、体会到了“毛主席为何会十几遍地熟读《二十四史》”的重要意义。
既然日讲的时间必须保证,那只有放权了,自己可做不到把这些权力,时时刻刻地都抓在手里。
日讲官用醒木敲敲桌子,提醒皇上要注意听讲。
崇祯道了个歉,同时叫过一个小太监,传旨:下午文华殿内议事,望内阁大臣、六部、六科、都察院主事负责的大臣都到。
下了决心的崇祯,终于能安静地听讲了。
炎热夏季,文华殿内有些气闷,但是大臣们的心更热,“皇帝竟然要放权!”
这让大臣们煞费猜疑:前朝皇帝再是怠政,可没有要放权的,都有太监在那儿给盯着呢;难道是要重新恢复相权,这个内阁制可是成祖朱棣好不容易发明,在宣宗时才成形的;难道是年青人没常性,前时的勤政坚持不下来了,也要荒嬉政事?
“朕不是要真正的放权,只是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有内阁票拟就可以了,当然出了问题,也要由内阁负责。如今以韩爱卿为首辅的阁臣共有四位,所有票拟须经首辅认可,但如果有半数阁臣未在上面签字时,则须报朕御批;或者认为事情重大犹疑难决时,也可报朕御批。”崇祯想参考后世的集体领导制。
崇祯接着说道:“奏折经通政使司汇总后,重要奏折由司礼监誊写一份;内阁票拟后,司礼监再誊写票拟一份,乾清宫将专辟暖阁收藏奏折,以做备案。当然,朕如果认为有些票拟不太妥当时,也会责成内阁改正的。不知,诸位爱卿以为如何?”
原来,奏折只由一位阁臣负责票拟,皇帝再予批红;崇祯的的这番作法,在给了首辅一票否决权时,又予以一定制约;必须征得半数(含)以上阁臣同意,票拟才能通过,而阁臣现有四位为双数,这将增大互相制约的力度。
首辅韩爌出班奏道:“臣等实不知陛下为何如此?陛下英明勤勉,正应率领臣等中兴大明,永保江山社稷。”
这番权力的调整,虽然增大了阁臣间的制约,却搬掉了压在他们头上的一座大山——司礼监,太监没有了批红权,将会真正放开他们被缚住的手脚。
首辅韩爌虽然马上就想明了这其中的关键,但却难以猜透皇帝的心思。
“朕还年轻,有许多东西要学习,也需要思考一些大事“我大明的发展方向”。这样,朕的时间就不够用了,就需要诸位爱卿担起更多的责任来。朕不希望再出现前朝旧事,似“魏忠贤、刘谨”之流,祸乱朝纲。”崇祯坦承地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臣等必将尽心竭力,辅保圣上。”韩爌忙带头表明心迹,生怕皇帝又改变了主意;其余大臣随声附和,连称陛下圣明。
这是放权,去掉了大臣们的心病——司礼监,这哪还会有不拥护的道理。即使跟太监走得最近的大臣,也是因为他们手中的批红权,而不得不去巴结;文人是从心眼儿里,瞧不起那些肢体不全之人的。
“呵呵,诸位爱卿也不必忙着谢朕,朕也会加强监督的。”崇祯见大臣们都满面笑意,也就笑着把丑话说到了前面。
众位大臣们的心里咯噔一下,刚才有些得意忘形,怎就忘了还有锦衣卫,还有诏狱呢?
崇祯又提出,加强都察院、六科两部门的监督力量,重申了这两大监督部门只对皇帝负责的原则;却绝口未提锦衣卫的事情,这让大臣们的心里,仍紧绷着一根弦儿。
崇祯受后世的影响,对太监、锦衣卫、诏狱等,都有些深恶痛绝,其它两样他想逐渐消除;锦衣卫却是要保留的,还要发展壮大,改造为强大的情报机构,暂时兼有国内外两方面的安全职责。
崇祯对于锦衣卫的认识,先受港台影视影响,都是残害忠良的印象,只是后来才真正知道了它的职能,看法才有所改变。只是他没有大臣们那么敏感,首先想到的是锦请卫的调查监督,诏狱的刑讯逼供、任意处置。
此次朝会,对今后政局的影响,可想而知。
现在的内阁,可以说是“准东林”内阁,都是同情支持者,或就是东林人;同时,东林一派也占据了朝廷部分关键岗位,对朝局的影响越来越大。崇祯的放权,使得东林人对未来的朝局,充满了乐观态度,年底的阁臣会推志在必得。
钦差大臣钱谦益的江浙赈灾,对于东林人就显得尤其重要:做得好,则凸显出东林人蓬勃朝气;做得不好,遭人弹劾,年来的努力即使不致前功尽弃,但也必遭皇帝另眼想看。如此一来,自有人书信驿递传送,将此朝局的重大变动,告知钱谦益。
温府书房,礼部尚书温体仁已经踌躇考虑半天了,踱来踱去,又坐了下来。如今的阁臣,更是位高权重,自己已经做到尚书了,要想更进一步,就需被推为阁臣。只是,现在的内阁多为东林友人,东林魁首钱谦益已是自己礼部的侍郎,眼见得崇祯重用,未来入阁怕已成定局。
周延儒,同样受到崇祯重用,广招诸生、教导集训,正办理得风声水起;教导员名为教化,实为监军,不论文武还是普通人家,哪个不想籍此安插进自己的人,哪个不想籍此能谋个出身,即使军中危险,但升迁也必迅速。
温体仁想到这里,如能引其盟友,同进共退,想必更有把握。
崇祯看到身旁服侍的太监,忽然意识到:放权于大臣们,大想自然拥护;太监的权力却大受损害,而太监却是自己的身边人,这要对自己有所怨气,暗地里使些手段,自己可是防不胜防。
这疑心一起,看着哪个太监,都象是要给自己投毒的人;崇祯摇摇头,别瞎想了,太监们就算有些怨气,也还不到这个地步,自己还没逼人走到绝路呢。
只是,这也让崇祯肯定了前时的做法,要给下岗的太监、宫女找到合适的出路,让留下的人也能安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