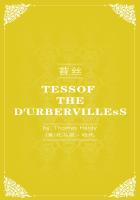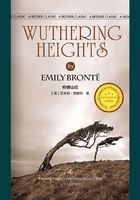唤到老蒋的时候,他又和老婆拧了好一会,架不住她连劝带推,脸红筋胀地进去了。回头看看,老婆给护士挡门外了。他才解气地哼一声,掉过脸来冲医生咧咧嘴。
大约前头已谈了一个的缘故,医生用手掩着嘴打了个呵欠。什么响声也没听见似地,一边快速翻着老蒋的心理测试表,一边例行公事地问了些姓名、职业之类问题。老蒋嘴上懒洋洋哼哈着,两眼却总向窗外翻。医生顺他目光看去,却只见窗外天色昏暗,玻璃上模糊不清,偶尔看得出纷乱的雪片打在窗上的闪光,令人不寒而栗。他赶紧收回目光,加重语气道:这么说你是初诊。表格上好像也没什么事。那我们就随便聊聊?聊啥?老蒋闷声道。这要问你呀?比方说,你到这儿来主要想求助什么。或者,有什么心里话或苦闷什么的,无话不可对我说……
为啥?
因为这是心理咨询呀?你看这地方暖和和的,又没旁人。我们的职责之一就是为患者保密。所以,此时不说,更待何时?
可老蒋没听见似的,歪着脑袋连哼也不再哼一声了。见多识广的医生多少也有些意外地观察了老蒋一会。见他脸上已恢复了青灰的本色,说话时眼神矜持而紧张地溜着窗口,就是不向他这儿看。但插在裤袋里的两只手却一直在鼓鼓突突、握紧松开地不安分着。经验丰富的医生马上叫他坐得放松些,把手从裤袋里拿出来。可老蒋的表情突然惊慌起来,怎么劝也不肯把手拿出来,反一再强调自己好好的,什么心病也没有,完全是老婆瞎胡闹,把自己硬哄来的。
既然这样,我们更可以自然相处了。医生表示宽容地笑笑:我也最好你什么事也没有,乐得轻松。只是有一点我该提醒你,别忘了你们打老远从县里赶这儿来,是要付钱的。一小时啥也不说,那60块花得就有点冤哪……不,你现在走也没用,不足一小时按一小时收费。
老蒋垂头丧气地坐回原处,两手却更紧地捂在裤袋里。医生不出声地又等了几分钟,见他仍不说话,突然道:你说你爱人硬把你哄这来是什么意思?莫非你好好的,有什么心理障碍的倒是她?
这倒不见得。老蒋又沉默了半晌终于开了口:她也没什么。就是妇道人家,什么都搞不清楚。其实我好好的,她总爱说我脑子有病,拎不清。可我错哪儿啦?那年我那么做,后来看是傻了点;可后来我不是早不那么做了吗,她还是三天两头说我傻拎不清……
那你能具体说说到底什么事使你们看法这样不同的吗?
老蒋下意识地偏头看了医生一眼,似乎想说什么,可眼光一落到他桌上的台历上,头又刷地扭开去,脸一下红起来,呼吸也变得粗重。而两手又在裤袋里一阵乱折腾。医生敏感地叫他回过头,看着自己说话,他就是不肯。医生神色陡然严峻,喝问他是否对自己不信任,他使劲摇头。那你在我身上或这桌上看到了什么?某种令你恐惧的怪物?或者,这枝笔变成了一把利剑?医生逼视着他不放,力图判定他是否出现幻觉:说,说出来,大胆说出你的真实感觉!把手拿出来,拿出来,手!
最后一个字医生几乎是命令式地叫喊,把老蒋吓得直往后缩,额头上也突然沁出一层冷汗。他不得不抽出一只手,哆嗦地指着医生面前的台历:请,请你把它拿、拿开吧。
为什么?医生一步蹿到老蒋面前:为什么它会使你害怕?你觉得它是什么?
什么也不是。
不,告诉我它到底是什么?
台历呀,一本普通的台历呀?
那你为什么害怕它?
也不是害怕,就是有点……紧张。因为我老觉得它放得不够正。
这不好好的吗,有什么不正?再说,它放得不正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也知道没关系。可是……总觉得不舒服。
想把它摆摆正?
是呀!你怎么知道的?可我怕你笑话我,就只好……老蒋谄笑着靠近桌前,可伸出去的手被医生挡住了:试试看,你今天不去摆弄它会怎样?老蒋脸色骤变,双手一下子又插进了裤袋里。医生恍然地叹了口气。回到座位上考虑了一会后,他请老蒋暂时出去一下,说要先和他爱人谈谈。
和老蒋正相反,他老婆显然早憋一肚子话了,闸一开就哗哗狂泻。好像来咨询的是她:医生你猜得真不错。老蒋他就是个顶真货,做起事来丁是丁卯是卯,一点不带含糊。别的不说,在部队上他年年得射击模范。靠的啥,就是他一丝不苟,舍得下死劲练!有时候一气能对着个靶子瞄几个钟头。可就这样吧,过去他一直好好的,除了脾气倔一点,没啥太出格的。可现在……细想,也就这三两年里的变化,他越来越怪,越来越走火入魔,还死不承认有病!
具体说,他都有些什么症状?
这个说起来话就多啦!起先吧我也没觉出来。他一般是回到家来就不爱出门,躲在自己房里,拿张晚报从头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连广告也不带放过的。后来吧,他看了报就爱骂骂咧咧,尤其是看到那些杀人放火、贪污腐化的;这些消息现在不是越来越多吗?他也就越来越爱冲动起火。常常还不讲道理,冲我又敲报纸又打桌子的评论个半天。我也慢慢习惯了。知道是他心里不痛快,寻思着让他泄泄火也有好处。可不知几时起,他渐渐不爱言语了。看报也不那么着迷了。却跟房里那架电视机过不去了。对了,是我们刚搬家以后的事。那电视也确实搁得不够正。他先是自己找纸垫了垫。好些了,过一天又嫌垫得太过了。又重垫。这样折腾几天后,突然跟我说,不行,总得要彻底解决这问题。于是找来会点木工活的女婿,把好端端个电视机柜一边的腿给截掉一小条,总算是满意了。
嗨!没几天他又来事了。这回是床对面墙上挂的那画碍他了。怪的是不躺上床他好像一点也看不到那画,一躺到床上就嘟囔着要我看那画怎么又歪了。起先吧,我看着也是有点歪。就帮他拨拨正。可他那个搅劲哪——天下哪有绝对正的东西呢?明明我看着很可以了,他却死活不通融。一会儿指挥我左一点,一会儿又指挥我右一点,反正怎么也觉得那画没挂正!我来气,就说你要嫌画不讨喜,干脆摘了它别挂。可他不许我摘,也不要我帮忙,每晚头等大事就是自个爬上爬下不厌其烦地拨弄那画,非弄得对劲才舒口气上床。有时不满意起来,他能摆弄上几个钟头,直摆弄到深更半夜,我都一呼噜醒来了,他还在爬上爬下。非弄到自己也累得不行了,才气哼哼关上灯往被窝里一钻!
后来我实在看不下去,就乘他上班偷偷把那画给摘了。他倒也好像没看见似的一声不吭。可没想到好了没几天,他又跟客厅和孩子房里的挂画过不去了……医生啊,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也不知我们是救了他还是害了他。反正弄到后来,我们家所有的画框呀、条幅呀、闹钟啊反正一切要摆正的东西,能摘的我都给摘完了。摘一样,他好像太平几天,过不了多久,又瞄上另外件东西。反正他就是走火入魔——对,就像你说的“强迫症”上了。
这倒也罢了。因为头一两年他只在家里犯这怪癖,一出门就跟什么人一样好好的。可后来就不得了啦,尤其是今年以来,他到了单位也犯开病啦。你想想,那么大个单位,什么锦旗哪、条幅哪、大钟哪、电视啊什么的,哪个房间没有个一样两样的,你也像在家里似的爬上爬下摆弄去?这下可把他自己也吓坏了。为了怕不小心动手动脚让人看出啥,一到单位就使劲把两手插袖袋里。可老这么着别说自己别扭,别人看长了不是也觉得不正常吗?但他不这么不行,非这么着在有那些东西的地方心里才轻松点,否则就烦躁、紧张、冒冷汗。厉害起来还会胸闷、手抖,甚至要死过去似地喘不过气来。有回洗澡时,我见他大腿两边都是一溜的青紫块,以为得啥病了。原来他在单位里,有时伸手拨弄的欲望太强,就用手隔着裤袋掐自己!
可这么老袖着手,又比伸手去摆弄什么强哪去呢?单位里人很快觉出他的怪异,背后送他个绰号叫:“袖手旁”——就是袖手旁观的意思。是他自己无意中听到的,倒也不恼,回来当个笑话给我说,还冷笑着说什么:算他们说着了,我这人可不就是个“袖手旁”吗?
那天我们还为这事大吵了一架,因为我一听这话气就不打一处来:你要是早知道该“袖手旁”还会有今天?你现在倒是给我把手给放出来呀,放出来你指手划脚试试看,会有谁真吃你蒋副主任那一套——医生,我指的不是真让他摆弄那些画框什么的意思,而是说……
我听得懂。我也正想问你,虽然登记表上显然是假名,但我也看出他像个干部,刚才你也提到他在单位是副主任;那他怎会“袖手旁”的呢?我指的也不是摆弄什么的意思。听起来好像他跟同事或领导相处得不怎么愉快?如果你信任我们为患者保密的原则,能否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没事,反正你也不知道我们真名实姓。只要你想了解的我都说。只是这要说起来,话就长喽。
我是85年随老蒋从部队转业回家乡的。我在县中当教师,他是团副政委,因为在部队挺先进,一回来就直接当了乡长。虽然那乡小点,毕竟也是“鸡头”,还说明领导器重。那时他才三十来岁,好好干,四面八方搞好关系的话,谁不信他前途一片光明?老蒋也确是块料,在部队上苦也吃惯的人,一上任就走村串户,和百姓同吃同住的,多半年没有过连续在家住三个晚上的时候。这情况很快引起县上重视,书记在全县三干会上把他大大表扬了一通,那意思不说马上提拔,起码也像要树个焦裕禄式好干部的架势——哪曾想正在这时,风云突变!老蒋他做出件下辈子也忘不了的大傻事。
说起来,这也是命,或者说,是一个人的性格、经历所必然决定的事情。老蒋他生性较真,好犯傻病还不承认。18岁当兵到转业,一直在部队上干。刚回来,对地方上的许多套路他还陌生得很,加上他固执己见不听我的劝,所以捅娄子就是自然的事了。
是这么个事:县委书记带了5个乡镇干部到南方考察发展乡镇企业的事。其中有老蒋一个。由此也可见书记是真赏识他。而这一路上都好好的,偏是临上火车时,县上驻那儿办事处的主任拍书记马屁,给大家每人备了个当时还挺稀罕的密码箱,里头装了两条三五烟,一件金利来衬衫跟领带,还有个8百块的小红包,说是车上的点心钱。8百块,要现在谁敢给县委书记送这么个破红包?在那时可不同,那书记心里肯定也挺受用的。可不光是他,连我也万万没料到,这又迂又蠢又死不开窍的傻老蒋他犯了难。一路上心事重重都不说了,要命的是回到家后,我见他忧心忡忡问怎么回事,他把情况给我说了,还问我该不该把钱物都上交,我当时就骂他脑子有病,这东西我们可以不稀罕,可你往哪儿一交,别人怎么办?县委书记怎么办?你自个今后怎么办?
嗨!世上也就是有这号人!老蒋他听了我的话再也没提这件事。顾自闷头在床上翻了一夜烧饼,第二天一大早,居然还是到纪委,把那些钱物统统交了!你道他交时人家纪委人怎么说?可敬可敬!这社会都像老蒋这样了,愁什么主义闹不成!你说,这倒是夸他还是刺他?
以后?我说医生,凭您这水平还想像不出来?对呀!不过书记到底是书记,钱物交没交我不知道,只知他一声没跟老蒋吭哧过这码事,只不过干脆利落地,一月不到就把他打发到全县最远最穷的小僻乡去。总算还不错,给了个副书记的虚名头,说让他“学南方经验,开创新局面!”
就那样也罢了。老蒋也不是没一点思想准备,而且时间长了,他要能接受教训不再犯傻的话,保不准书记消了气或换了新书记会时来运转。偏偏那命运不放他,总跟他恶作剧。老蒋的事虽然当官的听着都来气,老百姓听着却受用。于是三传两传地,不知怎地让一个来采访的省报记者听说了,给老蒋打了个电话问了问经过,回去就写了个表扬稿。说什么廉洁拒腐的,在省报上登出来。这一下更好了,虽然无论那稿子还是老蒋的谈话里,都一个字没提县上其他人,可那时正碰上省里要开廉政建设先进表彰会,见了这消息如获至宝,特地来了调查组,三问两核实的,县上纪委也只好把事情来龙去脉都说了。这下那个热闹呀,表面上老蒋是扬眉吐气了,又上省里出席大会,又上党校培养地在外风光了几个月。
可实际上是更重地砸了他一闷棍——受他那事的牵连,县委书记给调走了,可实际上却是成全了他,给弄到市里当了个统计局长。新来的书记看上去并没有成见,似乎还欣赏老蒋,逢到要说几句廉政的词时,也拿他夸了好几回。并且也把他调到县上来。却从此一副到底,十几年如一日当起了“放屁也不响”的“袖手旁”来。
这倒也成,太太平平不也是个活?可老蒋他哪个单位也呆不长。无论他怎么接受教训,夹紧尾巴,甚至同流合污,但那事的阴影和“廉政模范”的虚光,就此把他罩死了。也难怪,哪个单位的一把手几把手的见了他不来点条件反射?不看作异类,起码也担心他在身边是定时炸弹。屁股上有屎的就更不用说,见了他总觉得不舒服,自然便挤之惟恐不及。于是这十几年来,老蒋就总是副局长、副部长、副书记、副主任地,差不多把县里那些清闲的部委办局转了个遍……
这时老蒋爱人嗓子发哽,不得不停下来擦泪。医生忙开导她一番,多少也吐几句心里话:其实世事都在于怎么看。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很多矛盾都跟如何适应社会有关。起码从我的职业角度看,劝不了社会,就只能劝人。而人跟社会只能你适应或智取它,而不能指望取胜它。老蒋的处境的确够窝囊,但说到底还是他适应社会不良的问题。况且事已如此,他能换个角度看的话,能这么副副副的,比起许多差不多遭遇的人来说,可能已够幸运了。
你这些道理我也没少跟老蒋说。起先他很不服,总觉得时间会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慢慢地不仅泄了气,还知道后悔了。于是闭紧嘴巴,到哪都“袖手旁”;不管他有理无理,一把手说了就点头。下面开会发点这个那个,单位里变法子分点这钱那款的,都照收不误。不瞒你说,虽然他是个副的,毕竟还带个长字,到的单位有穷有富吧,总还有点儿权在。这年头就少不了也会有人送这送那。起先呢,他是礼重的不收。后来习惯了,就改成现金不收。再后来是先收了再说,红包超过一千块坚决退回。再后来呢……当然多了人家也不会送他,可老蒋他有一阵变得让我都吃惊。好像脑子又有点什么病,拼命想找补。作为他老婆,我还怕他有过火之处,不小心犯法坐牢。可他有时贪得让我都害怕。而且不是他转来转去吗?转到个好单位吧,他嫌人家瞧不起他,送礼也不送像样的;或者恨自己能得这么些,那一把手两把手不知要捞多少。转到个穷单位吧,又成天唠叨清水衙门、人心势利什么的。总之左右不开心,好像就这么慢慢地发开了神经,总跟电视机和挂画过不去。
去年,我们那县上出了个轰动一时的大新闻,你可能没看到,县上千方百计压着不让报呢——因为出了伙怪偷,专跟当官的过不去。头一家偷的是公安局长,第二家是政法委书记,第三家是组织部长,全都是百万以上的财物,边偷边录像,把带子和财物数往省上、中央报……直偷到第五家,那三个神偷才让日夜死守的警察给逮住了……这消息谁听了都拍手称快,可老蒋他怪了。起先也大呼痛快,恨他们给抓早了,要不然偷了他书记县长的,看哪家会比局长部长少。可在家嚷嚷了几天后却突然不言语了。不但烦我们议论这号事,一天黑就怕碰上贼,一遍遍检查门窗关紧没,后来又发展成反复检查煤气开关和水龙头,明明关过好几遍了,偏还一趟趟地往厨房卫生间拱……更可笑的是,他特意备了一千块钱,和一张纸条用橡皮筋扎一起,每天放在冰箱上显眼处。纸条上写的是:
敬启者:这不是贪官污吏家,拜托你放一马。这点薄敬,聊表谢意。
我说你又犯什么病、害哪门子怕呀?就你那副副副、“袖手旁”的,撑死了能收几个钱;就我们家这破烂相,哪个小偷看得上?可我越这么说,他越忙乎得紧,不得已只好硬把他拉这儿来了。医生你可一定得救救他,老这么下去,他自己都担心会发疯呢……
这个你们可以放心。医生笑笑说:他这是典型的神经症。是长期内心苦闷矛盾不得纾解,导致精神疲劳变态的结果。问题本不算太严重,只是医家治病不治命。他这性格,加上社会状况不太理想,治起来恐怕麻烦些。但我现在有数了,你叫他来,我们好好谈谈,再拟个疏导方案吧。……
没想到,老蒋爱人出去转了一圈却慌慌地跑来说老蒋不见了。医生忙跑出去,她指着候诊厅墙上的挂钟和贝雕画直怪自己大意,有这些东西在,老蒋一个人自然呆不住那么久。医生点头,却相信老蒋不会跑远,肯定到哪个没这些东西的地方猫着了。于是两人出了诊室到外面来找。外面寒气袭人,雪越下越大。随风乱飘的絮絮团团打得人不敢睁眼。两人踩着嘎吱作响的积雪直找到医院大门口,也没见着老蒋的影子。他爱人又抹开了眼泪。医生拍了会脑袋忽然道有了。拉着她就往回跑。果然,就在诊室后一拐弯,住院部前的老雪松后,两人发现了老蒋。
老雪松虬枝纷披,巍峨而孤独地挺立于大雪之中。枝上枝下和四面围护的冬青丛上都积坠着沉甸甸的白雪,唯独树下裸出一圈,枯黄的松针上躺着只呢帽和围巾。再看那“袖手旁”,此刻却双手大展,满面通红地站在冬青圈内,孩子般一个接一个捏着雪团,然后使足吃奶的劲,嗨哈有声地向着老雪松那粗壮的主干上狠命砸。雪团碎开成朵朵白花,苍劲的树干上布满点点白斑……
医生捂嘴偷偷乐了:好一个撼树蚍蜉!
老蒋爱人一拍大腿,刚想喊他,肩上被医生拍了一下:别管他!难得有个宣泄一下的乐子,你还想让他当“袖手旁”?
原载《广州文艺》2000年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