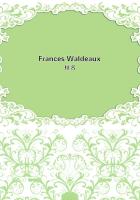立刻就剥了一颗荔枝,殷勤地递给艾连。一边说,一骑红尘妃子笑——
艾连说,无人知是荔枝来。接过荔枝,送入口中。
聊了一会儿,艾连就望着葛通说,你没忘记吧,你还没有给我去登记房间呢?
“怎么会忘记呢?”葛通说,也将艾连望了望,然后闪闪眼睛,又鬼里鬼气地说道,“非得去给你登记么?”
艾连点点头说,当然。
葛通说,好吧。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葛通就回来了。葛通说,真不巧,没房间了。
艾连将信将疑道,真的?
葛通说,真的,不信你可以自己去问问看。
艾连想,这是不是葛通的一个圈套?如果是一个圈套,还不是自己自愿钻进来的么?转而又想,要说是圈套,这何尝又不是一个美丽的圈套?这次跑到蓝市来,不来钻圈套,又来干什么呢?
这么一想,艾连就释然了。
艾连当然不会去问还有没有房间,有房间,难道就该另外开一间?艾连做出一个无可奈何的样子说,今晚我只能露宿街头了?
葛通说,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艾连说,你愿意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葛通说,唯有牺牲多壮志嘛。
不觉得就到了中央电视台播放夜间新闻的时候。葛通见艾连无法自抑地打了一个哈欠,知道再不能这么拖下去了,总得有个妥善的安排,就说,做一个折衷吧,这里本来就有两张床,我们平分秋色,井水不犯河水,怎么样?
艾连说,你做得到?
葛通说,这有什么做不到的?我们单位有一个女人曾说过,如果要她选择一个男人在同一个房间里过夜,而不发生任何故事,那她就选我这个男人。
艾连就笑了,说,她选了你没有?
葛通说,至今还没有。
艾连说,所以今晚你就拿我来做试验。
葛通说,也许我能经得起严峻的考验。
接下来的过程是艾连设计的,葛通洗完澡后先老老实实躺下,然后艾连去卫生间换了一件长长的睡服,躲到另一张床上。钻进被褥后,艾连还说,今晚我就相信你一回,也许你不会违背诺言吧。
葛通说,感谢你的信任。
说着就要伸手去拧房灯的开关。艾连赶忙制止道,不能熄灯。
葛通的手就停在了开关上,葛通说,为什么?
艾连说,你没听说黑暗里的犯罪率高?
葛通笑笑说,我就做一个光明正大的君子吧。
艾连斜眼望望一米外的那张床上的葛通,不觉得也笑了,说,如今是做小人容易做君子难的年代,真是难为你了。这样吧,把大灯关掉,留下一盏地灯就够了。
现在房子里变得幽暗起来,鬼鬼祟祟的地灯在地毯上无声地晃悠着,房间里的气氛显得有些神秘。沉默片刻,艾连在床上翻了一个身,忍不住又开口道,葛通你睡着了吗?
葛通说,我睡着了。
艾连说,那你还说话?
葛通说,没有哪本法律规定睡着了就不能说话吧?
艾连说,你睡着了,可我睡不着。
葛通说,说明你心里有鬼。
艾连说,我这是第一次单独跟一个男人过夜。
葛通说,我不相信。
艾连说,骗你是狗。
葛通说,你没跟你丈夫过过夜?
艾连说,那不算。
葛通说,你丈夫不是男人?
艾连说,他基本上不是男人。
葛通有些意外,脑壳在枕头上偏了偏,去看艾连。艾连那张床上的被子晃悠着暧昧的白光,艾连歪在枕边的头脸却模模糊糊的,不太清楚。葛通想,这是不是艾连发出的一个信号?
两人还聊了些什么,艾连后来就不太有印象了。也许是坐车累了的缘故,聊着聊着,艾连就迷迷糊糊睡了过去。却睡得并不安稳,混混沌沌,好像到了小时候故乡的一条小河边,河里的水清澈见底,有不少小鲤鱼在水里欢快地游着。艾连就忍不住把手伸进水里去捉鱼,鱼们左摇右摆,纷纷从她指间滑走。好不容易抓住一条,眼看就要捞出水面了,那鱼猛地一扭,又逃出了她的掌心。艾连很惋惜,脚一蹬,人就醒了。睁眼往隐约可见的天花板上望去,才意识到自己现在是在蓝市。
睡前发生的那些蹊跷事慢慢又回到她的脑海中。
艾连拿过枕边的手表,借着地灯微弱的反光瞧了瞧,此时已是深夜两点。艾连欠起身子,朝葛通那边看看,葛通的床上什么动静也没有,好像那是一具摆在太平间里的尸体。这么一想,艾连就有些害怕起来,不敢再往葛通那边瞧。
过了好一会儿,艾连才又望了葛通那边一眼,并大着胆子爬起来,伸长脑壳到葛通的床前瞄了瞄,发现葛通还在喘着气,而且有细微的鼾声从微合的嘴巴里缓缓流出。艾连放了心,重新回到自己的床上。
躲下后忍不住老是想,这个葛通真沉得住气,女人伴卧于侧,他竟然睡得这么自在。是女人没有吸引力?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否则他怎么会这么热热心心地把女人约到蓝市来?那么是他真如柳下惠那样,有坐怀不乱的功夫?可这已不是柳下惠的时代。也许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葛通已经废了武功,变成了一个不中用的男人。
对这多少有些荒唐的念头,艾连自觉好笑起来。她否定了自己这一毫无根据也毫无理由的想法。像葛通这种正值盛年而且事业得意的男人,一般是不会有这种情况的。说不定他还是那种优秀突出的男人哩。
艾连胡思乱想着,身上莫名地就有些燥热。她在床上烙了好一阵烧饼,又重新爬了起来。她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两圈,然后蹲到葛通床前,看他不紧不慢旁若无人地呼吸着夜的静谧。她想这个男人的睡相还是蛮中看的,有几分优雅。她真想把自己的嘴啜过去,在他微张的嘴上狂吻一阵。她的头都伏了下去,可半途又停下了。她想故事的开头应该是男人们的事,女人太主动了,不是有些下贱么?
艾连站起身,再次回到自己的床上。她在心里愤愤地骂道,这个该死的葛通,你这不是要我到蓝市来活受罪么?
这个晚上,该发生的故事终于没有发生。
第二个晚上
第二天两人游览了好几处名胜风景,然后又去了蓝城大学。
因为是星期六,校园里人不多,与外面的世界相比,这里真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葛通于是说,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园里可耕田。
艾连说,那你应该牵一头牛来才是。
说着两人走上那条他们去年走过许多回的校园小路。路旁长着梧桐、玉兰和一些不知名的树木。午后温和的阳光从树枝间斜下来,斑驳着宁静的小路和两人的身影。
葛通说,一年时间了,这里还是老样子。
艾连说,是呀,年年岁岁花相似,可是岁岁年年人不同。
葛通望望艾连说,我看你还是去年的老样子。
艾连摇摇头说,你这是安慰我。
他们就这样迈着缓慢的步子,一边慨叹着时光不再,一边随意聊着今人往事。轻风穿过树木,拂着他们的心事,使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缠绵。
这条小路其实并不长,可他们却在路上走了许久,直到夕阳偏西,才向校门口走去。
两人进了校门口一家他们曾经去过多次的小餐馆。主人把一个小包厢给了他俩。小包厢里就一张小餐桌,餐桌上罩着洁白干净的桌布,白瓷茶壶和茶杯素描一样摆在那里,显得十分协调。艾连很喜欢这样的格调,觉得这个葛通真会讨女人高兴。
两人刚落座,主人就走过来,要他们点菜。葛通请艾连点,艾连谦让了一下,也就点了几样不贵的家常菜。等主人走后,葛通就笑着对艾连说,从女人点菜就可看出,这个女人到底喜不喜欢跟他一起吃饭的男人。
艾连说,何以见得?
葛通说,女人如果尽拣昂贵的菜点,是她不怕吃穷这个男人,说明她并不喜欢他;反之,女人如果尽拣便宜的菜点,是男人多花钱女人心疼,说明她喜欢这个男人。
艾连就用手捶了葛通一下,说,你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