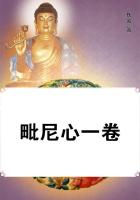“正是此理!正是此理!戴兄好心计!对了,那还有传学之法呢?也快说说?”
“呵呵,这我又要问戴兄一个问题了?为什么这老鼠人们从古捕到今,捕了几千年,用的法子也是花样百出,也捕不绝呢?反而越来越多了。”
“老鼠?” 戴闵生疑惑的问,又低头思考起来,只这一会儿思索得时间特别长。
“可是因为老鼠多,又狡猾?”
钟子启摇摇头,“这只算是原因之一。真正紧要的是老鼠生的快,一只老鼠一年就能生上百只出来,这样一年复一年,只要有吃的,就会不停的生下去,你说人捕的能有它生的快么?”
“戴兄的意思,我应该多传学,多收徒,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的发展下去?可我这也做了啊,我这二年以来所传之人恐怕以十万计都不只,并未感觉有什么大用啊?” 戴闵生说到这里,不由叹口气。
钟子启知道他是在感叹自己这么多学生弟子,事到临头,尽然没一个出面来救的,反要他这素不相识的人来搭救。也不说破。
“恕钟子启直言,你那些上所传之人都非真正得到真传的,他们不过是听了你说的觉的有道理罢了,却没有戴兄这般欲救天下苍生的胸怀与使命感,所以也自然指望不上。我所说的传学是戴兄从小培养一批真正明白了!真正有感同身受的觉悟!真正以拯救苍生为毕生理想的学生!然后一传一、十传百,假以时日,自必从星星之火燎原大明江山,成一发而不可收之势,到得那时,又还有谁能撼动戴兄学说?便是皇帝老子也办不到!”钟子启先还声音低微,说到后来,已是霍然而起,声如洪钟!
戴闵生只怔怔的看着钟子启,待得钟子启回过身来,才喜极而泣!“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戴兄,诚吾师也!”
“师以友,友以师!戴兄何必挂怀?”
“戴兄教谕的是,草泽倒是误入沉泥了。呵呵!” 戴闵生去了心中一块石头,心情也轻松起来。
“对了,戴兄,你去县衙和那个王观礼怎么谈的?”
钟子启赶忙原原本本的将自己与王观礼的谈话复述了一遍,末了,看看戴闵生神色变幻不定,便道:“还望戴兄能学昔日韩信,全大道而弃小节!”边又紧紧盯着戴闵生的脸色,戴闵生已被自己说动了心,只想成就毕生心愿,早去了死志,只希望他不跟那些不懂权变的人一样把名节、颜面看得比大业还重。那自己可真是白戴了半天口舌!
良久,看看戴闵生依然不表是否,便又加上一句,“慷慨赴死易,舍身求义难!”说罢,闭目养神,再不言。
戴闵生看了钟子启一眼,见他已经闭眼,瞅了一会儿,也闭目思索起来。
房间里一时静了,只有戴闵生手指在桌面上敲打,忽而如金戈铁马出塞外,忽而如春雨化夜润无声。
钟子启听着,心里便如坐了过山车般,起伏不定,可又知道这等事情不是自己说两句就能转变的,人一生的操守哪有那么容易动摇。只好耐心等着,大气也不敢出。
过了一会儿,实在不耐,索性抛开了这一切,想起自己的老婆来,不知她的那边过的如何了,可瘦了,有了新男友没有,是不是还想以前一样喜欢耍孩子脾气,一样天真可爱……想着想着,眼泪便止不住的留下来。
“戴兄,戴兄!”忽然,又被叫醒了,戴闵生的一脸关切的看着自己。
“戴兄可是在怪我不体谅你的一番好意?!”
钟子启忙定定神,笑着说:“呵呵,戴兄多心了,我只是触景生情,想起来以前的一些旧事罢了,决不是在怪罪戴兄!”
“那就好,那就好!” 戴闵生将信将疑的点点头。
“对了,戴兄到底怎么决断?!”钟子启想起正事来,不由立时又紧张起来,紧紧盯着戴闵生的脸,眨也不眨一下。
“我决定听钟兄的,求大义而舍小节!” 戴闵生一字一顿说着,直直看向远方天际。眼睛里也湿了。
钟子启不由伸手过去,紧紧握着戴闵生的手,他能体会的出,戴闵生做这个决定有多么的痛苦。王观礼只要将那悔过书一贴,戴闵生这半生的名节就立时毁于一旦,以后再难抬起头来,对一个名声在外的儒士来说,这无疑是比自杀都难受!
戴闵生看着钟子启,也将手紧紧握了,“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有钟兄在身边,我便不后悔!”
钟子启柔声安慰道,“这只是一时权宜之计,戴兄不必难过,终有一日,世人都会明白你的苦心!”
戴闵生摇摇头,“钟兄不必安慰我,后果是什么我心里明白的很。不过正如钟兄所言,‘慷慨赴死易,舍生取义难!’我既做了,便不后悔。是非功过,千百年后自有后人评论,我只求问心无愧!”
钟子启正要说什么,突然,房门被推开了,福悌笑着跑进来,开口说了一句,“义父,瑞儿都办妥了!”才发现屋里两个大男人正将手握在一起,含情脉脉的对视着,不由楞住了声,半晌才怯生生的说“义父,你们在做什么?没打扰你们吧?”
钟子启和戴闵生对望一眼,再都低头看看依旧紧紧握在一起的手,不由哈哈大笑。
福悌却是被他们笑楞了,脚不由的往后退缩着。钟子启看了他的动作,指着他,笑的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福悌被钟子启指着,立时动也不敢再动,只眼含恐惧的看着两个笑得前仰后合的大男人。
良久,钟子启才好不容易止住笑,“福悌,你这家伙,进来也不敲个门。好了,你办的好,没事了,自己下去弄点吃的吧。对了,你……”钟子启正想说你别把今天看见的事情说出去,转念一想,那不是欲盖弥彰么,反而让人生疑,便立时止口。
福悌看着,小心翼翼地问,“义父,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钟子启挥挥手,“算了,这没你事了,你下去吧。”福悌如蒙大赦般,飞一般逃了。
钟子启和戴闵生看着像兔子一般逃开的福悌,对视一眼,又哈哈大笑起来。
半天,钟子启才说,“戴兄,这一来只怕咱们两人要被扣个相公癖的冤名了,呵呵,真搞笑!”
戴闵生听着,似有所悟一般,叹息道“是啊,众人皆曰眼见为实,岂不知眼见也并不当真!哎!”钟子启听了,不由也是感触顿生,正想接话,戴闵生忽大喝一声,“钟兄,帮我拿了纸笔过来,乘我这会儿还有勇气,将那‘悔过书’写了!”
钟子启先还一楞,回过神来,不由不大喜,立时跑到书案边上,将纸笔取了给戴闵生,又在边上磨起墨来。
只听戴闵生笔下沙沙做响,不多时,两张悔过书便一挥而就,写完,戴闵生将笔往地下重重一抛,叹口气,怔半晌,回过身去,再不看钟子启,“钟兄,这个麻烦你拿去给那狗官,我今日累了,不想再说话了。”
钟子启知他心里十分难受,忙好言安慰了几句,帮他把被子又掖了掖,轻手轻脚的退下去了。出了房门,见福悌在院子里正看葡萄,便小声交代了不要去惊扰、只晚上按时喂药吃饭。福悌点了点头,却道:“义父,是不是因为刚才我撞进去,戴先生生气了?”钟子启不由失笑,“呵呵,傻孩子,和你没关系,刚才我们两人正在商量一件极为难的事情,我正鼓励他呢。现在戴先生违着良心被着毁名败誉的危险写了这书,心里很不好受,你就不要去打扰了,让他自己静会儿,知道了么?”
福悌点了点头,也不知是真懂假懂了。钟子启拍拍他头,又叮嘱了两句,出去了。
怕着夜长梦多,钟子启急急跑到客栈取了全部四千多两银子装成一大包,背了身上,带了那“悔过书”立即赶到县衙,本来想再到费文清那里借个四千两凑成八千两索性一块儿给了那戴“青天”,后来想想,只怕反会让他以为自己这银子容易弄,多得很,再有别的索求,便罢了。
到了县衙,给了那王观礼“悔过书”,王观礼大喜过望,连声夸奖他会办事,有手段,钟子启忙推辞道是王观礼威望过人等等,又乘热打铁,让他赶紧把这事结了,王观礼自是一口答应,当下便写了公文附上“悔过书”命衙役送交嘉兴府。两人晚上又是一场豪饮,在酒席上,钟子启便将那四千多两给了王观礼,并保证三日内再筹集余下的给他。这下王观礼真是笑得嘴都合不拢了,要不是碍着朝廷官员不得结党的律令,只怕当时就要和钟子启结拜不可。
两人在席上互相又是吹捧一番,听得都高兴,再加上都是心事尽去,别无牵挂,没一个时辰,又是大醉而罢。这回王观礼却是借着酒胆,并这夜里天黑,别人不易看见,将钟子启直送出大门才依依不舍作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