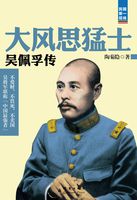这本书从开始确定撰写到最后截稿,耗时一年多,而书的结尾也从最初他“第一张协奏曲专辑的发行”拖到现在“柏林音乐会的圆满成功”。之所以跨时良久,结尾“一拖再拖”,是因为李云迪本身总处于变化状态,而我有责任展示这位年轻的钢琴家在取得最初的成功后如何进一步地延伸、攀升。当然,柏林音乐会只是本书的一个结束,对李云迪来说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无论如何,当我修改完最后一个字,原以为会特别兴奋,截稿后的感受也是我在写作过程中最常出现的想象。然而,我却出奇地平静,这才体会到内心深处的喜悦绝不是流于表面的兴高釆烈。
这本书算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光是搜集资料和大量的采访就用了半年多时间,而最艰难的部分是对李云迪本人的采访,他常年在国外演出,即便回国也是忙于音乐及配合一些宣传工作,因而我们能坐下来见面交流的机会显得尤为珍贵。
或许我该先说说对此书最初的设想,名人传记自然少不了对主人公成长经历的详细描述,展现一位成功人士的奋斗史。按着这想法我开始动笔,而与李云迪第二次见面时,他对该书的理念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我不希望写成一本单纯的人物经历式的传记,我不需要过多地介绍我的过去、我从小的经历这个过程。其实,在所有关于我的报道中,几乎没有人能真正触及我的本质。所以我希望大家能从这本书了解到我对音乐的感受,对钢琴的理解,了解很多重要的音乐事件,了解我在音乐中的成长,然后得到我的音乐性和个性。”
也许是看到我脸上的惊诧,他接着说;“我知道你已经开始写了不少,但是我仍然坚持这本书的主题是音乐,希望你能按着这个思路来写。”
于是,我重新开始构架这本书。这时候,事情也变得有些困难了,原以为凭借小提琴的底子,写音乐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动笔后才发觉,用具体的文字表现抽象而丰富的音乐多么困难。我开始大量地听名家不同版本的钢琴音乐,阅读有关书籍,然后我陷落在音乐里。这个过程太享受了,以至于听古典音乐成为我的习惯。我得到的太多了。
做李云迪的采访除了时间上的难度,我还有另外的顾虑,因为他一直很习惯面对媒体,我担心他对我的问题都是流于表面的程序式回答,让我无法进入他真正的状态。然而,与他交流后,才发现这顾虑是多余的,整个过程他都非常配合我,坦诚地与我畅谈,使我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此外,还要非常感谢他不断接受我的电话与邮件“纠缠”,以及他极大的耐心。
感谢李云迪的父母。李川先生为我提供了很多资料,也常给我一些诚恳的建议;云迪妈妈张小鲁身体一直欠佳,在这种情况下还接受我的采访多达9次,而对于我的电话采访也都在核实后给出最准确的回答。他们夫妇每次都很客气,在我把部分章节给他们看的时候,必然会说“谢谢,辛苦了”,令人心生暖意。
但昭义教授也在非常忙碌的情况下挤出时间接待我,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师长,记得2006年春节的大年初四,我打电话给他,没想到这位老教授已经开始给学生上课了。自始至终他对音乐教育工作的严谨和投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夫人高红霞女士,接受了我两次采访,一些宝贵的细节都是从她那里获得的。
还要感谢李云迪的爷爷奶奶,两位80多岁的老人非常朴实,对我的来访给予了最大的支持,甚至将从未示人的资料也交给我。爷爷再三地向我叮嘱:“这本书一定要说明,云迪是在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下成长起来的,是国家培养了他。”
在离开重庆向两位老人告别的那一天,腿脚不便的爷爷坚持要送我下楼,让我非常感动。还有云迪的姑姑和小姨,在重庆期间,两人从头至尾为我安排并陪我进行了一切采访,在这里要衷心感谢两位大姐的悉心照顾。
还要感谢深圳艺校的李祖德校长,这位老校长接受采访时正在养病,对于我几次三番的打扰,都不厌其烦给予接待。感谢深圳艺校的老师们为我提供资料,感谢所有全力配合与帮助我的人。
有人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其实文字未尝不是如此。毕竟,对于李云迪这样一个不露声色的年轻人,一位时时处于变化状态的钢琴家,总会错失某些珍贵的细节。好在,钢琴家仍有音乐与大家交流,他指下形塑的音符是属于他的表达方式,也唯有音乐才是他这个人的注解。
李音
2007年夏至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