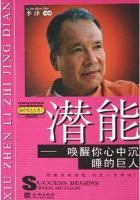对一个平常之辈来说,只有通过令人愉悦的谈吐、迷人的举止、八面玲珑的待人接物之道,才有可能被邀请出现在豪门府第、顶级聚会和名流社区。
我已经收到你有关战争的拉丁文讲稿,虽然你的拉丁文水平尚无法与恺撒、西塞罗、贺拉斯、维吉尔和奥维德等人相提并论,但已与那些博学的德国人口头或书面使用的拉丁语难分高低了。经过长期以来的观察,我认为那些所谓最博学的人,只不过是阅读了大量的拉丁文文献而已。至于他们的拉丁文写作水平,用非常糟糕来形容都不为过。也正因为如此,使得我们能够将绅士式的拉丁语学者和纯粹的拉丁语学究加以区分。一位绅士式的学者很可能只对奥古斯都时期的拉丁文感兴趣,所以能写的东西也不外于此。
然而看看那些学究们所读的拉丁文,糟粕远多于精华,不懂得加以取舍,其最终写出来的东西也就难免会有糟粕的影子了。在学究们看来,那些经典的书籍只适合在校的学生们去阅读,根本不值得自己一看。相反,他们乐意去苦心钻研那些无名作家的残存片断,并将所碰到的冷僻的词语铭记在心,抓住一切场合使用这些词语,以显示自己过人的阅读量,殊不知这是以牺牲他自己的判断力为代价的。普劳图斯是其所喜爱的作家,并不是喜爱普图劳斯那机智的个性,也并非是迷上了普图劳斯喜剧作品中的强烈喜剧效果,而是因为在普图劳斯的作品中,时不时地会运用一些冷僻的词语以及低层人物的措辞,而这些东西在别的地方难得一见。举例来说吧,他宁愿用olli而不用illi;用optume而不用optime;宁愿用不体面的词汇也不用体面的。假如他写的东西能够被证明是严格意义上的罗马人所写的拉丁文,那么按照这一原则,我现在也许就能用乔叟或斯宾塞的语言给你写信,并声明我写的是英语,因为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英语。但是如果我这么做,在别人眼中我就成了一个既矫情又自负的年轻人了,你也将难以明白我信中的片言只语。以上这些和诸如此类做作的怪癖,都是自以为是的蠢人与学究的特长所在,应当为所有理智的人们所摒弃……现在我要着重谈谈讲稿本身了。其中有一处教义使我非常惊讶。然而无论如何,我都无法想像毒药的使用可以被当作一种自卫的合法手段。毫无疑问,某种力量可以通过正当的手段击退另一种力量,但决不能通过背叛和欺诈的形式。当然我这样说并非是要将伏击、伪装、佯击这样的战争策略与背叛和欺诈混为一谈,这些策略通常是战争双方用以计划进攻以及抵御攻击的有效手段。但是,毒箭、毒水或其他你们军队使用的毒药(只有反叛者才会干出如此的勾当),就如我曾听说、读到和思考的一样,是非法的、无耻的防御手段,也是迄今为止你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所在。但是,我宁愿选择死亡也不去毒害敌军吗?是的,回答是肯定的,宁死也不能做出此类卑劣低下、十恶不赦的事情。此外,事先我也无法肯定:这支军队不会在最后一刻出击。然而,依我个人之见,如今的大众律师们,为了获取权威,宁愿践踏法律,也不去检讨那些君王和联邦州的非法行为。这些非法行为越来越盛行,以至于已发展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做法,虽然我敢保证,它再怎么盛行也永远不可能改变善与恶的本质。但可悲的是,人们对此已见怪不怪,因而这些非法行为似乎已不显得那么卑劣有罪了。请不要套用律师的遁词和诡辩家的“精妙绝论”,而应该根据每个人正确的理念和平实的常识,直接并坦诚地给出或对或错的看法。像处理自己的事情一样去行事,这是平实、肯定、无可争辩的道德与正义的准则。坚持这一点,并要确信:如果稍有违背,你就会让人觉得伪善、难以捉摸,尽管也许这一准则本身是错误、不公正和有罪的。我不明白:世界上那些罪证确凿的犯罪案例,何以在诡辩家们的眼中,其中的一些甚至许多竟然是无罪的。深入地想想,其实他们事先制定的原则经常华而不实,措辞貌似有理,但结论却是个谎言。这显然与正义、明晰、无可争辩的准则相违背,也与我上面所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大相径庭。然而,这些精巧的辩术和谬论,恰恰迎合了人们的情感与品味的需求,人们乐意接受这样的一种宽容,却不愿去发掘托词背后的谬论。确实许多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就使这些遁词与“精妙绝论”的发表影响更为恶劣。我既不是技高一筹的诡辩士,也算不上是反应敏锐的争论者。要不然我就能为响马贼从事的行业辩护和增彩,逐渐地、有理有据地说服那些无知的人们承认这个职业是清白的,甚至是值得赞美的。我读过一本书名为《颠倒黑白的伎俩》。如果一个人一旦脱离了普遍真理,脱离了众所周知的事理,去追求充斥着大量幻想和推断的所谓的“精妙绝论”,那么想要颠倒黑白就不像它所显示的那么难了。贝克莱博士是爱尔兰基督教新教的主教,是非常知名、足智多谋、学识渊博的人,曾经写过一本书,阐明世界上本无物质,所有的一切只存在于意识之中。如果真是那样,你和我只能在想象中吃、喝、睡。想象着你在莱比锡,我在伦敦。明明意识到自己有血有肉,四肢健全,然而却只能将自身当作一个精神体。对于他的论断,无法从严格意义上加以驳斥,但是也很难真正地令我信服。为此我决定不理会他的这一理论,继续吃和思考、散步和骑马,以保存物质。我无可救药地认为,体内存有物质。常识(实际上非常不寻常)是我认为的最好的依据。遵循常识,它将为你提供最佳的建议。出于娱乐的目的,可以阅读与听闻那些构想巧妙、真伪莫辩并充满丰富想象的精妙绝论。但只能将此看作是一种思维训练,真正要解决问题还得依赖常识。某天我在一个书摊前,因为两个小册子而驻足逗留。我以前曾读过这本书,这次带着新奇重新翻阅了这本书。这本书中绝大多数的放肆言语均出自犹太希伯莱,他大放厥词,并通过犹太教神秘信徒和玫瑰十字会会员的参与,以晦涩难懂的行话传播至今。这些人的数量,我相信已经缩减了许多,但是至今还有一些。我自己就认识其中的两位,他们研究并坚信那些神秘的胡话。当一个人那被禁锢的理智,通过幻想与偏见得到最大程度释放时,还有什么极端的言行所做不到的?!对此,古代的炼金术士又添油加醋地加以夸大,并由此认为他们发现了哲学家的碑石。另有一些极为知名的江湖医生,也采用它来寻求通用的医药。帕拉切尔苏斯,一位胆大的医师和疯狂的神秘教教徒,断言他已经发现了此物。为什么抑或为何,只有上帝知道。只有那些疯子才给以超感觉的名字。你能在海牙轻易获得此书。读了它,你会感到愉悦与惊奇,这确实是非常必要的一课。你的来信,除了十分简洁地围绕某个既定的主题进行阐述之外,既没有对我所期望之事作出答复,也不符合通信的目的。书信,类似于远离的朋友间的亲密交谈。因为我期盼以一个亲密朋友而不是父亲的身份与你相处,所以希望能从你的来信中,看到更多的有关你本人和你怎样为人处世的陈述和描写。当你写信给我时,假想你和我是在火炉旁自由地对话。这样的话,你会很自然地提及日常琐事,比如,你曾在哪儿待过,碰见过谁,你是怎么看待他们的,等等。
请在写信时也这么做吧,以便时而让我熟知你的学习和消遣情况。告诉我你的新朋友和他们的特点,写上你自己对他们的观察感受。总之,让我从信中读到更多关于你的事。你与普尔蒂尼公爵相处的如何,他在莱比锡的近况怎样?他是不是一个好学、才华横溢、勤奋的人?他的天性是善良的还是邪恶的?总之,他干了些什么?你是如何看待他的?你可以毫不保留地告诉我,我保证不会泄露出去。我热切希望能与这一年龄段的你,开展更多的彼此信赖的书信交往。就我而言,也会在给你的信中充分地表达对人和事的看法,这些看法除了你和哈特先生,我不愿其他任何第三者知晓。所以,站在你的立场上,你可以毫无保留地写信给我,寄予我充分的信任。如果你曾浏览过德塞维吉乐女士写给她女儿德格里格姆女士的信,你一定会体察到流露于字里行间的那种交流的随意、自由与友谊。不过我希望我们俩之间的情感能胜过她们。给我说说你手头正在看什么书,不管是学习方面的还是消遣方面的,我都爱听。说说你在国内和国外时的夜生活。我了解到,你有时会参加瓦伦廷女士召集的聚会。你在那做些什么呢?玩乐还是吃喝?或者那仅仅是礼节性的会话?当舞蹈教师在你左右时,你会介意自己的舞姿吗?由于你经常需要跳跳小步舞,我愿意让你的舞姿变得更优美。记住,手臂优雅的姿态、抻手的动作、脱帽戴帽的绅士风范,是一位有教养的男士跳舞时的重要部分。舞姿优美的最大好处在于能够教会你必要地展现自我,无论是坐、立还是行,都能显示出一种优雅的风度。这一切对于一位时尚男士来说,是真正重要的所在。但愿你到达柏林以前,就已成为了一个举止优雅和得体的绅士。不过,考虑到你将在那儿置身于上流社会,我会尽力帮助你尽快拥有这些得体的举止和风度。拥有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外,对达到你预定的目标尤为重要。打个比方,外交大臣的首要任务是查明秘事,了解他职责范围内可能存在的诱惑。而对一个平常之辈来说,只有通过令人愉悦的谈吐、迷人的举止、八面玲珑的待人接物之道,才有可能被邀请出现在豪门府第、顶级聚会和名流社区。到了那时,即便他有某些过时的举动,也不会再那么引人注目了。这或许是因为人们信赖他,或许是由于圈中人士的疏忽大意,因为这些人已习以为常地将其看作其中的一员,因此对他毫不设防。大臣只熟悉其在朝廷所赋予的那份职责,如果有意识地询问一下王子或大臣的拥护者,最近有什么最新指示,他们一定会警惕起来。但事实上,他们内心所知道的决不会超出其所应该知道的范围。这里,女士们也许可以派上大用场。王子的恋人、大臣的妻子或情人能够提供大量有用的信息,并且她们也非常乐意这样去做,借此炫耀她们是多么地受信任。不过在那种情况下,那种能打动女士的非凡谈吐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言辞有理得体、优雅有教养,是女士们所无法抗拒的。也有一类男士比较女性化,可以采用同样的方式吸引他们。这样的男士通常被认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他们云集于名宅豪邸,缺乏思想,没有知识。然而,由于优良的出身,他们能为各种团体所接纳;并且由于他们长辈的轻率与大意,他们无意中能得到有价值的秘密,这些秘密将会从他们那所谓得体的谈吐中轻易地吐露出来。
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