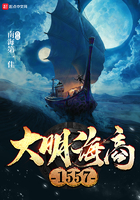三郎略一思索便明白了这里的玄机,当今皇上迷信道教,曾对林灵素信任有加,虽然后来醒悟过来把林灵素赶出京城,但林灵素和杀人案有牵连的事情一旦被宣扬出去,皇上的颜面就没地方搁了。
“这个案子最后只能以图财害命来结案,聂山这次可作难了。”何蓟苦笑着摇摇头。
石运宝道:“老何就别替人家操这个心了,聂山玩起花样来一点都不比别人差。你只管往后看,他肯定会把事情做得皆大欢喜。”
这时,茶酒博士进来撤了看盘,随后,各色菜肴不断地摆了上来。
“来来来!咱们喝酒,今天高兴,不喝翻一个不算完。”何蓟端起酒杯。
三人酒杯一碰,一饮而尽。
放下酒杯,钱大拿问:“你们两位上官这次破案有功,是不是要升官了?”
何蓟道:“按道理应该是的,聂山身边的人偷偷透露给我消息,聂山已经把有功之人的名字上奏给皇上,估计很快就会有结果,若不出意外,俺会到其它地方去,留下的位置八成是老石的。”
“恭喜!恭喜!”钱大拿站起来给他们倒酒。
“老钱,你就别和俺们客套了。”何蓟摆摆手,问他:“倒是你自己的事情怎么办,想过没有?”
“不知道,走一步说一步吧。”
“你别以为俺提前来这里是想找女人寻快活,俺是为你打听事儿来了。”
“为俺?”钱大拿有些摸不着头脑。
“是啊,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俺吃了你的,自然要为你办事儿,可不想欠你老钱的人情。”说着,脸一沉道:”你老钱看着挺精明的,其实做起事情很糊涂。”
“俺咋了?”钱大拿诧异地道。
“你这两天是不是还在四处花钱走门子?”
“是啊,你咋知道的?”
何蓟道:“别忘了俺是司录司的,想要打听个事儿不是什么难事,这会仙酒楼可不一般,来这里的人好多是京城的官员,这些人喝点酒,上边和下边都把不住,神魂颠倒之际,秘密就不是秘密了。只要肯花点小钱找这里的娼妓打探消息,一打探一个准。”
“这么说,你刚才来这里是为安打探消息的?”
“刚才俺从那个妓女那里把你的事儿打听清楚了,为这个,花了俺十两银子,都记在你的账上。”
“好的,我认,别说十两,一百两俺都认。”钱大拿毫不在乎的点点头:“打听出什么了?”
“京城里的人几乎都知道你的事情,还有人把你的事情当笑料告诉了这里的妓女。”何蓟瞥钱大拿一眼,见他不吭声,又道:“她们都知道开封府的人破案时救出个光屁股的官儿,而且这个光屁股的狗官还把开封府尹聂山吓个半死。想想看,你这时候去跑官,人人避之犹恐不及,更别说为你办事了,即便你掏钱再多人家也不敢要,明白吗?”
“你这一说俺算彻底明白了。”钱大拿地下头。
何蓟见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安慰他道:“别那副没出息的样子,男子汉大丈夫要拿得起放得下。等这阵风过去后再说。”
“就听你们的。”钱大拿自嘲的一笑道:“俺做官其实就是吃饱了撑的,既然不能做官,俺也死了这条心,老老实实做俺的富家翁。”
石运宝大笑道:“这就对了,富家翁的生活可不是人人都能有的——娘的!赶明儿有空闲就到温州找你这狗东西耍去……来来来!咱哥俩干一杯!”
钱大拿端起酒杯:“老石,你这狗东西只管来,到时候俺让你开开眼,见识一下什么叫享受……”
“好!就这么说定了。”
几人越喝越兴奋,说话越来越投机。
喝了一会儿,三郎趁着酒意对何蓟道:“何大哥,俺求你点事儿成么?”
何蓟道:“别说求不求的,兄弟你有事尽管说。”
“嗯,是这样,那天在万家后院,你射万老大的那一箭射得太准了,小弟佩服的很,俺想跟你学学射箭。”
“俺当是啥大事儿呢,”何蓟一拍胸脯道:“这事包俺身上。”
石运宝道:“找老何学射箭算是找对了,射箭可是老何的家传。”
“家传?”
石运宝道:“他爹是步军司的何太尉,箭法入神,名声远扬,连西夏的箫太师见了他也行礼。老一代武将中,何太尉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有这样的老爹,老何的箭术自然是不差。”
“噢!这么说,我还真找对人了。”三郎很高兴。
何蓟道:“不瞒几位说,俺的箭法和家父一比,差得不是一星半点,惭愧的很!不过,教三郎入门倒是没问题。”
石运宝道:“让俺说,择日不如撞日,明天你就开始教吧,黄河滩上野兔野狐多得很,一边学箭一边打些野味,就地烤了来吃。”
钱大拿一拍大腿道:“好主意!带着酒菜往黄河岸边一坐,一边观风景一边喝酒,不亦……这个……乐乎。”
石运宝道:“老钱,又没你什么事儿,你乐乎个屁啊?”
钱大拿瞪着眼道:“咋了?你们去射箭,俺就不能去瞧瞧?”
“老钱想去也可以去,只要你不怕累就行。”何蓟端起酒杯,“来来来!干了这杯酒,就这么说定了,明天去黄河滩射箭!”
。。。。。。
第二天一早,三郎便按照何蓟告诉他的地址来到报慈寺街,远远地看到石运宝站在一棵柳树下东张西望。
见到三郎,石运宝老远就招手,等三郎走近,便亲热地拉着三郎道:“走吧,老何的小院在对面那小巷子里。”
“老钱呢?”
“早来了,这个蛮子能把人笑死,大包小包的带了好多吃的,生怕饿死似的。”
何蓟的住处是一个很平常的四合院,院子不大,两边厢房前各种一棵石榴树,稀稀拉拉挂了十几个青色的石榴。
三郎一边四处打量一边问:“何大哥的家就在这里?”
“他啊,根本不在这里住,这套院子是背着阿嫂添置的,本打算娶个小的在这里,后来便不吭声了,估摸着是怕阿嫂晓得了和他闹。”
“看来何大哥还挺花花呢。”
“是挺花花,不过阿嫂看得紧,不然的话,早在外面生几窝了——你瞧瞧这四合院多安静,养个小娘皮专心生崽子,再合适不过了。”
“滚你的臭鸭蛋吧!”何蓟从院子后面出来,瞪石运宝一眼道:“别只在这里只说俺,说说你自己吧,前些时是谁光着腚被人捉奸在床的?”
“直娘贼的,怎地哪壶不开提哪壶?”石运宝讪讪的道。
“还不是你先挑了头?俺虽说有讨小的念想,但还没有真的讨。”何蓟拉着三郎的手道:“走,后院看马去,老钱也在后面,这家伙嫌俺借来的马不好。”
后院里,钱大拿正背着双手挺着蝈蝈肚围着马转圈子。
三郎笑着提醒道:“老钱,怎的在马屁股后面溜达?小心它撩蹶子给你一蹄。”
“三郎你看,这哪里是马?简直就是驴子么,就这么二指半高,还瘦得皮包骨头,俺正怀疑这东西会不会撩蹄子。”钱大拿说着,伸手拍拍马屁股,那马经他一拍,尾巴甩了甩,“哧哧”地撒起尿来,钱大拿慌得赶忙往后退:“这畜牲,撩不动蹄子便使这下三滥手段对付俺。”
石运宝哈哈大笑道:“蛮子,你可真色,连马的那地方都要摸,这下好了,赏你一泡尿。”
何蓟道:“这是俺到骥騏院借的马,人家不敢借给俺军马,又不愿拂俺的面子,便拿几匹快淘汰的马糊弄俺,好在咱们只是到黄河滩,路程不远,老钱你就别挑剔了。”
“好吧,既这么说了,便骑这个了。”钱大拿无奈的答应了,低声嘟囔道:“赶明儿俺去骡马市买两匹好马去。”
何蓟道:“如此,一人牵一匹,咱们上路。”
三人骑马出了酸枣门,胸怀顿觉一畅,石运宝贪婪地看着野外的景致,大大咧咧地道:“好!好!真好!”
何蓟道:“运宝夸风景的词很别致,虽然说得直白了些,但一个‘好’字把该说的话全说完了,要是换了那些文人墨客,准会吟诗填词感慨一番。”
石运宝道:“俺最讨厌这些家伙,有话不会好好说话,偏要拐弯抹角,直到把人说糊涂为止。”
钱大拿道:“你糊涂是你自己的事,别人未必象你一样糊涂。”
石运宝撇撇嘴:“算了吧,你若不糊涂,会被人灌蒙汗药?”
“被人灌蒙汗药咋了?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liu。”
“风liu个屁!心肝都快被人掏出来喂狗了,还风liu呢。”石运宝成心逗他,依依不饶的道:“那女人是牡丹花吗?狗尾巴花还差不多。”
“狗尾巴花也挺好,闻着有味。”钱大拿毫不相让。
“是有味——骚味!”
“女人有味道才招人喜欢,不管她是骚味还是香味。”
石运宝嗤之以鼻:“照你这么说,你找女人就省事了,不用眼睛看,只用鼻子闻,即便是黑灯瞎火也不耽搁事儿——狗就是这样找伴儿的。”
“错了,俺说的‘味道’可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且说来听听。”
“假如你见到一个女人,你可能会说这女人很风骚,也可能会说很温柔、很贤惠、很妩媚、很娇艳……这就是女人的‘味道’,这‘味道’只能用心去品,不能拿鼻子来闻。”
石运宝不理会他那一套,嘲笑道:“你老钱真是越活越回去了,连黄口小儿都知道味道就是用鼻子来闻的,不能用鼻子闻的就不叫味道。”
“真是对牛弹琴,白废俺这么多口舌。”钱大拿无奈地摇摇头,用手指着路边的野花道:“看到这些花了吗?在人眼里,它们是鲜花,在牛眼里,它们却是草料。”
“哦?你说我是牛?”
钱大拿道:“错了,说你是牛就夸你了,你是头猪!”
“呸!你才是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