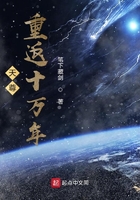1956年,苏联莫斯科兽医学院院长、著名寄生虫病学研究专家叶尔绍夫在莫斯科兽医学院作过一个《关于中国的兽医教育》的报告,他说:
“我考察了中国十多个兽医专业教育机构,包括南京农学院的兽医专业,其前身为中央大学兽医系,曾经拥有中国第一流的兽医师资和设备,培养出许多人才。但我考察后认为,唯一与莫斯科兽医学院相当的,是兰州小西湖的那个小小的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所以,通过外交途径,我们之间建立了姊妹学院关系,可以直接交换资料,相互交流。”
当年在莫斯科兽医学院进修的西北兽医学院教师买永彬聆听了这一讲话,他作了详细记录并传到了国内。
莫斯科兽医学院在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兽医行当里的龙头老大,没有人能与之抗衡。究竟西北兽医学院有什么能使苏联驻中国农业专家组组长叶尔绍夫如此看好,并认为可以与之比肩而立、不相上下呢?
首先是学校形成了一个以盛彤笙为核心的强大的办学团队。经过几年的努力,伏羲堂前已汇聚了全国业内学界的一大批精英。到1956年,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已有16名教授,6名副教授,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来自欧美的海归人士。其中盛彤笙为一级教授、中科院学部委员,朱宣人、许绶泰、张松荫、杨诗兴、粟显倬为二级教授。由于教师力量的加强,主要学科都有了学术带头人,兽医专业有中国兽医病理学奠基人的朱宣人,寄生虫病学家许绶泰,兽医内科学家、中兽医学家蒋次昇,兽医微生物学家廖延雄,兽医产科学奠基人陈北亨,兽医解剖学家谢铮铭,兽医外科学家秦和生,传染病学家蒋鸿宾;畜牧专业有动物营养学家杨诗兴和彭大惠、养羊学家张松荫、养马学家崔堉溪、畜牧学家粟显倬、牧草学家卢德仁、植物学家栗作云、农业经济学家李林海、草原学家任继周,这些都是当时国内畜牧兽医界的顶尖学者。以他们为首,又形成了每门学科的学术梯队,以畜牧系当年的养羊教研组为例,张松荫为“主帅”,下面有范涛、张尚德、张汉武、张鹏亚、卢泰安、魏怀芳、徐慧茹等多员“大将”,在国内同行中,阵容空前。兽医系的微生物教研组以廖延雄担纲,配备有张树藩、张思敏、赵纯庸、张秉一、沈斌元、安爱荣、方永祥等,无论课题研究还是诊治疫病,都得心应手,挥洒自如。以后廖延雄回到老家江西,还感叹当年学术梯队的强大,现在无梯队、少帮手,再也搞不出成果了。
基础课的师资力量也十分了得。教生化的,有生物化学科主任高行健教授、戴重光教授,教生物学的有郝逢教授,教英文的有张素我教授,教英文和国文的黄席群副教授。他们的到来,使学院犹如鲜花著锦,盛极一时,使国立兽医学院成为藏龙卧虎之地,他们像璀璨的群星,闪烁在大西北的天空。有的校友自豪的称当年兽医学院的老师“那是绝对权威”。世界上本没有绝对的事情,而校友觉得唯有用“绝对”二字方能抒发自己的情感。当初兰州各高校教授相互兼课,兰州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感叹“兽医学院的教师怎么都这样厉害!”
其次是在教材编写上执农业院校之“牛耳”,居盟主地位。教材作为知识的载体,操作的依据,学术的指南,学生的食粮,历来受到盛彤笙的重视。他认为学科建设赖名师,专业建设赖教材,学术以教材为基石。1949年以前,中国没有自己编写的兽医专业教材,学校大多数用的是英、美教材和自己在教学实践中编写的讲义。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一些学者才开始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和心得,将所授课程出书,但不成系统,所以盛彤笙在西农、成都时期,就自己开始了教材的编写。1947年,盛彤笙在国立兽医学院成立了出版组,秦和生被聘为出版组主任,要求教师将自己的教学讲义,经验结晶,付之于文字。1949年以后,全盘苏化,教材完全采用苏联的教材,直到1956年,农业部组织全国高等农业院校编写试用教材,才开始教材的本土化。当时兽医11门专业课,有7门半是由西北畜牧兽医学院主编的,可谓“十分天下有其七”。这些教材是:
《家畜解剖组织学》,西北畜牧兽医学院谢铮铭主编;
《家畜病理学》,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朱宣人主编;
《家畜微生物学》,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廖延雄主编;
《家畜产科学》,西北畜牧兽医学院陈北亨主编;
《家畜外科学》,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秦和生主编;
《家畜内科学》,西北畜牧兽医学院蒋次昇主编;
《家畜诊断学及X光学》,西北畜牧兽医学院蒋次昇主编;
《家畜寄生虫学》,北京农业大学的熊大仕和西北畜牧兽医学院许绶泰共同主编。
只有《家畜生理学》《家畜药理学》《家畜传染病学》分别由江西农学院向涛、华南农学院冯祺辉、南京农学院罗清生主编。
由于这些教材出自名家之手,有些已成为中国现代兽医学术的发轫与奠基之作。教材全面、系统、新颖,传承了美、德、英先进的畜牧兽医理论与实践成果,是其与苏联畜牧兽医界一比高下的资本,也成为与全国畜牧兽医界同仁学术交流的纽带。时延至今,许多畜牧兽医教材仍为甘肃农业大学担纲主笔,优势与传统昭彰,这是其治学精神和学术遗产流传的印证。
其三是较为雄厚的科研实力。随着一批“海归”的到来,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最早在大西北揭开了科研工作的序幕。他们针对畜牧业生产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先后开展了家畜疫病防治、家畜繁殖和草原等方面的研究,如许绶泰开展的家畜的多项寄生虫病研究;张松荫关于新疆细毛羊与西藏羊、蒙古羊杂交代性能的鉴定研究和在永登县进行的甘肃肉毛兼用细毛羊培育;杨诗兴在朝鲜战场解决战地军马牧草中毒和军马粗饲料就地收割、贮藏的研究;朱宣人首次结合外检对我国马属动物肿瘤进行的组织学分类;廖延雄对羔羊痢疾的发病机理和治疗的研究;任继周对高山草原定位研究和草原生产规律的研究等,都取得显著成果,并逐步形成了一些重点专业和学科。
当时这些科研成果虽然没有评什么奖项,但却提高了自己的学术水平,实实在在地解决了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为老百姓带来了福祉,同时在国内外畜牧、兽医和草原界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先后有苏联、保加利亚、波兰、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的专家学者来院参观、讲学,相互建立了科技学术交流关系。
1954年秋,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偕文化参赞、秘书、翻译等来兰州,参观访问了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盛彤笙全程陪同。他们一路看后,来到微生物教研室,想不到大使却对正在进行的中药抑制细菌的试验很感兴趣,其中对黄连素的灭菌作用更为关注,让廖延雄详细地介绍了试验过程。临行前,大使还索取了资料,说“我们印度也有类似的工作,我将你们的做法带回去,也将印度的出版物赠送给你们,互相交流”。1955年3月,印度大使馆新闻专员古华致信学校表示感谢。此后,学校收到了从印度寄来的3种最好的畜牧兽医刊物,并期期相送,一直到1962年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开始方才停止。
其四是图书、仪器、教学设施日渐完备。经过盛彤笙持续不懈的努力,最终图书仪器之精良,当时已在全国各兽医教育机构中首屈一指,仅显微镜就有188架,其中精细天平和电动天平就有23台,使外国同行参观后都自愧弗如。这些贵重的仪器和药品大多购自美国,手术器械来自德国。许多老校友还津津乐道当年上实验课每人一台显微镜,实习用的手术剪、手术刀、镊子等都是驰名世界的德国“蛇牌”商标,用了多年还和新的一样。
学院还与国外的许多大学和学术机构建立了联系,他们称其为“中国的兽医学院”。以至于在搬离兰州十几年后的“文革”时期,国外同行写信或交换资料,寄的地址还是“中国甘肃兰州小西湖硷沟沿18号国立兽医学院”收。
廖延雄曾经对学校好有一比:“那时的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是兰州的一朵玫瑰花,既红艳又芬芳,教学、科研、结合生产、体育、伙食、卫生、接待等都很好,校风也好,这也是盛彤笙院长及全体师生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令人怀念。”
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的校友和教师都为母校堪称“亚洲一流”感到骄傲和自豪。这绝对不是师生们的自我吹嘘,事实的确如此。除了盛彤笙和同仁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心血外,客观上也有一些原因。民国时期,中国知识界有南渡与北归之说,所谓“南渡”,指日本侵华时形势危急,一些重要的教育机构、文化机构、科研机构南迁;“北归”,指抗战胜利后,这些教育科研机构,人员“还都”京沪。但也有一些机构和人员并未北归,一些强大的学术团队“离散”。原来盛极一时的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在1946年复校南京时,一部分知名教授或留在四川或转聘其他农业院校,还有的进入政府部门设立的畜牧实验所、兽疫防治处、羊毛改良处、血清制造厂等事业单位任职,人员四散各地;而盛彤笙却借此机会聘来了当时国内许多一流人才,新中国成立初院系大调整时又补充了不少师资,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学术队伍;国内其他一些畜牧兽医院校多为新中国成立初期设立,基础薄弱,自然难以匹敌。再从亚洲当时的情况来看,畜牧兽医还都是综合大学中的一个学院,单独设置的仅此一家。这样纵向一比,自然言之不谬。
1957年对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来说,是一个由盛转衰的“拐点”。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将一批知名学者打入“敌对阵容”,被戴上“右派”帽子,调离教学岗位,监督劳动改造。更为令人惋惜的是,随着甘肃省委“文化西流”战略的实施,在一片反对声中,西北畜牧兽医学院于1958年7月迁往武威黄羊镇,与筹建中的甘肃农学院组建了新的甘肃农业大学,许多专家教授大量外流,专业队伍大为削弱,一所“亚洲一流”的学校从此消失,但盛彤笙始终对这所学校有一种血肉相连难以割舍的感情。它如同一个小孩,是在他手中诞生的,以后又由他抚养长大,对学校是那样亲切、深情。学校迁往河西,他一直持反对态度,特别令人想不通的是,他仍兼任院长,迁校的事却没有任何人征求过他的意见,他觉得过去环境那样险恶都没有迁校,为什么现在说迁就迁了呢?即使调任南京后,学院在他的心中仍占有一席之地,80年代重病期间,还写信嘱托时任甘肃农业大学校长的陈北亨教授把兽医学院恢复起来。1986年4月,学校派人专程赴南京探望病中的盛彤笙先生,他抱病在家中接待,还寄语说:“相信到了一定的时候,甘肃农业大学一定会有和国外一样的学院,其中也包括一个畜牧兽医学院、草原学院。”
原夫科学之发达,由于分工、文化之交响,盖亦由斯;而人类之进步,莫不自粗而精,自疏而密焉;分工细则其学也专,精而密则其交融也和;学专而文化昌明,和谐而矛盾以去,人类文明之幸福基于此,科学真谛之原则亦肇于斯。
———盛彤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