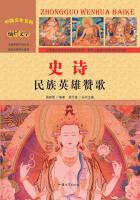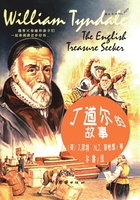在以往的红学爱好者中,褒黛贬钗者居多,他们赞扬黛玉的个性、爱情,批判宝钗的圆滑、世故。其中最容易被拿来说事的就是“扑蝶”一事。黄衣裳说“曹雪芹写林黛玉与薛宝钗,分明是以‘敌体’相待。写林黛玉抓的是一个‘真’字,写宝钗突出一个‘伪’字。其中最不留情面的当然是‘扑蝶’一章,人物的心理变换,急遽间采取的决策,把嫌疑推到黛玉身上,一切都那么自然,而从小红她们的反应看,私话被林姑娘听了去,可不得了了。想不到一笔竟写出两个不同的个性,如此鲜明而不留余地。”“注释1”真如评论者所说是宝钗嫁祸于黛玉吗?笔者却不这样认为,研究人物的个性、心态,要把人物的言行放在特定的语境中去分析,不能凭主观臆断,更不能凭自己的好恶。宝钗在此情境下为避免尴尬,急中生智,文本写道:
宝钗在外面听见这话,心中吃惊,想道:“怪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了,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才说话的声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的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犹未想完,只听“咯吱”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颦儿,我看你往哪儿藏!”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那亭子里的红玉坠儿刚一推窗,只听宝钗如此说着往前赶,两个人都怔住了。宝钗反向他二人笑道:“你们把林姑娘藏在哪里了?”坠儿道:“何曾见林姑娘了。”宝钗道:“我才在河那边看着林姑娘在这里蹲着弄水儿的。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还没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见我了,朝东一绕就不见了。别是藏在这里头了。”一面说,一面故意进去寻了一寻,抽身就走,口内说道:“一定是又钻在山子洞里去了。遇见蛇,咬一口也罢了。”一面说一面走。心中又好笑:这件事算遮过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样。
谁知红玉听了宝钗的话,便信以为真,让宝钗去远,便拉坠儿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这里,一定听了话去了!”坠儿听说也半日不语。红玉又道:“这可怎样呢?”坠儿道:“便是听了,管谁筋疼,各人干各人的就完了。”红玉道:“若是宝姑娘听见了,还倒罢了。林姑娘嘴里又爱刻薄人,心里又细,他一听见了,倘或走露了风声,怎么样呢?”二人正说着,只见文官、香菱、司棋、侍书等上亭子来了。二人只得掩住这话,且和他们顽笑。(第二十七回)
这两段话成为评论者指摘宝钗的主要“证据”。就字面意义看,似乎宝钗使用了“金蝉脱壳”的计策,将“偷听”红玉和坠儿说话的嫌疑人指向林黛玉,将自己洗脱干净。就深层分析,这是曹雪芹使用的迷魂阵,故意引导读者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行。曹雪芹的真正目的是刻画下人视阈中的薛宝钗和林黛玉的性格与形象。一些评论者没有细读文本,仔细揣摩其中的真意,就主观臆断,硬说是宝钗陷害黛玉,宝钗实在冤枉!从情理上分析,这是薛宝钗等人嬉戏、玩耍时的话语,既然是嬉戏、打闹、追逐、玩耍,就要有嬉戏、打闹的对象,因此,与宝钗嬉戏、打闹的对象就有了基本的框定:
第一,宝钗不能与丫环嬉戏、追逐,所以不能说丫环的名字。宝钗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颇具修养,深谙封建礼法,主奴有别,尊卑有界。她不可能与丫环嬉戏,至少在室外是不可以与丫环打闹嬉戏的。所以,宝钗不能说丫环的名字。那么,宝钗是否可以以寻找自己的丫环为由,顺便说出丫环的名字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宝钗的身份是主子,她身边不止一个丫环,即使有寻找丫环这样的差事,也应该由小丫环来做,身居闺阁的千金小姐——宝钗不可能亲自出来寻找丫环。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宝钗都不可能说丫环的名字。
第二,宝钗不能说寻找宝玉。在那个时代,“男女授受不亲”,男女几乎不来往,即使来往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就是表兄妹亲戚,也要严格遵守封建礼法。宝钗的性格、学识、修养决定了她是一个恪守封建礼规的“淑女”,不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傻少女”。因此,她不可能与自己年龄相当的男性宝玉在公开场所追打取闹。
第三,不能说长辈。王夫人、邢夫人等长辈,不论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都有丫环通报,而且,宝钗也不可能与长辈如王夫人、邢夫人等追逐打闹、玩耍。
第四,不能说王熙凤。王熙凤所到之处,都有丫环尾随左右,并且宝钗也不能与管家奶奶王熙凤追逐、打闹。从王熙凤方面来说,身为管家奶奶,掌管着贾府上下几百口人的吃穿用度,论工作、论活计,可以说是够忙活的,有时忙活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真巴不得有分身之术,哪有时间与宝钗玩耍、嬉戏?再者说,王熙凤管家少奶奶的身份也不允许她在公开场所与姊妹们追逐、嬉戏。
第五,不能说迎春。迎春性格内向,少言寡语、木讷,是出了名的“二木头”。即使姊妹们在一处玩耍,迎春也是少言,静坐,看得多,说得少。宝钗不可能与这样性格的人在园子里玩儿“捉迷藏”。
第六,不能说惜春。惜春尚小,与宝钗年龄相差悬殊。宝钗与她无论志趣、爱好都不相同。只有年龄段相近的人,才有基本相同的爱好,才能玩儿到一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宝钗顺口说出的只有黛玉和探春二人了。那么,为什么不说探春呢?探春的性格、年龄都适宜与宝钗嬉戏、玩耍,为什么不说探春而说黛玉呢?这就是值得探究的问题了,也是问题的关键。
宝钗不能说探春。宝钗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她所遇到的问题是,宝玉屋里的丫环小红正和坠儿说贾芸捡到小红丢失手帕子,要酬谢的事。丫环与爷们儿私传物件,违反了贾府规矩,理应受到制裁。探春是一个思维敏捷、有思想、有主见的人,是贾府的主子,对家中出现的违规之事,她不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即使自己不亲自处理,至少要汇报给王夫人或者王熙凤。如果宝钗假装寻找探春,让小红和坠儿误以为自己的谈话内容被探春听去了,真有可能做出“狗急跳墙”的事情,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宝钗说出黛玉的名字,让小红和坠儿误以为她们的谈话被林黛玉听去了。林黛玉是客人,对主家的事情不便说三道四,只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视而不见。因此,不能说探春,只能说黛玉。
宝钗顺口说黛玉的另一个理由是,自宝钗与黛玉二人长谈之后,二人关系比以前密切了许多,可以说是交心交肺。宝钗顺口说出黛玉的名字,是其关系密切的体现,只有二人关系亲密,黛玉在宝钗的心中占有一定的位置,才能时时刻刻出现在宝钗的脑海中,顺嘴说出她的名字也就成为必然。只有二人你心中有我,我臆中有你,形同一人,你才能在对方心中、眼中、口中时常出现,不经意间才会流淌出来。宝钗顺口说出黛玉的名字,就是这种情形的无意识流露。
以往评论者之所以抑钗扬黛,是基于以政治功用和社会功用的审美观审视小说,把黛玉的语言尖酸刻薄,视为富有个性,是具有反抗性、叛逆性的体现;把宝钗的处世“圆滑”、机敏、随和,视为自觉维护封建卫道者的“帮凶”。因为年轻,尚不具备封建卫道者的资格,故慷慨赠其“伪善”之桂冠。有评论者把宝钗“扑蝶”的话语视为对黛玉的陷害,把金钏跳井后,宝钗对王夫人劝慰的话语,视为宝钗讨得王夫人的好感往上爬的“伪善”。那么,当黛玉生病时,宝钗亲自送去的人参又当何解释?难道也有什么目的吗?若说有,那只能是对黛玉的关怀!如果说,她们二人是“情敌”,宝钗若没有宽广的胸怀,善良的心肠,岂不希冀“情敌”消亡,还能送人参与她?更何况,薛宝钗压根儿就没有看上宝玉,宝玉不是她理想的未来丈夫。所以,说黛玉是宝钗的“情敌”缺少足够的证据,难以成立。从而说宝钗陷害黛玉,也就失去了根基。
第二十二回,贾母为薛宝钗安排的十五岁生日隆重热烈,不仅有上等的酒席,还在院中搭起了小巧戏台,请了一班新出的昆弋两腔小戏。因是薛宝钗生日,又加之贾母喜欢她稳重平和,特意问宝钗爱听何戏、爱吃何物等语。薛宝钗深知贾母老年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食,便总以贾母往日素喜者都说了出来。贾母更加欢悦。
薛宝钗依照贾母的口味和爱好,把老太太素日喜欢的戏文和食物说出,博得贾母欢心。这是没有错的,她体现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薛宝钗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她为人处世不是仅仅考虑自己,而是尽可能地考虑身边的人;如果人数众多,不能照顾到每一个人,那只能考虑最主要的人——贾母的感受。基于此,她按照老太太的爱好和口味说了戏文和食物。有人由此认定薛宝钗虚伪,是为了抢占宝二奶奶的宝座,故意在贾母跟前表现自己,讨好贾母。这一观点极其错误,试想一个知书识礼的年轻人,老祖宗出钱为你过生日,内心已是充满感激,为了表达对老祖宗的感激之情,点一些老祖宗喜欢看的戏文和爱吃的食物,不是人之常情吗?怎么就成了虚伪了呢?难道要薛宝钗以自我为中心,置所有人于不顾,表现极端自我,只点自己喜欢看的戏文、自己喜欢吃的食物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她还是那个知书识礼、处事稳健的薛宝钗吗?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孝”为先,薛宝钗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了“孝”的内涵,这是读者应该尊敬与学习的。可是,到了某些评论者的笔下,为什么就成了虚伪与阴谋呢?这真是奇事怪事!为了吸引读者的视线,抛开文本,一味追求观点标新立异——“新”、“奇”、“怪”,这不是研究者的姿态。真正的研究者,是立足文本、研读文本,从文本中挖掘出蕴含在字里行间的意蕴,不以自己的爱好取舍文本原意,更不人云亦云。薛宝钗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表现出一个少女少有的胸襟与肚量,值得赞美。如果薛宝钗以自我为要,不顾及众人感受,点自己爱听的戏文,点自己爱吃的食物,充分彰显自我、个性,那还有和谐、欢悦的气氛吗?薛宝钗这一人物形象,之所以具有永恒的魅力,与她身上存有的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不无关联。
宝钗的命运是悲惨凄苦的,她制作的灯谜已经暗示出她婚后孤凄寡居的凄凉结局。“朝罢谁携两袖烟,琴边衾里总无缘。晓筹不用鸡人报,五夜无烦侍女添。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光阴荏苒须当惜,风雨阴晴任变迁。”
论财富,贾府荣华富贵已尽,轮到宝钗时则是一无所有。论夫妻关系,她和宝玉既无琴瑟和美的夫妻浪漫,也无夫妻相拥、恩爱缠绵的情感享受,宝玉先是呆傻,后是出家,宝钗年轻守寡,孤寂凄苦,她像一支香烛在凄苦煎熬中耗尽一生。